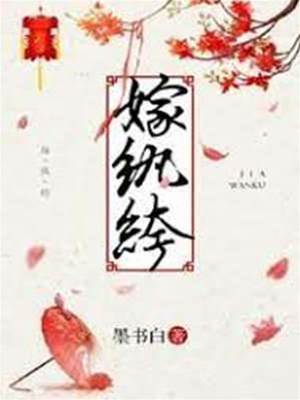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尚書大人,打發點咯》 第二十四章 鐵打的方婉之
在那之后,玉塵奉宛的車還是會隔三差五的來接方婉之。方正又讓送過去很多古董,價值不菲,稱得上名貴,卻日日堆積在茅屋的房檐之下,被春風吹的灰頭土臉。
連喻在方婉之和自己之間掛起了一道簾子,中間還是留了兩個窟窿,只是停駐在上的視線越來越。發間的那簪子,也重新換了常用的玉冠。
皮皮說:“方大姑娘....東西別再送了,我們家爺不喜歡。”
其實他更想說的是,連喻不喜歡每次來時端起的諂笑臉,和誠惶誠恐的討好賣乖。
但是方婉之每次來時都會說:“閣老安好,這件瓷瓶是家父特意讓奴家送過來的。”云云。諸如此類的話,連喻聽的太多了。太多了,就會厭煩,遠不如村頭張小二的三媳婦喂豬的時候被咬了聽。
他能看得出方婉之跟的爹是不同的,但是有些話方婉之不說,他便也不會多問,畢竟個人都有個人的活法,覺得這是的活法,那便由著,沒理由看不上。
連閣老十分喜歡這種偶爾的自省以及自我告誡,然而真正運用到實際上的卻并不多。諸如他會告訴自己,你的聲已經很差了,從今往后要做個好。但是事來的時候,他還是不介意往自己上潑一潑臟水。再如方婉之這件事兒,他心里很理解,也知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卻還是很看不上。
王守財仍舊一如既往的混蛋,睡醒一覺之后就會喜歡著爪子四撓墻。沒有了方婉之管教的王守財,已然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今日不知怎麼,它無端就瞧著橫亙在連喻和方婉之之間的簾子不順眼,爪子向上一勾,利用胖的優勢就地一滾,刺啦一聲就給扯下來了。
Advertisement
貓臉兜頭蓋臉被蒙上的簾子似乎讓它不勝其煩,躺在地上轉圈的四肢爪子踹,像極了一個跌壞了腦子的神經病。
連喻看見了,方婉之也看見了,都沒。
只不過前者是遷就,由著它玩兒,后者則是在思量,到底要不要胖揍它一頓。
王守財這兩天,因著方婉之對它一味的不敢手,囂張之氣簡直昂首。頭臉鉆出簾子之后,又后一蹬跳上了連喻的桌子,爪子踩在硯臺里,又跳回連喻上,沾了他一的濃黑墨。
方婉之就那樣看著,看著,看不下去了,徑自走過去提起它。
連喻還是那副聽之任之的樣子,低頭看著袍子上的墨點,又了方婉之一眼,神淡淡的道。
“下手別太狠。”
他難得跟說話,方婉之卻是抓著王守財不了。
抬頭嬉皮笑臉的一笑,拿著帕子仔仔細細的了貓爪子上的墨對連喻說。
“哪能呢,連尚書的貓金貴,奴家只是想幫它一,斷不敢欺負它的。”
連喻就不說話了,右手抬起來似乎是要往畫上描邊,抬起來了,卻又重重的放下了。是抿著,沾飽了墨的筆尖落在桌上,落下豆大一滴墨,他站起來一聲不響的扯著方婉之,直接將人關到了門外。
他實在有點煩,想圖個清靜。
可是沒過多久,方婉之就又回來了,不是從門外。門鎖著,進不來。所以翻了墻,半邊子掛在墻頭,笑的難看死了。
說閣老,您老別生氣啊,您看奴家哪里不順眼,奴家改還不行嗎?
一邊說著,還一邊對著他手。
“誒,您拉奴家一把呀,不然奴家摔死在您院里不是大白日的給您找晦氣嘛。”
Advertisement
連喻仰頭看著墻上沒皮沒臉的方婉之,突然覺得有些喪氣,因為自己好像拿一點辦法也沒有。
又是不算和諧的一天,方婉之又給連喻送東西了,是件價值不菲的西域緞子。被用手一團,扭扭的掛著笑,像是想裝出些樣子捧到他的近前。
“您老瞧瞧,可還喜歡?”
連喻連眼風都沒留下一個,徑直朝著京郊槐樹林溜達。
方婉之現在長能耐了,他不派車去接,便守在他下朝的路上來迎他。
灰頭土臉的蹲在道一角,還算顧忌著姑娘家的份,沒敢在人前臉。冷不丁從角落里扯住他的時候,險些被他一掌拍死。
也還好看清模樣之后沒有真的下手,方婉之要是死了,他還得再去找個會撒潑的婆娘跟他去赴宴。
今日早朝之后,劉禮過來找他了,熱洋溢的表達了必須請他們小兩口吃飯的意愿。神頗有些驕傲,因為放眼這些個拉幫結伙的皇子中,只有他親眼見過連喻的這個正妻。也想襯著這個機會,多拉攏一下他。因此態度上十分堅決,連喻待要推拒起來,自然就沒那麼容易了。
說到后來,也就未置可否的應了。
方婉之依舊沒完沒了的嘮叨。
連喻將領到一顆老槐樹下,盯著樹上的馬蜂窩壞心眼的思量著,到底要不要將這個東西捅下來將蟄個滿臉包。
方婉之遲早要嫁人,定然不能在劉禮面前真容。他可以理直氣壯的告訴,自己這麼做是為了的后半生考慮。不然將來被認出來,也是個不大不小的麻煩。
連喻這般想著,又為這點子認知不痛快了。
他覺得方婉之的子壞了。聒噪,呆傻,缺心肺,趣味極低。整日只喜歡打聽小道消息的人,嫁給誰都是個禍害。
Advertisement
再抬眼一看沖著自己一臉恭維的模樣,又默默加了一句,趨炎附勢。
他認為自己想的對極了,面上更加沒有好,手腕一轉甩出腰間的鞭子。
他告訴:“站在這里別,等下蜂來了,將你這張臉蟄的半人半鬼咱們就可以走了,我有藥。”
方婉之聽后笑容整個僵在了臉上,心說你有藥就趕自己吃了吧,你都已經病弱膏肓到可以駕鶴西去了。
當然不可能傻到站在那里被蟄,一面迅速挪到他跟前一面道。
“大人做什麼讓蜂蟄我?您要是想看大腫臉,奴家這就回家把奴家的爹拉過來,蜇我爹給您看怎麼樣?”
承認,自己對方正的一些做法很是反,父兩之間的分不多,唯一可值得念及的,也只剩下這二十年的飽飯之恩了。如果連喻要看,大概真的會把方正過來。
方婉之要‘蜇我爹’給連喻看,連閣老卻并沒有那個興致,淡眉淡眼的一挑眉。
“蟄他做什麼?我又不帶他去吃飯。”
方婉之這才知曉,這貨是迫不得已應了陳王的約。
兩人一起站在樹下守著那個馬蜂窩,最后當然也是沒有蜇,只是在去的時候讓皮皮找了一張算是清秀的鹿皮面在了臉上。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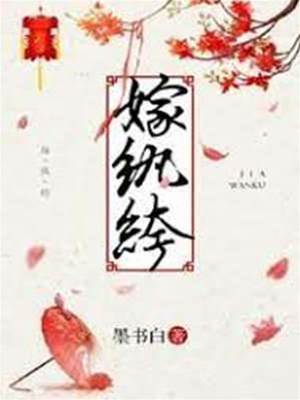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