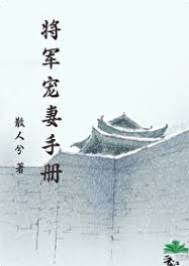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諸事皆宜百無禁忌》 第4章 忌重逢
秋欣然許多年前在學宮讀書時替夏修言看過一回面相。那時候清和公主還在,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梳著兩條羊角小髻,托著腮滿臉好奇地問:“欣然,你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一個人的命勢來?”
秋欣然搖搖頭,清和公主卻不信,湊近了附在耳朵旁邊悄悄問:“你看看夏世子的面相,他以后會怎麼樣?”
秋欣然順著的目朝東南角看過去,那是整間屋子最好的位置。夏修言弱多病,慣常就坐那里。不過雖然如此,他較這宮里其他的皇子還是白上許多,或許是因為他平日不上騎課。
大約察覺到了什麼,角落里的人從案前的書冊上抬起頭,正對上的目,微微挑眉。秋欣然定定看了他一會兒,才若無其事地轉開眼:“你問他干什麼?”
清和公主苦惱道:“前幾日,小令告訴我長大了想嫁給夏世子,可我看夏世子這麼弱,萬一等不到長大可怎麼辦?”
小公主一臉天真可,萬分嚴肅的替小姐妹憂慮著這個事,兩條細眉像是兩蟲擰在一起,秋欣然忍俊不:“那公主就勸勸韓小姐換個人喜歡。”
清和公主聞言大驚失,愈發張地湊近過來,憂慮道:“他……他當真是個短命的?”
“短不短命倒不好說,”秋欣然低著頭一筆一劃地在紙上寫字,“但看面相是個薄的。”
……
生得一副薄面相的定北侯如今站在湖邊,似笑非笑地問:“秋司辰別來無恙?”秋欣然總覺能從里頭聽出幾分憾來,一時不知答什麼能他覺得高興一些。
“一切都好,侯爺看起來也是大好了。”
“托司辰的福,”夏修言意有所指道,“帶病之軀可不能領兵。”
Advertisement
秋欣然干笑兩聲:“侯爺早年離京恐怕不知,我如今已不在司天監任職了。”
夏修言微微一頓,略帶譏諷:“圣上竟舍得放你出宮?”
他這話若傳出去可算大不敬,但他今時不同往日,想來宣德帝便是當真聽見了也多半哈哈一笑不會放在心上。秋欣然如今一介白自然也只裝作沒有聽見,只低頭看了眼腳邊的湖水,往前挪了一小步。
夏修言像察覺了的心思,頓了一頓,才古怪道:“道長這幾年的膽子倒是越發小了。”
秋欣然訕訕拱手道:“夜里風寒,貧道就不在這兒不打擾侯爺……”
話未說完,不遠花園的小徑上便出現了一個人影,黑黝黝的看不清模樣,但那一嗓子出來就能人聽出份:“侯爺,里頭找你哪!”
賀中今晚喝了不酒,醉倒是沒醉,但神已然是十分了。夏修言轉過,他才看清楚自己侯爺后還有個人,看裝束卻分不清男。若在平日,他就該識趣地退下了,但這會兒,顯然腦子還有些轉不過彎來,就那麼直愣愣地在原地又瞇了瞇眼仔細地往這兒看了看。
秋欣然忽然就想起他方才在席上同周顯已說得那番話來,不由得往夏修言后又站了站。賀中沒等到回應,以為自己離得遠了些,方才那話沒侯爺聽清,又往前走了幾步。
秋欣然見狀,不由得又往后退了兩步。夏修言正要開口同賀中說話,余見這兩步已站在了湖岸邊,眼皮微微一跳:“站住——”話音未落,后便傳來一聲驚呼以及接踵而來的“撲通”一聲落水聲。
秋欣然一腳踏空之前,看見背對著自己的人似乎折過來,手試圖拉一把。可惜今日穿得一窄袖胡服,眼睜睜看著那雙手著自己的袖口撈了個空,接著便絕地落進了二月冰水初融的春池里,濺起了好大一朵水花。
Advertisement
賀中夏修言那聲“站住”驚得定在原地,等湖邊的落水聲引來了四周的守衛才反應過來,侯爺方才那一聲并非是說給自己聽的。等反應過來,再趕到了湖邊,已有人跳下湖將水里的人撈了上來。
夏修言站在岸邊,瞧著被人撈上來的子,臉有些難看。對方頭上的發簪在落水掙扎中人打落了,如今頭發披散著粘在臉上,模樣著實有些狼狽。不過平日一貫束發,做道人打扮,如今散發倒是出些兒氣來。加之今日本就一窄袖胡服,落水之后,打的衫著子,勾勒出玲瓏態,人為之側目。
秋欣然坐在地上氣未勻,忽然兜頭蓋臉人扔了一件罩衫。等拉下服披在上,眼前已是里三層外三層的侍衛宮,簇擁著將送到偏殿換了裳。等灌了一碗姜湯,人服侍著休息后,竟也無人傳去前頭問話。
那晚之后的事,是后來從周顯已口中得知的。
彼時周大人坐在何記飯館二樓的雅室里,手捧著熱茶心有戚戚道:“本來好好的太后壽宴出了這種事,圣上是很不高興的。不過后來聽說是定北侯多喝了兩杯酒后失儀,這才沒有怪罪。”
秋欣然納悶道:“定北侯酒后失儀就可不怪罪嗎?”
周顯已瞥一眼,意味深長道:“當然不止如此。主要還是聽說落水的是你,圣上這才平息了怒氣,還你得空進宮面圣。”
秋欣然聞言心下不由生起幾分懷:“圣上仁慈。”
周顯已等慨完,捧著茶盞湊近了些低聲音道:“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同我說句實話?”秋欣然抬起頭,便見他一臉嚴肅地低聲問道:“那晚當真是定北侯將你推下水去的嗎?”
Advertisement
“……”
紫冠抬手了眉心:“宮中是怎麼說的?”
周顯已干笑道:“此事倒也怨不得宮里傳,畢竟一聽說落水的是你……”他手撓撓臉,迷道:“再者說那時候就你們倆個站在湖邊,你總不能好端端的自己掉進湖里吧?”
秋欣然不作聲,二人兩廂對,沉默許久:“當真不是他推的?”周顯已又忍不住確認了一遍。
“你什麼時候見他作弄人用過這麼顯眼的法子?”
周顯已無法否認,頗為同地著道:“那你好自為之吧。如今這樣,他恐怕更要記恨你。”
過了幾日,宮中果然來信傳召。
這一回秋欣然再坐車到了宮門前,守衛果真不再阻攔,只不過瞧著的目里掩不住的好奇。事實上不止是他,這一路上傳話的小太監走在前頭也要時不時地打量一眼。
秋欣然一路眼觀鼻鼻觀心,只做不知。一路到了上書房,等進殿才發現這殿除了皇帝竟還有一人——定北侯坐在一旁手里捧著清茶,聽見進殿的靜,連眼皮都未抬一下。
宣德帝與七年前相比老了許多,他命秋欣然起時也不由慨道:“朕還記得初見你時你還不過垂髫小,如今已有幾分仙家之姿了。”秋欣然也依樣回道:“數年不見,圣上卻還一如初見,俊朗不凡。”
宣德帝聞言笑了起來。秋欣然自認自己許多方面都并不像一個出家人,通都在詮釋一個“俗”字,與“雅”半點不沾邊。不過在求簽問卦上又確實有一些本事,這些都在京中那三年過得不錯。
如今也是一樣,宣德帝很快找回了當初與論經講道時的親切,不由多寒暄了幾句:“你后來回了山中,朕也同監正問起過你,景明說九宗的抱玉道人十分看重你,屬意你接過的缽,朕也不好強人所難。不過你這次回京可是改變主意了?”
Advertisement
秋欣然此時又端出一副嚴謹肅穆的模樣,恭聲道:“臣十年前京方知天下之大,此次也無久居長安的打算,只在市井中替尋常百姓看相,雖未仕于宮中,也愿以微末之力替圣上分憂。”
說完這句話,一旁一言未發的人目在上落了一秒,又很快移開。宣德帝欣道:“你能有此心,朕深安。”
宣德帝又過問了幾句這幾年山里清修的境況,終于進了主題:“前兩日聽聞你回京,朕還想著太后壽宴邀你宮,不想發生了意外。”
秋欣然立即正道:“擾了太后壽辰,臣罪該萬死。但此事與定北侯毫無關系,確實是臣一時不察,失足落水,臣愿領罰,還圣上明鑒。”邊說邊拱手長拜。
殿中靜了片刻,宣德帝失笑道:“那日的事,修言已與朕稟明了經過,今日找你來,不是為了此事。”
秋欣然拜服的手還沒收回去,不免有些尷尬。余瞥見一旁坐著的人似笑非笑地看了自己一眼,定了定神,才問道:“不知圣上召臣前來所為何事?”
“定北侯回京不久,如今住在邸總是不便。太后的意思是替他選個侯府,不過修言不大干戈,準備先找個府邸安置下來。正好你也頗通風水,此事給你最為穩妥。”
“這……”秋欣然遲疑道,“臣雖學過些相地之,但到底只是些皮而已,恐怕難當此大任。”
“欣然不必自謙,你有幾分本事朕最清楚不過。既不是選侯府,也不便驚禮部,主要還看修言自己的心意。”宣德帝說著轉頭去看一旁坐在側首的青年,和悅道:“所謂家立業,堂堂一個定北侯在京中連個住都沒有,哪家的貴愿意嫁你啊,是不是?”他說著笑起來,夏修言便也跟著笑了笑,起謝恩:“那就先謝過圣上恩典了。”
二人說著就將這事給定了下來,顯然沒有秋欣然再推拒的余地。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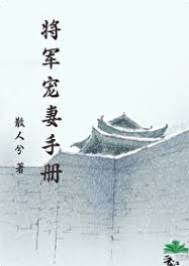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