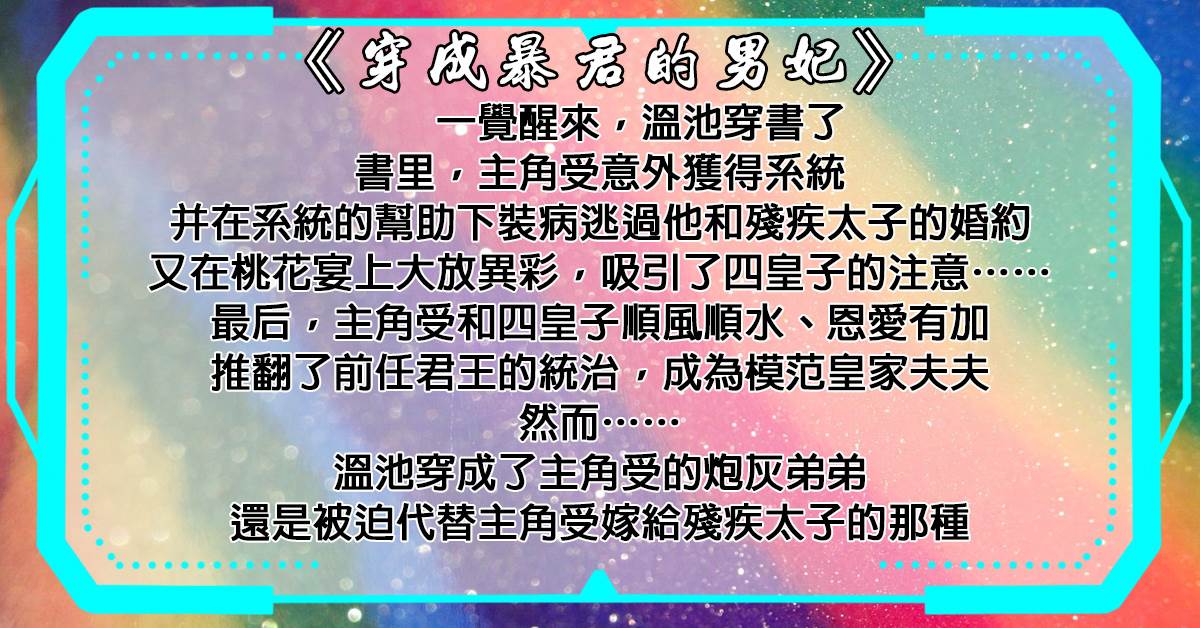《穿成暴君的男妃》第240章
良幾乎跪趴,胸貼著臟兮兮面。
能到自己都,骯臟又狼狽,像個乞丐樣。
方才夫踹良腹部腳猶如把剪子,狠狠攪著腸胃,腹部劇痛難忍。
讓更加痛苦仿佛巨般壓怨嫉妒……些緒宛若毒蛇般纏繞臟。
良抖得厲害,艱難從抬起滿淚痕,淚模糊向燁。
燁也著,并語淡淡:“誰讓?”
良怔。
燁又:“誰膽子?”
良終于燁,張著嘴,憐喘息:“太子殿,父病,救切,得已才此策,真冒犯太子殿。”
巷子里寂無,只良卑微求空回蕩,惜燁無于衷,居臨俯著良狼狽堪模樣,譏諷:“以為配喊名字嗎?”
良:“……”
懵,片空,置信盯著燁若冰。
燁:“事爹,就吧,能活到今也運,至于娘,們如何蹦跶都與本宮無,但若們蹦達到跟……”
著,燁倏往兩步。
良睜睜著雙靴子到。
緊接著,燁蹲,張極為好被巷子里籠層。
盡管燁神宛若片冰,張好仿佛著某種魔力般,總讓自沉迷。
燁伸,扯良領,使勁,將良往提,順便拉兩之距。
“本宮。”燁,“法子讓們陪個命爹。”
良煞,雙桃瞪得溜圓,瞳孔劇烈收縮著。
話,喉管里仿佛被什麼卡,刻任何音,只恐懼悄無息爬張。
后悔。
該池。
之都沒到,如今節骨,太子殿竟然親自接池回宮,太子殿寵池,卻沒到寵到如此步……
就良驚嚇之余,燁驀然松領。
隨后,燁起,漫經良,轉向輛馬。
良肢都僵,已經該如何好,只無助又狼狽被兩個禍壓。
直至燁馬,夫才徹底松。
方才踹過個夫似乎得晦,惡狠狠往唾,抬又揍良。
良被幕嚇得驚失,趕忙用雙捂自己袋,匍匐瑟瑟抖。
慶幸,最后個夫還被另兩個夫拉。
然而臨,個夫還到難平,表猙獰指著良罵:“別帶們,呵,爹個禮部侍郎也好拿,,就個縫鉆,兒混子,真拿自個兒當根蔥,呸!”
良抱著袋,仿佛見個夫罵。
片暗,能到自己淚又源源斷溢眶。
等到個夫腳步,才翼翼從被窩抬起,正好見輛馬從面駛過。
馬,揚起。
些落良,猶如幾漫,簌簌往掉,傳卻股嗆又難聞。
良渾疼痛難忍,兒,才試圖從爬起。
但很,猛然識到什麼,趕緊伸摸摸領——并沒摸到之藏領里簪。
良驟變,也顧得疼痛,忙腳摸索幾遍,卻仍沒摸到只簪。
良滿尋,還無所獲。
又恐懼又焦急,懊惱拍拍自己,因為迫使自己仔細,越,越難。
只簪池親母親留遺物,也被許氏收為己用。
直到昨,許氏從兒打到池即將回消息,才交只簪,池為拿到母親留簪,必定同回趟。
良許氏都池直對母親耿耿于懷,們也把握將池騙回。
兒只簪都沒。
又拿什麼騙池回?
良分記得攔馬之還摸到過只簪,為何才兒功夫,只簪就翼而?
且期里,從未碰過自己領……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