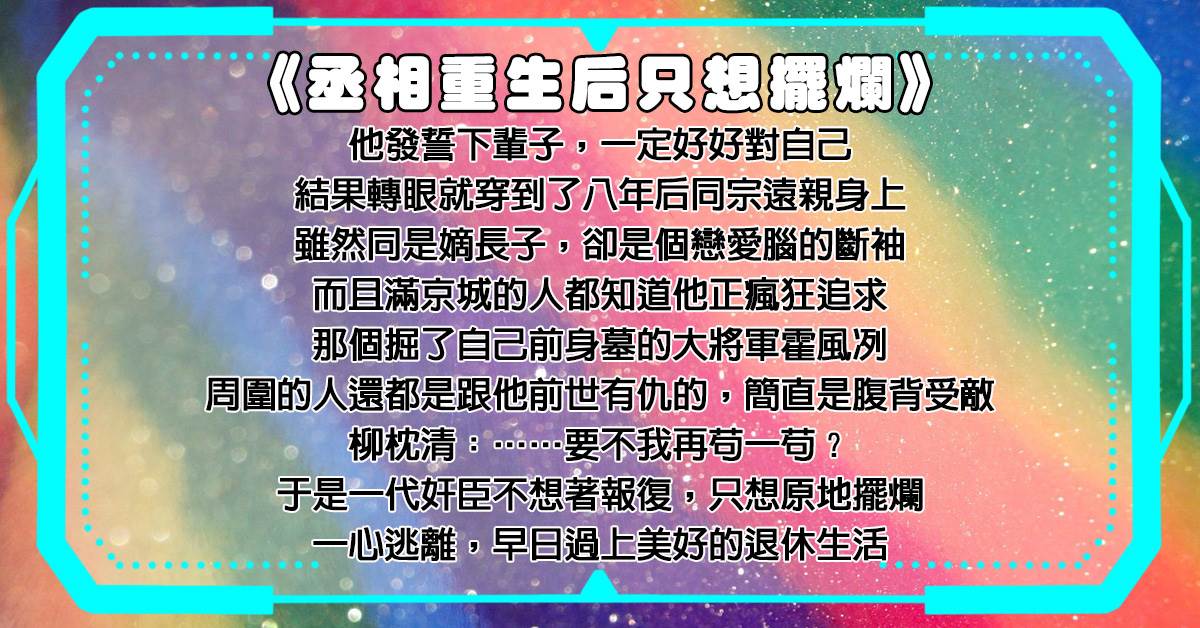《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第188章
過久,柳枕清自己背后都被汗浸濕,就到師父耐煩:“滾。”
仿佛每次被師父考驗,師父都自己瞎收個好好醫徒弟,叫囂著讓滾。
柳枕清每次都頑劣唉,麻溜逃。
次恭恭敬敬禮,轉,卻突然到后傳,“孽徒!”
柳枕清腳步頓,仿佛釘子般,再也。
到師父語幾乎切調呼喚,閉閉,終于還轉,兩步沖到榻,對著師父就跪,禮。
“師父,請受孽徒拜,師父……對起,枕清錯,枕清……錯。”里,柳枕清幾乎已經始哽咽。
被霍冽認,都至于讓如此失態。
世唯敬輩。
唯個能訓斥,能懲罰,能……當變得也得丟輩。
師父顫抖著榻,執百根針都穩,此刻卻顫顫巍巍挪到柳枕清頂拍幾。
“錯?還錯,……忤逆孝孽徒,……還打算認為師,連師都認叛逆!”
師父幾乎邊咬痛罵,邊撫柳枕清頂,用矛盾至極兩種緒宣泄著相認沖擊。
最終還如過般把擰著柳枕清朵,“臭子!就皮癢!”
濃稠愁緒瞬被沖淡,柳枕清熟練抓著師父腕,借力往站起,“啊呀呀,疼,疼,師父,疼啊!錯,錯,再也敢。
疼疼疼!”
著熟悉擠眉弄,子就跟以樣夸張演,讓對個成器徒弟狠,兒面對同面容,師父現自己還被演狠,只能松,吹胡子瞪。
柳枕清憐兮兮捂朵,“師父,老勁麼還麼啊!朵都被擰掉。”
“哼,誰讓話,擰掉!”師父完抬還教訓,反正見徒弟就癢。
柳枕清趕緊躲躲,就又見師父熟悉。
“師父,您。”柳枕清趕緊討好,扶著師父。
等師父之后,又陣,柳枕清也著,真啥好,只能:“師父,麼到……”
師父柳枕清,“對霍子般回應,種神態,老又瞎,再加默些,幾乎跟過弄些個系,相信世麼巧事。”
柳枕清師父邊討好錘肩膀:“倒相信神神鬼鬼事?”
“醫越,什麼奇跡見著。”
師父常常云游,事也見識廣,也許真很傳都真呢,所以師父比常更加能接受復。
“何?”師父問。
“個,柳蕭被綁架,就過。”
“若若呢?”
“……避師妹,沒讓。”
師父詭異,“連都,卻讓霍?”
柳枕清被師父神尷尬無比,“本就讓任何,只打算活遍,狗自己現。
”
師父到里,馬豎起眉毛,“回好事,為何讓們。”
柳枕清嘆:“愿相認,份等于個致命毒藥,誰若,誰就拿著個毒藥,又麼能害自己呢。若還活著,正名,幫些事,怕什麼都,到別更激烈反應,帶著樣枷鎖,過跟太,既然已經面對,各自都往,又何必此舉。個,論對,還對而言都分危險。讓再置于危險之。而且對師妹……終究還份愧疚,敢見。”
“子瞎什麼,若若麼麼!”師父即嚴厲反駁。
柳枕清著就笑:“徒兒累,再活世,就擺爛,啥也干,當個富貴閑,悠游自過子。也再面對過切。”
師父微微怔,終究還疼個徒弟,拍著:“現又干嘛?跟著霍到處冒險?還受傷?讓為師,傷麼樣。”
柳枕清敢讓師父自己肩膀,印還能模模糊糊能見呢,趕緊:“師父,怕最差徒弟,對自己還數呀。而且跟狗起,也……也因為柳分支被牽扯到麻煩,管也,被標莫須罪名,以后活得寧,得為自己清份證,所以才……”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