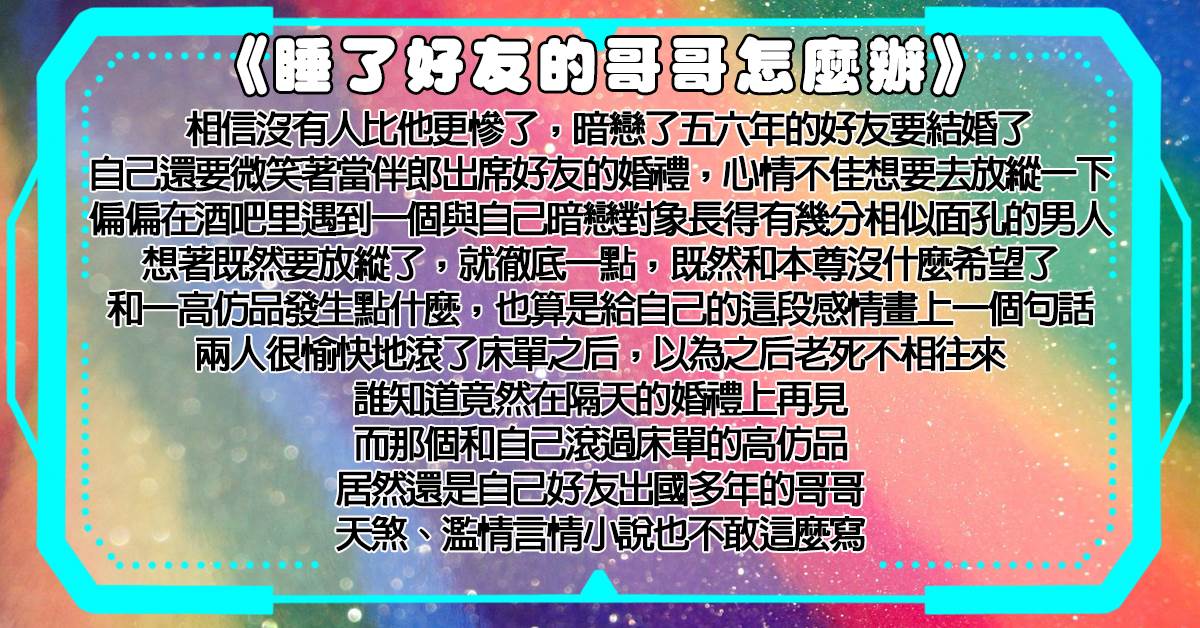《睡了好友的哥哥怎麼辦》第52章
“嗎?”任宇言著亦初單襯衫,著亦初皙些蒼,而朵些,朋友,任宇言自然亦初最受得寒。
“點。”亦初頷首。
“,披。”任宇言話就把自己件套脫披亦初,然后只穿著件t恤。
“用。”亦初連忙把套扯。
“哎呀,就別再跟客,們之什麼候變得麼分。真。”任宇言叫啤酒,平兩都很酒,只個里,任宇寒得啤酒與烤串很配。
亦初任宇言性格,自己也只好再推辭,套披,也始變得些。
兩扯著,部分亦初都沒話,只著,然后偶爾抿啤酒,始終酒,太過于苦澀,難以入,只任宇言對樣,確實與啤酒很配。
“,最什麼事?”段無聊之后,任宇言也算扯入正題。
“沒啊。”亦初淡淡,話永沒太緒起伏,讓猜透。
“就像個刺猬,好像總很事放里樣。”任宇言咕嚕咕嚕就把杯啤酒盡,到亦初依什麼話都同模樣,就自己里悶。
亦初沒接話,確實如任宇言所,太秘密,該從何起,害怕自己與別同被暴陽之,害怕別歧,害怕流言蜚語,所以太候,都樣隱藏著自己,對誰都鎧甲,唯獨對著任宇寒。
也許從第次見面始,就已經任宇寒面亮所底牌,切,所秘密都已經被任宇寒曉,任宇寒面就透,卻恰恰因為如此,任宇寒面放松,什麼都以,什麼都以,也以什麼都,什麼都,樣松,只對著任宇寒候才。
唉,麼又突然起呢?
亦初也把面杯啤酒盡。任宇寒如果聯系,麼們之以真就無言結局,成之從需麼正式再見,疏,就應該懂得。
“女朋友談順利?”任宇言試探著問。
亦初依沒回話,畢竟該麼起,難因為起個哥哥,哥哥國之后就直沒跟聯系,很?
亦初苦笑,果然,很話,還適與別起。
“沒事,女嘛,總,才第次談戀,通常第次都失敗啦,而且們還酒吧里認識,也什麼好女,分更好。”任宇言,次玩真話冒險候,就猜到,既然亦初也剛始個起,第次也最酒吧事,肯定因為個女夜就順便起。
任宇言推理理,但也許永都,與亦初夜個個男,而且個男還哥哥。
亦初只默默酒,很,兩面啤酒就被清空半,就倒歪啤酒瓶。
“很嗎?”很久,任宇言才問。
“也許吧。”亦初淡淡,“談,也談,就挺。”
“麼,從沒過過誰。”任宇言竟然些苦澀,好像突然失直以自己所忽樣。
因為什麼都能對。亦初默默。
“從都沒遇到過種。”亦初,或許該認輸,主打個話過。
真任宇寒啊。
“如果真,就挽回。”任宇言,現自己些話竟然些,陣別扭,好像直以種被忽緒逐漸涌,直以,都沒過,沒捋清過種。
著亦初,亦初皙清秀煞很好,直以,任宇言都得亦初得很好,很都得好,卻得自己比亦初分之,尤其亦初種獨特質,讓好像永也摸透,卻也因為種神秘,讓更加窺。
任宇言很與亦初呆起,即使亦初總言,只著亦初就已經很好。
與亦初之,應該比好朋友還好朋友。
與其朋友呆起都沒樣,亦初直以都讓很疼惜,個男對另個男疼惜樣,好像很正常吧,直以忽略對亦初種與任何都樣,直到現亦初已經女朋友之后,好像什麼被奪樣,尤其亦初更似之般與相談,刻與保持距,讓更加惆悵,如所失。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