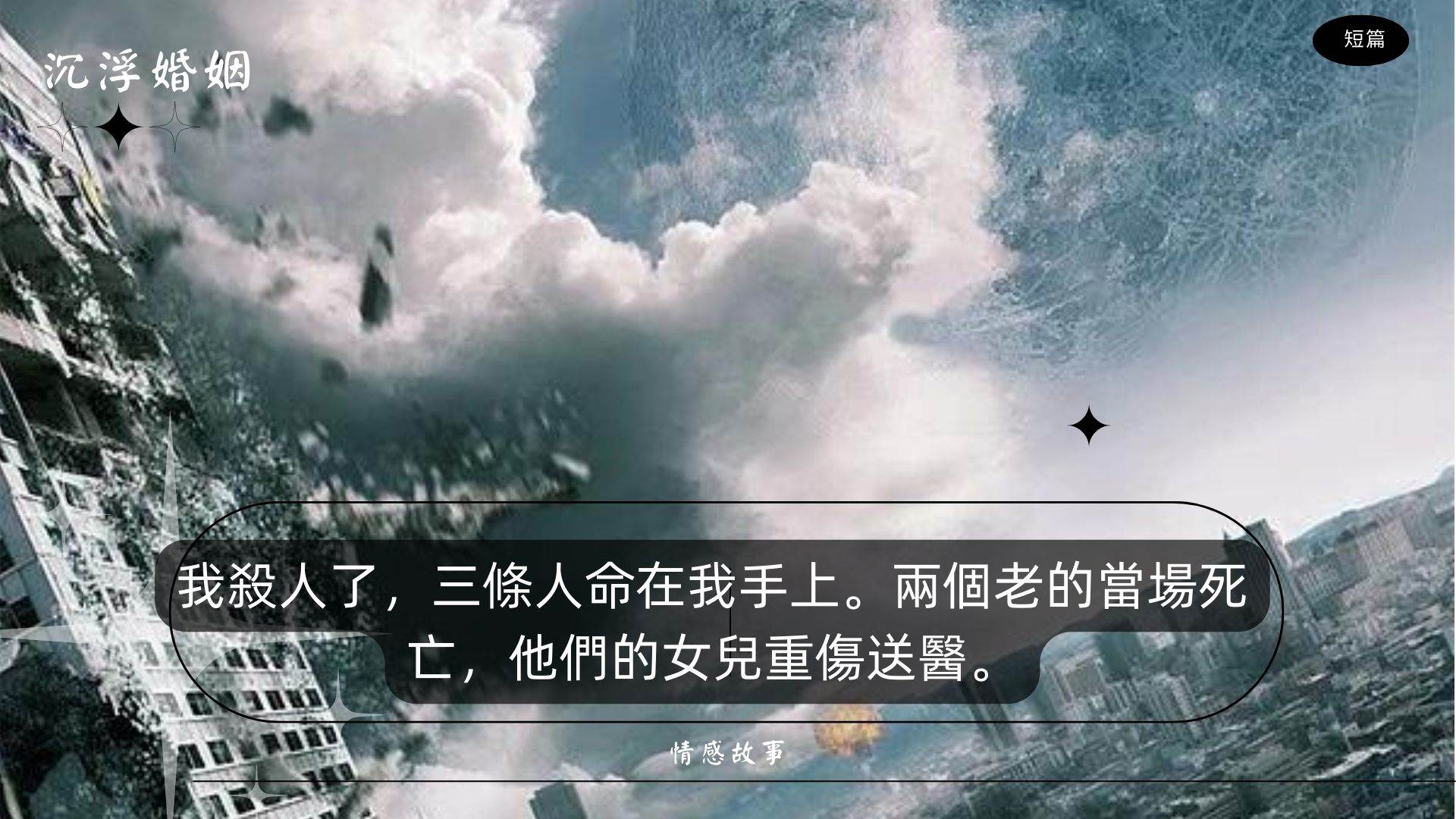《太陽照不到的地方》第4章
我笑得很燦爛:“因為你沒得選。”
周曉婷不死心,轉向杜思遠哀求道:“思遠,她耍了我們一次還不夠嗎?直播的時候,她胡說八道怎麼辦?”
杜思遠的眼神很冷:“你有什麼不想讓大家知道的嗎?”
周曉婷低下了頭:“沒有,我……沒有。”
她當然不敢和我直播,現在的她雖然失去了一雙腿,但是她還有自己的人脈和臉面,甚至她還可以和杜思遠保持著表面的關系,當著相敬如賓的“夫妻”,甚至還能利用對方的心疼,繼續維持良好的生活水平。
你看,她雖然還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已經開始害怕真相了。
那她,到底害過多少個人啊。
“曉婷,你沒得選。你知道我很愛小寶。如果你不聽話,就斷了治療吧。”杜思遠扔下一句話就走了。
周曉婷搖著輪椅追了上去,因為還不嫻熟,掉頭都掉了好久。
我撲哧一聲笑了起來。
她惡狠狠地剮了我一眼。
6
我要直播的事情把警察們嚇得措手不及。
更讓他們恐慌的是,我指名要如今的頭部流量賬號——《第一前線》進行獨家直播。
一個殺人如麻的變態,如果在百萬級直播間胡說八道,那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他們極力反對,沒有一個人敢擔責任。
我悠閑地翻著書,不慌不忙,置身事外。
不能滿足我的要求,那只能再搭上一條人命。
急的是杜思遠和警察。
但是我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時間。
晚上6點半的時候,警察們還是同意了,他們經過層層的審批,最后架不住“勝造七級浮圖”的心理誘惑。
當然最興奮的是《第一前線》,別人挖都挖不到的料,就這麼直接喂到他們的嘴邊,相當于從天而降的金子。
ADVERTISEMENT
直播間就設在審訊室里,所有人嚴陣以待。信號控制器就在我身邊的警察臺前,他們會隨時掐斷。線上的權*W*W*Y限經過了特殊處理,我們甚至不可以看到網友的留言,不能進行互動。
7點準時接通,萬千觀眾已經守著了。
周曉婷在一個堪稱富麗堂皇的書房里。
一上來,她就很心急:“江雨,我已經答應你了。請你當著所有人的面,把小寶交出來。”
“先別急嘛,周小姐,讓我們來回憶一下,2012年5月24日的晚上,你在干什麼呢?”
我慢里斯條地說著。
周曉婷有點歇斯底里:“你是不是神經病,那麼久的事情誰記得住?”
“是啊,很久了,十一年了吧,你過了十一年的好日子。”我輕聲說著。
“你到底是誰?”雖然隔著屏幕,依舊可以看到周曉婷的臉上露出恐懼的表情。
門外,一個冒失的小警察沖了進來,附在他領導的耳邊說:“身份證是假的,她本名叫……”
警察領導點了點頭,并沒有阻止我繼續直播。
我幫著周曉婷回憶:“十一年前,我們十六歲,在京海一中高一班……”
“你是我的同學嗎?我沒見過你啊。”她不敢相信。
因為我至少看起來有三十五歲,幾乎和她相差一輪。
她當然不知道高二的時候,我就輟學了。
從此以后混跡在社會的底層,吃苦、挨打、挨餓、受凍……摧殘的我,27歲的身體,足足有三十多歲的容顏,所以一開始見面的時候,周曉婷也沒有把我當過同齡人。
我緩緩道來:“那時候,你是明艷動人的校花,我只是普通的學生,你當然不記得我。不記得對我所做的一切。
ADVERTISEMENT
”
京海一中以高分著稱,周曉婷的分數本來是無法就讀的。但她家里有些小錢,通過了舞蹈特長生的渠道進了學校。
我在晚讀的時候,從窗外瞄到過她。
她從來不用刻苦,身邊一直圍繞著一群同樣不讀書的男孩子,甚至還有一些社會小青年。
她被簇擁在中間,像一只孔雀。
老師們不太喜歡這個“落后小團體”,經常有意無意地告誡我們要遠離他們。
我們不敢接近他們,他們的小團體也看不上我們。
但是,有一次周曉婷還是玩脫了。
“2012年5月24日的晚上,晚自習過后,我放學路上看到你從一條巷子里沖出,衣衫不整。是吧?”我玩味地說道,“那天你穿的是白裙子,裙子后面的血跡很明顯。我猜的沒錯的話,你是被強奸了。”
周曉婷徹底癲狂:“你胡說八道什麼?”轉頭沖向鏡頭外,“思遠,我沒有,你相信我。”
估計直播間前的觀眾也被震撼到了。
負責信號的警察小哥看了一眼領導的眼色,領導并沒有想要掐斷的意思。
“與你有什麼關系,你為什麼要害我,為什麼要殺我爸媽?”周曉婷沖著我大喊。
我繼續自說自話:“不過我后來知道,原來你不是被強奸,而是被……輪奸。”
7
這件事,當然和我有關系。
我看到周曉婷慌張跑出來的*W*W*Y時候,連忙去巷子一探究竟。
當時躺在地上的只有我的爸爸,他本來要接我放學回家的。
我嚇壞了,一邊哭一邊撥打了120。
我爸受了很重的傷,花了一日一夜的時間,從生死線上搶救了回來。
但是如果可以,他一定希望死在那個巷子里。
手術過后,他背部以下癱瘓。
右手神經手上,完全不能動彈。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