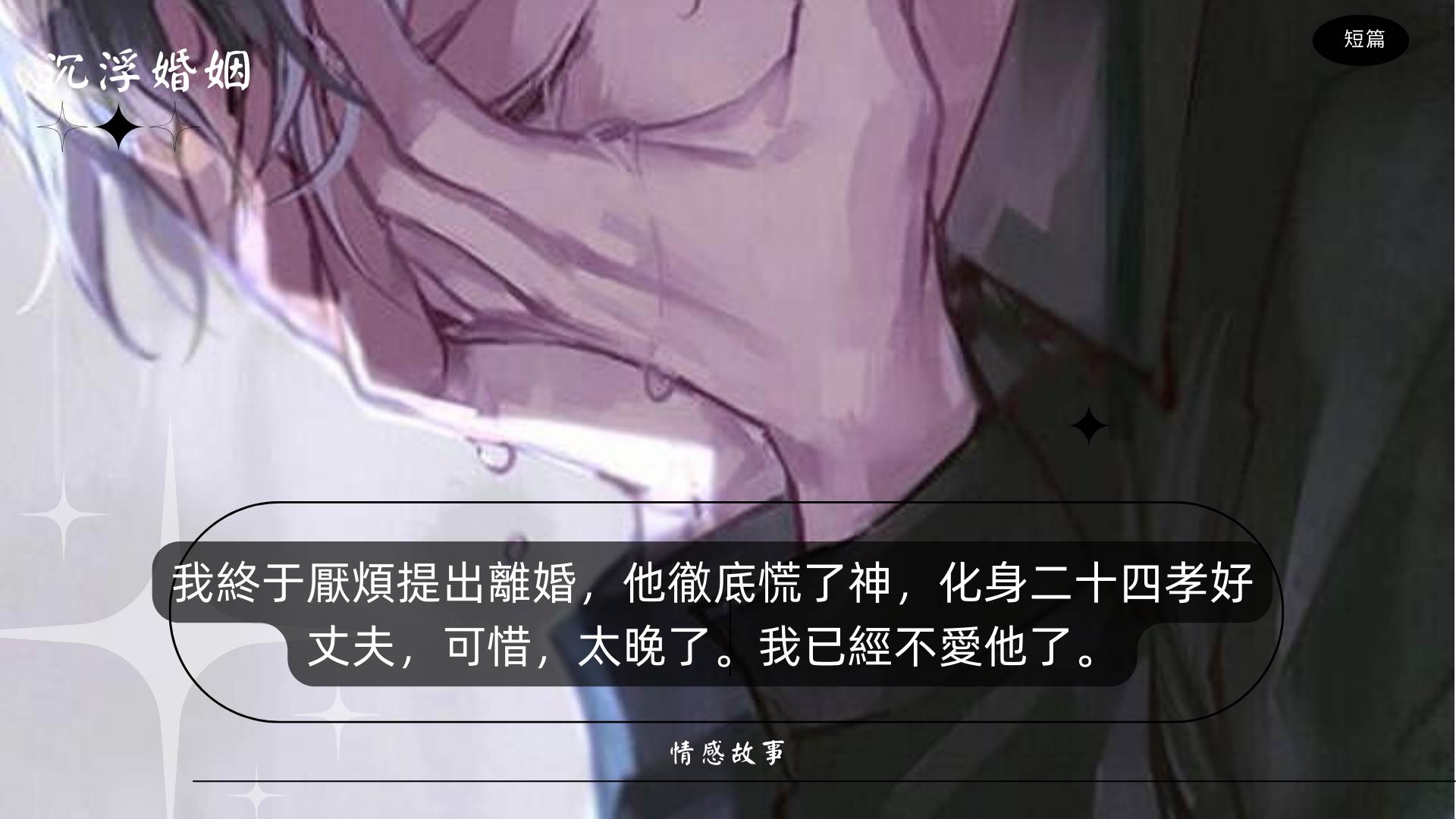《唇槍舌劍》第3章
他擰著眉,耐心消耗殆盡,語氣很沖,
【少廢話,我孩子要不了幾個月就要出生了,你這時候去祭拜死人不是晦氣嗎?!
蘇荷,都離婚了,你為什麼還是跟我找不快呢?!】
我再次表明立場,我可以走,但是必須等到我祭拜完母親。
周野怒了,一腳踹翻了我的茶幾,帶著幾分猙獰威脅道,
【蘇荷,你可別忘記了,你媽骨灰埋葬的墓地是我名下的產業。
你今晚不走,我不敢保證你媽的骨灰第二天還在不在里面!】
我怔怔的看著他堆滿怒火,仿佛恨不得掐死我的臉。
我深吸了口氣,忍著指尖的顫痛,轉身回房,一言不發的開始收拾東西,拉著行李往外走。
背后傳來他得逞后的調笑聲,
【蘇荷,你糾纏了我這麼久,我終于擺脫你了。】
我向前的步伐頓了頓,握著行李箱的手陡然用力抓緊。
隨后,繼續向前走,不再回頭。
這七年是我偷來的,我小心翼翼的珍惜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生怕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東西。
但在周野心里,這七年只是一道沉重的枷鎖。
4,
我走后,周野有了孩子,膩了流連花叢的生活,收了心,開始接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物。
聽說生母被他用錢打發走了。
我在澳洲分公司歷練了三年。
回國后,我祭拜完母親,回家里的公司任職。
我負責商談的第一單業務,森*晚*整*理對方公司項目負責人竟然是大學時期幫了我很多忙的學長,陳以深。
不知道周野抽什麼瘋,說不放心我一個人去談這單業務,偏要跟著我一起去。
ADVERTISEMENT
還威脅說,如果我表現不好,就到我爸那打小報告,說我不適合繼承家業。
于是,兩個人的飯局,變成了三個人。
飯桌上,我和學長故人重逢,相談甚歡,幾乎是把周野晾到一邊了。
陳以深長相斯文,氣質溫文爾雅,但又帶著幾分疏離的距離感,與周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型。
他給我點了杯檸檬水,笑得溫柔好看,
【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你的口味變了沒有?】𝚇ł
我將長發撩到耳后,扯出一抹淺笑,
【沒變,還是和以前一樣喜歡喝檸檬水。】
飯局從開始到結束,周野始終黑著一張臉,不知道還以為誰欠了他幾個億。
學長提出送我回去,被周野咬牙切齒的拒絕了。
他不管我穿著高跟鞋會崴到腳,拽著我的手,一個勁的往前沖,打開副駕駛的車門,直接把我丟了進去。
他坐到駕駛室,開始看著揉著紅腫手腕的我,陰沉著臉開始陰陽怪氣的諷刺我,
【到了澳洲三年,別的沒學會,倒是學會勾引男人了,嗯?!
我以前怎麼就沒發現,你還有這本事呢?!】
我氣得不行,恨不得當場掐死他。
我閉了閉眼,壓下弄死周野的沖動,極力保持平靜,偏過頭與他四目相對。
我嘴角扯出一抹不屑的笑,語氣輕佻中帶著揶揄,
【周野,你不會是在吃醋吧?】
斗了這麼多年,我太清楚怎麼逆風翻盤,迅速壓他一頭。𝙓|
果不其然,周野臉色難看的嚇人,周圍的氣壓都低了下來。
別人怕他,我可不怕。
我冷笑了一聲,打開門,想下車,卻被他壓在副駕駛上。
他的臉在我眼前放大,薄唇貼得很近,只要我稍微動一下就會親上去。
ADVERTISEMENT
他炙熱的呼吸帶著煙草味侵入鼻腔。
我難受的推了他一把,勒令他趕緊從我身上滾下去。
他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看著我,冷哼了一聲,
【吃醋?呵。】
他緩緩湊近的我唇,在毫厘之間停下。
我的大腦宕機了好幾秒,才反應過來。
我用盡全身力氣推開他。
他抽了張紙,擦了擦薄唇,看著我氣憤得恨不得殺了他的模樣,笑得愉悅,
【蘇荷,你剛才不會是在自作多情吧?】
5,
到了周家,我迅速從車上下來,黑著臉“嘭”的一聲關上車門,回到自己的房間。
我本想搬出去,但拗不過周母,就只能算了。
我忙完工作后,陳以深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看電影。
我稍微思考了一秒就同意了,我對他挺有好感,想繼續接觸一下。
我披上外套,推開門往外走。🗶ᒝ
沒走兩步路,就突然被人一把按在墻上。
周野一只手撐在墻上,低頭居高臨下的看著我,唇邊掛著冷笑,
【大晚上的不睡覺,是不是打算出去森*晚*整*理和野男人私會,嗯?】
他骨節分明的手,捏著我的下巴,逼迫我與他對視。
我用力的拍開他的手,譏諷道,
【我跟誰約會好像不關你的事吧,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嗎?】
他低低的笑了兩聲,黑沉的眸子卻死死的盯著我,語氣諷刺到了極點,
【你頂著周家養女的名頭,剛回國就急不可耐的找男人,丟周家的臉,本少爺還不能教訓你兩句?】
我簡直氣笑了,咬著牙,盯著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從牙縫里擠出來,
【對于丟周家臉這件事,所有人都能指責我,唯獨你沒有資格。
麻煩大少爺有點自知之明。】
說完,我不顧他難看到極點的臉色,猛的推開他,走了出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