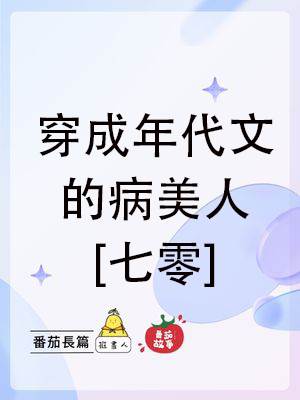《穿成年代文的病美人[七零]》第465章
雖然他們也去馬春花被扔的地方看過,也看到藏人的荊棘叢,只能判斷應該是小孩子所為。
這年頭沒有監控,小孩子又到處亂竄,到處都是他們的痕跡,要從這些痕跡判斷出哪個孩子做的還真是不行。
而且家屬院和部隊附近鄉里那麼多的孩子,總不可能一個個都找過去問吧?
最后,這事不了了之。
找不出人來,他們也沒辦法啊,總不能為了這事,要將家屬院及附近的孩子都聚集起來,就為了給馬春花討個公道吧?
部隊真沒這麼閑。
馬春花卻不肯接受這結果,憤怒極了,每天都在家里大罵。
“我不管,一定要將那些死小孩給我找出來,看我不打爛他們的屁股!我一定要讓他們付出代價,還有他們的家長,孩子都沒管好,生啥孩子啊,生出一堆爛**來禍害別人……”
馬政委回到家,聽到那尖利的罵聲,內容越發的粗俗,就像農村里的潑婦罵街一樣,又習慣性地頭疼。
以前他沒有頭疼這種毛病,就算是部隊里最令他覺得棘手的軍官單身的問題,也沒能讓他這麼頭疼。直到他娘和他妹來到部隊,和他們相處久了,他開始頭疼,最后身心疲憊起來。
就算對家人有再多的愧疚和容忍心,也在馬春花日復一日的鬧騰中消耗沒。
“春花,你這說的是啥話?”馬政委喝斥道。
馬春花朝他怒目而視,“敢情被扔**的不是你,你才能對我說風涼話!你還是我哥嘛?我咋會有這種不愛惜自己妹子的哥?”
說著她悲從中來,撲到床上號啕大哭。
ADVERTISEMENT
馬政委看她這樣子,臉色又開始發青。
這幾天,馬春花自覺沒臉見人,一直躲在家里,在家天天鬧、天天罵,有時候罵得極為難聽。
那嗓門尖利高亢,能傳一條街遠。
附近的鄰居都忍不住來找馬政委抗議,讓馬政委管管他妹子,這白天黑夜都在罵在號,他們剛睡下去,就被馬春花的聲音嚇醒,哪里能行?
馬大娘還是心疼女兒的,見兒子臉色不對,拉著他說:“老大,春花心里憋悶,一直找不到朝她扔臟東西的人,你就讓她出口氣吧。”
馬政委抹了把臉,“可她已經嚴重擾鄰了。”
馬大娘不悅,“他們還有沒有同情心了?春花是個年輕姑娘,遇到這種事心情不好,讓她罵兩句又咋啦?”
“……可也不能影響別人休息啊?”
“春花只在家里罵,又不出去罵,咋會影響別人?”馬大娘不以為然。
馬政委看著他媽,知道他媽和春花壓根兒沒有自己嗓門很大、很刺耳的自覺。這也不怪她們,鄉下人為了點雞毛蒜皮的事就能吵起來,往往誰的嗓門大,就能將別人的聲音壓下去,對她們來說是利器。
馬政委明白有時候,他媽是沒法溝通的,便不和她糾纏這事。
他走到床前,對趴在那里哭的馬春花說:“聽說溫營長回來了。”
馬春花的哭聲一頓,雖然還在哭,但小了許多,而且聽起來就假,更多的還是裝給他看的。
也對,這些日子,馬政委也算是知道自己這妹子是什麼樣的人。
雖然被人扔臟東西、找不出罪魁禍首讓她確實很憤怒生氣,但要說她不想活了什麼的,那完全是沒有的。
ADVERTISEMENT
其實她這麼鬧,更多的是想給他施壓,也讓家人對她更寬容,得到更多好處。
馬政委看得明白,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而他媽還高興地說:“真的?那溫營長回來啦,啥時候讓他們相親?憑咱們春花的條件,配那溫營長絕對使得。”
馬政委差點想問,他妹子有什麼條件?
但想到面前的是他媽,是他親妹子,馬政委還是將那話吞咽下來,說道:“讓春花別哭了,養好精神,等過幾天,我就安排他們相親。”
馬大娘皺眉,“為啥子要過幾天?明天不行嘛?”
她也很心急,想趕緊將好女婿扒給閨女,就怕出什麼意外,好女婿沒了。
在馬大娘心里,那溫營長確實是個非常好的對象,自從聽兒子說了溫營長的事,她還特地去部隊打聽過溫營長,真是越聽越滿意。
大院弟子出身,上過軍校,年輕有為,家世過人,長相不俗,簡直是為她的春花量身打造的一樣。
這樣的女婿她可不想放跑了。
馬春花的哭聲也已經很小,豎起耳朵聽。
同樣偷聽的還有趴在門口的三花,不過屋子里的三人正說著話,沒人注意到她。倒是二花有些疑惑地看著妹妹,不知道妹妹在干啥。
馬政委沒好聲氣地說:“這幾天,部隊要進山拉練呢,大家都忙,哪里有空?”
馬大娘不懂什麼叫拉練,很是失望地說:“那溫營長啥時候有空?”
“等他們從山里回來就有空了。”
“啥時候回來?”
“應該三天后吧。”
馬大娘道:“行,就等三天,剛好到時候春花的新衣服也做好了。”想到女兒這次去鎮上做新衣服遇到的事,她又說,“到時候我和春花一起去鎮里取衣服。
”
她氣勢洶洶的,這次她倒是要看看,是不是還有人再朝她女兒扔臟東西,要是有,她一定要將對方揪出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