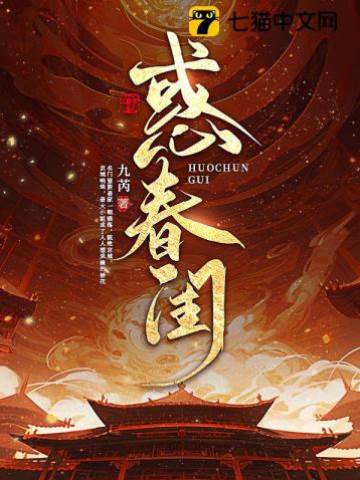《阿媛》 18.殺人
「阿媛。」
黑黢黢的屋子裏,一盞微弱的油燈下阿媛正在洗碗,聽到喊聲回頭:「胡姐,還沒有睡?」
胡姐走上前來,擼起袖子站在旁邊,主端了一盆洗過一遍的碗,道:「你來洗頭遍我來洗第二遍,這樣快點兒。」
「多謝胡姐。」阿媛激道。
胡姐一邊洗著一邊說:「你還小,要是做再時間長點兒你的腰也會不住的。」
「是,這樣彎著是難的。」阿媛抿一笑。
兩人通力合作,速度加快了不,不到半個時辰,幾大盆碗碟就乾乾淨淨地瀝好了。
「胡姐你先去睡,我把這幾盆水到去了就睡。」阿媛仗著自己力氣大,端著滿滿的一盆髒水就往外面走去。
「好。」
這個時候的軍營十分安靜,阿媛找了一條渠倒了水,一抬頭便看到了一清亮的明月懸掛在天邊,清極了。將水盆放在地上,展開雙臂仰頭了一個大大的懶腰,月灑在的臉蛋兒上,出瑩白的澤,讓人覺得秀麗俗。
這樣的月,這樣安靜的夜,倒是讓阿媛想到了在清水村的日子,安靜悠閑。
展了筋骨,彎腰端起盆往回走,轉頭的瞬間瞥到了對面站著的一個模糊的影子。腳下步伐一頓,思及鄒嬸的話,愈加匆匆地往前走去。
「那是誰?」對面,一個高大的影停住了腳步。
「回將軍,對面是伙房,應該是在裏面做工的人。」隨行的人說道。
軍營里的環境並不好,好多人睡一個大通鋪,什麼味道都有,複雜的。阿媛爬上自己的床鋪,掀開被子躺了下去,胡姐剛巧睡旁邊,兩人不約而同地往對方的方向移了移。
「胡姐。」阿媛低聲喊道。
「嗯?」
Advertisement
「我能問一件事嗎?」
「你問。」
「之前你們說的那個滿都是心眼兒的人……也在這裏做過工嗎?」
胡姐閉著眼道:「沒錯,就睡在你這個位置。」
阿媛:「……」
「長得不錯又會來事兒,現在過好日子去了。」
「哦……」阿媛可不相信這裏的「好日子」是褒義詞。
果然,胡姐睜開眼轉頭看,「你就不問怎麼過上好日子的?」
「應該是嫁人了吧。」
「嗯,嫁人了。現在是大將軍的妾侍,聽說還十分寵。」
阿媛愣了一下:「大將軍?」
胡姐冷笑了一聲:「說起來,大將軍的歲數都可以當爹了,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生齣兒子!」
阿媛:「……」難得胡姐說出如此刁鑽刻薄的話,不知那位是如何得罪了。
空氣靜止了下來,阿媛往被子裏了,雖然知道這一定是個很不錯的睡前故事,但卻不敢再問下去。
第二天一起來,阿媛才剛剛將面好,鄒嬸便從外面進來了,眼神複雜的看了一眼阿媛,道:「你出來。」
阿媛不知所然,洗了洗手,跟著走了出去。
「你昨晚去哪兒了?」鄒嬸的臉有些臭的問道。
「……在屋子裏洗碗,洗完了就回去睡了。」阿媛被問得更愣了。
「沒去哪裏?」
「沒有。」阿媛搖頭。
鄒嬸臉愈加黑了起來,道:「行了,金大人找你,趕去吧。」
「找我?」阿媛錯愕。
鄒嬸不再看,手一招,一個士兵跑了過來,鄒嬸指著阿媛道:「就是,領去吧。」
阿媛有些慌張,拽住鄒嬸的袖子:「嬸子,怎麼回事?要帶我去哪裏啊?」
「去哪裏?去過好日子去!」鄒嬸沒好氣地瞪了一眼,撇開的手,轉離開。
Advertisement
「鄒嬸!」阿媛上前兩步,想跟上去,現在對「好日子」三個字實在是恐慌,想搞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金大人」要找,為什麼一貫對還不錯的鄒嬸會突然對黑臉。
誰知才往前走了兩步,一旁侯著的士兵就握著兵上前攔住:「阿圓姑娘,這邊走吧。」
阿媛本想不理他,但看著他手中的刀,有些發怵。
識時務者為俊傑,實在不夠格嗆聲,只好跟著他離開伙房。
雖然來了大半個月了,但軍營並不是可以隨意走的地方,除了后廚阿媛還沒有走出來過。不知道前面的人要將帶去哪兒,拐了幾道彎之後,阿媛就徹底分不清東南西北了。
「裏面請。」士兵在前面停下腳步,讓出了門口的通道。
阿媛遲疑在原地,四周雕廊畫棟,彷彿是書上才有的房子。不知為何要將帶到這裏來,心裏湧上了一害怕的緒。
「請。」士兵大聲地催促了一聲。
阿媛被嚇了一跳,哆嗦著往裏面走去。
「砰——」
大門被關上,阿媛一下子回頭,聽到了落鎖的聲音。
「你幹什麼!為什麼要將我關在這裏!」阿媛撲了上去。
「安心待著,一會兒你就知道了。」士兵將大鎖合上,出鑰匙離開。
不知為何,突然想到昨晚的那道影,那種無法讓人忽視的氣場和被盯上的覺,讓從心底開始發寒。
好日子……
真會有那麼好?
阿媛被關在這間屋子裏很久,一直到晚上都沒有人出現,坐在椅子上抱著雙膝,腳底下是一地剝落的果皮。了自己的肚子,覺得有些難。
左右環視,看到了簾帳後面的床,十分生地又將頭轉了回來。
突然,外面有腳步聲傳來,一下子跳了起來,輕手輕腳地走到門邊。
Advertisement
「將軍,就是這間屋子。」
「怎麼鎖門了?」
「屬下是擔心會逃跑。」
「嗯,做得不錯,下去吧。」
聽到鑰匙/鎖頭的聲音,阿媛飛快轉坐回椅子上,順便將果皮踹到桌子下面,用桌布擋住。
「吱呀——」
一個高大的影走了進來,不聲地環視了屋子一周,自然看到了那空空如也的果盤,角微微一勾:「胃口不錯。」
阿媛站了起來,一臉警惕防備。
說起來,這個影子,倒是和昨晚瞥見的一模一樣。
男人走上前來,手想要的臉,飛快地躲開,一臉防備地轉到了椅子後面。
「別誤會,你只是長得很像我一個故人。」中年男人輕笑道。
阿媛的腦子飛快地思索著……這人大約四十歲左右,形高大,一的果決殺伐的氣息,加之住在這樣的院子裏,除了那個喜歡納人為妾的大將軍,不做他想。
可問題來了,就這樣的長相也能大將軍的眼?
「張什麼,坐。」大將軍退後一步,坐回了對面的椅子上。
阿媛杵在原地,掐著自己的手心,吸了一口氣,端端正正地給他行了一個大禮:「民拜見將軍。」
對面的人眉一挑:「你怎麼知曉我的份?」
「民妄自揣測,若有失禮之,還將軍海涵。」阿媛跪在原地不敢起。
半晌,一道影子落在了的前,阿媛盯著那雙黑的靴子一不。
「起吧,年紀不小,規矩多。」
阿媛只有撐住地面手臂才不會發,巍巍地起,巨大的力讓全都猶如針扎,幾乎抬不起頭。
「你長得不錯,人也機靈,怎麼就是有小家子氣?」大將軍輕笑,笑聲有幾分爽朗。
「民確實上不得枱面,平時只能在後廚幫忙做些事,若是將軍沒有吩咐,民要回去做事了……」阿媛往後退了一步。
Advertisement
「你既了本將軍的眼,便可以不用再回那種地方去了。」他輕輕一笑,抬手勾起了的下,湊上前去看的眼睛,「昨晚就是這雙眼睛吸引了我,我得仔細看看……」
阿媛僵在原地,拳頭差點兒出水。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熱熱的落在了的臉頰,一瞬間,滿臉通紅。
見「害」,他正調侃兩句,卻看雙目含淚,一副被欺負得不敢說話的模樣。
「你……為何做這樣的姿態?」男人的慾在蘇醒,這樣弱無骨的樣子正是他們所想要的樣子,他們不會手下留,反而會吹起進攻的號角。
果然,阿媛被他一個橫抱抱在懷裏,他帶著往剛剛看見的那張大床走去。
「別怕,我會輕輕的……」他低頭,緩緩解開的帶。
阿媛撇開臉頰,出了瑩白修長的脖子。
比起兩年前,阿媛確實長開了許多,量也高了,五也更清晰立了,以前一團孩子氣漸漸褪去,反而是出了一些的態。
「唔……」他埋頭,吻上了的脖子。
背對著他的上方,一隻握著銀簪的胳膊悄悄抬起……
「刺啦——」
「唔!」
兩道聲音同時響起,前者是他扯開襟的破碎聲,後者是銀簪刺他脖子的悶哼聲。
一瞬間,他眼底的/褪去,單手掐住了下人的脖子,他的手掌寬大有力,平時拉的都是幾百石的弓,掐斷一個人的脖子真是易如反掌的事。
阿媛的臉漲得通紅,手住他的手往下扯,結果卻是分毫未。腔里的空氣越來越,脖子更像是被人生生拉長了一截,鼻翼極速扇,眼球凸出,似乎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覺得漫長的像是幾百年的時間,卻只是幾息的功夫,掐著他的手掌漸漸鬆了力氣,巨大的軀倒在了的上,被刺中的傷口源源不斷地開始流,幾乎染紅了整個床鋪。
這一招曾用在何瘤子的上,他逃過一劫。與那次不同,這回卻是下了狠手,直接刺中了大脈。
呼吸重新灌了腔,倒在床鋪上一不,彷彿也跟上的人一般死去了似的。
殺了何瘤子,僅僅是殺人,殺了大將軍……無法想像自己該怎樣逃出這層層包圍的軍營,如何亡命天涯。
猜你喜歡
-
完結2204 章

退親後,我嫁給了渣男他叔
九皇叔,他們說我醜得驚天動地配不上你。 揍他! 九皇叔,他們說我行為粗魯不懂禮儀還食量驚人。 吃他家大米了嗎? 九皇叔,她們羨慕我妒忌我還想殺了我。 九王爺一怒為紅顏:本王的女人,誰敢動! ——一不小心入了九皇叔懷,不想,從此開掛,攀上人生巔峰!
326.9萬字8.18 116114 -
完結1946 章

農女雙雙的種田悠閒生活
老穆家人人欺負的傻子穆雙雙,突然有一天變了個樣!人不傻了,被人欺負也懂得還手了,潑在她身上的臟水,一點點的被還了回去。曾經有名的傻女人,突然變靈光了,變好看了,變有錢了,身邊還多了個人人羨慕的好相公,從此過上了悠閒自在的好日子!
341萬字8 118440 -
完結115 章

和清冷權臣共夢,嬌嬌臉紅心跳
【甜寵 雙潔】薑四姑娘年幼便喪失雙親,常年躲在薑家的內宅裏從未見過人,及笄後還傳出相貌醜陋膽小如鼠的名聲,引得未婚夫來退親。隻是退親那天,來的並不是她未婚夫,而是未婚夫的小叔,更是她夜夜入夢的男人。薑芙有個秘密,從及笄後她每晚就夢到一個男人,那男人清冷淩厲,一雙鐵掌掐住她的腰,似要將她揉進懷裏......後來未婚夫退親,京城眾人譏諷於她,也是這個男人將她寵上天。---蕭荊性子清冷寡欲,年紀輕輕就掌管金吾衛,是京城貴女心中的最佳夫婿,隻是無人能近其身,更不知蕭荊早就心折夢中神女。夢裏乖順嬌媚的小姑娘,現實中極怕他,每每見了他都要躲開。可她越是怕,他就越想欺負她。“你夜夜夢到我,還想嫁給旁人?”又名:春/夢對象是未婚夫小叔
20.9萬字8.23 33958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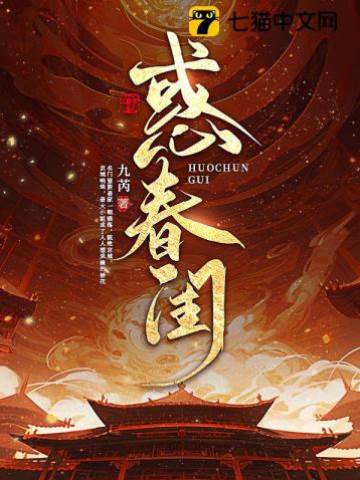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