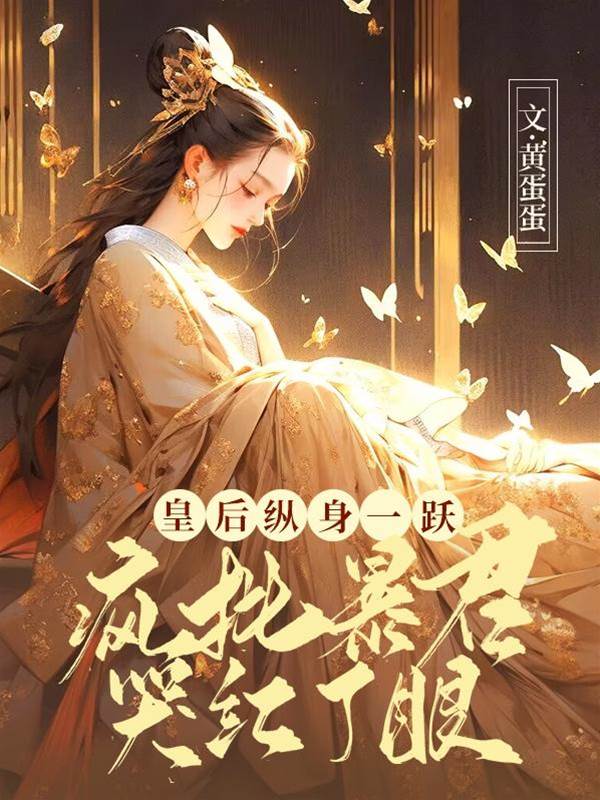《締婚》 第22章 第 22 章
關於某世族查了宗婦賬的事,項寓最初聽到只覺荒唐的不行,但越想越覺得哪裏不太對勁,恰得知寫這則事的人,家住附近,乾脆約了他來寺廟見面。
他走之前倒是不忘囑咐項寧,「你這裏等長姐,別跑記住了嗎?」
項寧乖巧地點頭,點了頭又想起自己是姐姐他是弟弟,怎麼又了被他叮囑了?
要扳回一點來,不想年腳下像踩了風火,人已不見了。
項寧嘆氣。
......
項寓算著長姐可能快到了,他最好在長姐到之前,去同那學子見上一面。
只是他還沒走到安螺寺後門口,差點與一人撞上。
那人一眼見了他愣了一下,然後飛快地眨了幾下眼睛,將他認了出來。
「寓哥兒,是不是你?」
譚建勉強到了山腳下,就連忙尋借口逃離了他哥,道是去從後山過去,替他們采些松林里的新雪泡茶喝。
這般好歹才能在他哥的威下口氣。
可巧就遇到了悉的面孔。
譚建曉得項寓和項寧搬到了青舟縣住,只是他卻從未見過項寓和項寧登過譚家的門。
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問過大嫂要不要請他們過來一起過節,大嫂都是說不用,說項寓學業張,還是留在書院附近好。
在項寓的勤里,譚建只能頭。
但這不妨礙他對項寓頗多好,至兩人年歲相差不大,都是還沒有參加鄉試。
他興緻頗高地走上前去。
不想項寓向一旁避開兩步,皺眉看了他一眼。
「譚二爺,有何見教?」
這口氣有點不對,但譚建卻發現他也認出了自己,越發高興起來。
「咱們之間何須有什麼客套?」
他又向前捋了捋關係,笑著道,「你是大嫂的兄弟,我也是大嫂的兄弟,咱們不就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嗎?」
Advertisement
「兄弟見面客氣什麼?」說著,手要拍項寓的肩膀。
不想項寓忽的一個閃,他手下尷尬落空。
他看向項寓,只聽項寓怪氣十足地來了一句。
「不敢當。譚二爺是譚氏宗房的二爺,項某隻是山野小民一個,怎能與二爺稱兄道弟?」
這下,譚建終於聽出不對勁來了,再看項寓神,橫眉冷眼彷彿跟他有仇一樣。
譚建不敢說話了。
他原本想著大嫂那般平和溫的子,弟弟約莫也差不多......怎麼差別這麼大啊?
恰在此時,有人找了過來。
來人不是旁人,正是項寓約在後山見面的人。
「二位是青舟書院的學子嗎?」
譚建搖了搖頭,項寓走上了前去,直接問了來人。
「在下項寓,閣下可是與我約好來此的?」
那人一聽,連忙道是,項寓甚是客氣,同人家正經行了一禮。
只是譚建在旁看著,才發現原來項寓禮數周道得很,只不過跟他不想有禮罷了。
這又是為什麼......
眼見著項寓同此人聊上了,譚建尷尬地準備走了。
不想正在此時,項寓問了那人一個問題。
「兄臺信中所說的,某世家以為宗婦手腳不凈、查了宗婦的賬的事,不知到底是哪一家?」
原本他在信中也問了,但那人說不清楚,只是從舅父聽來的,要先找舅父問明白。
當下項寓問了,沒等到那人回應,反倒先見著一旁的譚家二爺平地踉蹌了一步。
項寓奇怪地看了譚建一眼。
譚建聽著自己撲通跳的小心肝,莫名有種大難臨頭之。
他突然有點明白為何項寓對他全無待見之了。
他乾咽了口吐沫,正說想走,那人開了口。
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吉祥印鋪姜掌柜的外甥符耀。
Advertisement
他昨日剛回到清崡縣城去問了自家舅父,只是不知怎麼,舅父口風的很,讓他不要再問。
當下符耀道,「抱歉啊項兄,舅父說什麼都不肯告訴我,興許是那世家過於勢大了吧。」
一聽過於勢大,項寓皺了皺眉。
一旁的譚建冷汗都下來了,他都不敢同項寓再說什麼了,悄悄轉準備離開。
項寓沒過多理會他,只是問符耀,「不知符兄舅父是哪裏人?做什麼營生?」
符耀直接告訴了他。
「家舅父就住在清崡縣城,開了家印鋪喚作吉祥印鋪。」
這符耀還想告訴項寓,下次給自己寄信,可以直接寄到他舅父的印鋪里,只是話還沒說,見項寓突然瞪大了眼睛。
「姜掌柜?!」
符耀訝然,「項兄知道?那正是家舅父。」
話音落地,項寓眼睛陡然紅了起來。
姜掌柜知道且不便說明的事,還能是哪家的事?
而再回想符耀寫的那則事,都和自家長姐的境切!
他看向開溜的譚家二爺,突然兩步上前,死死地盯住了譚建。
「你告訴我,這事是不是你們譚家做的?!」
事實在前,本由不得譚建否認。
譚建冷汗都冒出來了,想要讓項寓冷靜、息怒,又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口。
而項寓一想到那麼多譚家的人,圍困著他長姐要查的賬目,沒有人給撐腰替說話,只有一個人獨自靠著自己的清白支撐。
他只覺得自己氣翻湧得厲害。
他一副眼睛發紅的樣子,譚建嚇壞了。
「寓哥兒你、你冷靜啊......」
「冷靜?你們譚家這樣折辱、欺凌我長姐,你讓我怎麼冷靜?!」
譚建抖不已,一旁的符耀總算看明白了。
那位被欺負的宗婦,竟就是項寓的長姐!
Advertisement
此時,從旁傳來幾個小沙彌急促的話語聲。
「......說是譚家大爺親自帶著譚家眷過來了,主持讓咱們趕快去迎接!」
小沙彌說完就跑去前院了。
而項寓在這句話里,也聽到了關鍵的字眼——譚家大爺。
原來這位譚大人也來了啊......
他當即棄了譚建,直奔前院而去。
他去得極快,腳下捲起一陣旋風。
譚建還沒及鬆口氣,就意識到了什麼。
「寓哥兒,你要做什麼呀?!」
話音未落,項寓已經不見了影。
......
安螺寺每年最大的一筆香油錢的來源,就是清崡譚家。
之前主持接到譚家的消息時,已經有所準備了,當下見譚家的宗子大爺親自來了,驚訝不已。
往年譚家並沒大辦那位項氏夫人生母祭奠的事,他雖然也會著人行方便,但是項氏夫人姐弟要求極,只是齋戒點燈,他也不好說什麼。
但這次不一樣了。
主持很有眼力地見項宜和楊蓁去了不遠的古松下,才在大殿外廊下拐角,低聲同譚廷道。
「譚大人放心,七天的獨姓水路都為項氏夫人的亡母空出來了,屆時由老衲同項氏夫人提及,只道是佛緣饋贈。」
主持把話說這般清楚,也是想同這位譚家宗子再確定一下。
畢竟這事聽起來,實在匪夷所思。
譚廷點了點頭,目在不遠的古松下微停,見正側著頭同楊蓁說話,才道。
「嗯,只要不提是我的意思,便是了。」
他話音未落,一陣猛烈的旋風從拐角的另一邊席捲了過來。
年的怒喝聲直衝譚廷耳中。
「用不著你可憐我們!」
譚廷轉頭看去,看到了項寓怒不可遏的臉,聽見他咬著牙道。
「你們譚家是高貴的世家大族,我姐姐在你們眼裏從來都是卑賤的庶族,所以就算是宗婦,你們也可以隨便查的賬,完全不顧的面質疑!」
Advertisement
項寓冷笑連連,「既是瞧不上,這會兒又來假惺惺地出什麼錢?以為我們卑賤,就可以拿錢讓我們低頭嗎?!」
他怒到了極點,盛怒的質問之後,整個安螺寺一瞬間靜得連鳥鳴都沒有了。
從後面追過來的譚建,整個人都僵住了,甚至不敢上前去看自己大哥的眼神。
譚廷神僵了僵,但在這質問之中,沒有出聲辯解。
只是他沒有認為他們卑賤,也沒有想用錢讓他們低頭的意思,他下意識轉頭向後看去,見項宜已經快步趕了過來。
項宜起初在譚家大爺提出來送他們過來時,便覺得有些不好,想著弟弟的子,生怕他同譚廷起了衝突。
上次他們遇上,已經讓事後知道的項宜后怕了。
之前弟弟試,有人使壞還能被譚家的而名聲住,但到了鄉試,名聲就未必有用了,他們可能需要譚廷出手相幫。
項宜一直不願項寓和譚廷鬧僵,就是出於這層考量。
可萬萬沒想到,項寓竟然知道了查賬的事,又正好撞上了譚廷。
著急地跑上了前來。
譚廷看見,莫名地心下了,他只怕也似項寓那般想,剛要說什麼,就見一把拉開了項寓。
「寓哥兒,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項寓看見了自己的長姐,想到自己還讓項寧在信里寫了那樁「趣聞」,而長姐的回信里一分表示都沒有,完全沒出來一個字,那個被誣陷的宗婦就是。
他簡直不敢想像那時是怎樣的心?!
項寓嗓音都抖了起來,「姐,他們譚家欺人太......」
「好了,不要說了!」
項宜一貫無甚緒的臉沉到了極點。
的反應出乎了譚廷的意料。
下一息,譚廷看見轉過來,同他深深行了一禮。
「項寓年,不懂分寸,大爺大人大量,不要與他小孩子一般見識,妾替他給大爺賠罪了。」
素白的衫下,青白的臉上,半垂下的眼眸帶著濃重的憂慮。
可他並沒有責怪項寓的意思,這事本就是他的錯,是他對不住。
不該向他道歉的……
高大殿堂下的檐鈴紋不。
譚廷在凝滯了的空氣中,目落在低頭同他道歉的妻子上,心口莫名悶到發慌。
他抿沉默,手去扶,可又在他到的一瞬,不著痕跡地退開了。
譚廷心口發悶到了極點。
他之前一直沒找到同道歉的機會,而似乎也無意聽到這些,有些話在心裏一直沒說。
但如今他曉得,這些話該從他口中說出來的,不管聽不聽,他都該說出來。
「你不用替寓哥兒道歉,寓哥兒說這些都是應該。此事本就是譚家的不是,更是我的不是。」
他微頓,看住了,「讓你委屈了。」
他這句徘徊在心口多時的話,終於說出了口。
只是項宜卻在這致歉里,不由地抬頭看了他一眼。
譚廷知道約莫又沒想到,只是項寓在這時卻冷哼一聲,「然後呢?」
他問了,譚廷目越發定在上。
他想補償,只是怕不肯要......
項寓像是讀懂了他的想法一般,又是一聲冷哼,「我們項家雖窮,卻也不缺你們譚家這兩個錢!」
「項寓!」住項寓。
譚廷在這姐弟二人各異的神中,默了默,他口氣坦然。
「寓哥兒想要我如何做,只管說便是。」
項寓聽了,恨不能回答他「請譚家大爺立時與我姐和離」,可在長姐嚴厲的神里,只恨聲吐了一句。
「明日,我要帶我姐回項家!」
猜你喜歡
-
完結1021 章

華帳暖,皇上隆恩浩蕩
大計第一步,首先得找個結實的金大腿,可沒曾想抱錯了,紮臉,可否重抱? 隻是為何她重新抱誰,誰就倒了八輩子血黴?不是傾家蕩產,就是滿門抄斬? 好吧,她認,就算三王府是龍潭虎穴,她入,反正她有二寶。 一,讀心術,雖然,此術獨獨對卞驚寒失靈。 二,縮骨術,雖然,此術讓本是成人的她看起來像個小孩。 在三王府眾人的眼裡,他們的王爺卞驚寒也有二寶。 一,豎著走的聶絃音。 二,橫著走的聶絃音。 有人問聶絃音,三王爺對你如此好,你要怎麼報答他? 聶絃音想了想,認真說道:「我會把他當成我親爹一樣侍奉!」 直到那一日,有人當著他的麵,跟她說,等她長大了娶她,她點頭如搗蒜,卞驚寒便徹底撕破了臉,也撕了她的衣。 她哭得驚天動地:「你禽.獸,我還是個孩子。」 某男淡定穿衣,唇角一抹饜足微弧:「比本王小兩歲,的確算個孩子。」
154.6萬字8 3477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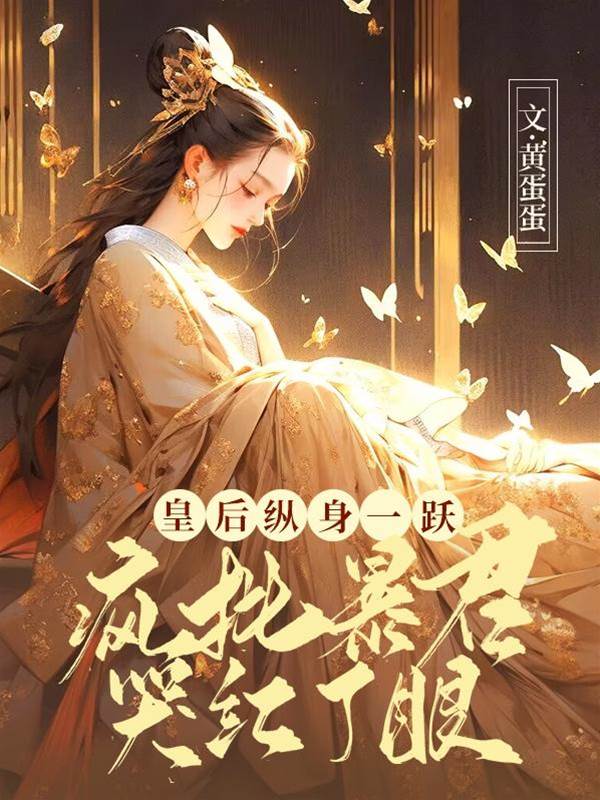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31 章

惹春嬌
【冷情國公世子vs草包將門美人】【歡喜冤家 一見鍾情 奉子成婚 甜寵1V1sc】崔恪出身名門,大家公子,這輩子都沒想到自己會娶甄珠這樣一個女人。她出生鄉野,毫無學識,貪財好色,蠢笨粗俗。且與他是天生的不對付。第一次見麵,脫鞋甩在他臉上,還將他推下河引來重病一場。第二次交集,因賭錢涉案栽在他手上,罰她吃了幾天牢飯,臨走時把滿腹汙穢吐在他的衣裳。輪到第三次,一夜春宵後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懷上了他的崽崽……起初的崔恪:“要娶甄珠?我崔夢之這是倒了幾輩子血黴?”後來的崔恪:“娘子不要和離,夫君什麼都聽你的!
7.9萬字8.18 3744 -
完結436 章

繼妹非要和我換親
宋尋月繼母厭她,妹妹欺她,還被繼母故意嫁給個窮秀才。怎料沒多久,窮秀才居然翻身高中,后來更是權傾朝野。她一躍成為京中最受追捧的官夫人,一時風光無量。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玩意背地里是個多麼陰狠毒辣的東西,害她心力交瘁,終至抑郁成疾,早早亡故。重生后,就在宋尋月絞盡腦汁想要退婚時,她同樣重生回來的繼妹,卻死活要和她換親。為了擺脫前夫,宋尋月咬牙上了郡王府的花轎。都說琰郡王謝堯臣,母妃不受寵,自己不上進,除了身份一無是處。可等真的嫁去郡王府,宋尋月才發現,謝堯臣居然這麼有錢!而且他還貪玩不回家!過慣苦日子的宋尋月,一邊品著八種食材熬制的鮑魚湯,一邊感動的直哭:家有萬金,府中唯她獨大,夫君還不愛她,這是什麼神仙日子?謝堯臣上輩子只想做個富貴閑人。怎知那蠢王妃借他之名奪嫡,害他被父皇厭棄,死于暗殺。重生后,謝堯臣備下一杯鴆酒,準備送蠢貨歸西。怎知蓋頭掀開,王妃竟是前世病逝的顧夫人。謝堯臣冷嗤,看來不必他動手。可時間一長,謝堯臣發現,他這個新王妃不僅身體康健,還使勁花他錢。每天吃喝玩樂,日子能過出花來。謝堯臣坐不住了,憑什麼娶回個王妃使勁花他錢他還守活寡,他是不是傻?于是在那個良夜,他終是進了宋尋月的房間。老皇帝當了一輩子明君,可上了年紀,兒子們卻斗得一個不剩。悲痛郁結之際,他那廢物兒子和王妃游歷回來了,還帶著個小孫子。一家三口紅光滿面,圍著他又是送禮物又是講游歷趣事。又感受到天倫之樂的老皇帝,輕嘆一聲,就把皇位送出去了。謝堯臣:?宋尋月:?在顧府悔恨難當的宋瑤月:???
70.6萬字8.18 55917 -
完結190 章

花好孕圓
从棺材里醒转,传说中的相公跟小妾在旁亲热,是躺回去呢,还是爬出来?——这是一红颜祸水不幸遇到个色中饿鬼的狗血故事。
56.7萬字8.18 27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