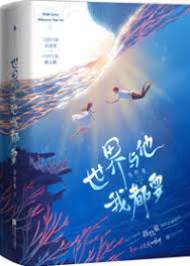《守村人離村后,我不傻了》 第12章 背叛
下午,工地上的一切都顯得格外安靜,只有泵車還在“嗡嗡”地運作著。
突然,泵車發出一聲尖銳的聲響,然后就卡殼了。
我借著檢修的機會鉆到了車底,發現輸料管里堵著一團頭發,那些發又黑又長,纏繞在一起,在發間還纏著一枚金鑲玉的耳墜。
我正要手去夠,后腰突然被一個頂住。
“別去撿,這工地上的東西邪門著呢!”
我轉過頭,看到了駝背老頭,他正舉著一鋼筋,昏花的老眼里泛著灰翳,眼神中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
“這工地...吃人呢。”
他低聲音說道,聲音里充滿了抖。
老頭老趙,是滄州人。
他把我拽到工棚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確定沒有人注意后,才從床底拖出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皮盒。
他打開盒子,里面堆著三十七枚銅錢,每枚銅錢都穿著紅繩,繩結掛著半截小指骨。
那些指骨在昏暗的線下泛著慘白的,讓人不寒而栗。
“半年前,工地打樁機挖出個壇子。”
老趙的假牙在不停地打,他的聲音也變得斷斷續續。
“里頭全是這玩意,工頭讓我們連夜埋回地基...從那以后,這工地就開始不對勁了,每天晚上都能聽到奇怪的聲音,還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蹤...”
我聽著老趙的講述,心中雖然也泛起一不安,但多年的經歷早已讓我習慣了各種詭異之事。
我面平靜,眼中沒有毫慌,只是淡淡地說道:“我不管它吃不吃人,它要是不給我工錢,我就該吃人了。”
這話一出口,老趙整個人都愣住了。
他瞪大了昏花的雙眼,不可思議地看著我,仿佛在看一個天外來客。
過了許久,他才緩過神來,結結地說道:“你...你可千萬小心吶。”
Advertisement
“我不用小心。”我看著他,笑了起來:“你們才應該小心一點。”
老趙搖了搖頭,將一枚銅錢遞給了我:“給你吧,你用得著。”
我看著手中的銅錢,點了點頭。
自從倒賣鋼筋嘗到了巨額利潤的甜頭,我心的貪婪再也無法遏制。
每天,我在工地里游時,眼中看到的不再是正在建設的高樓大廈,而是一堆堆等待變現的財富。
那些堆積如山的建筑材料,在我眼中就是一沓沓厚厚的鈔票,不斷著我。
我再次找到之前那些和我一起倒賣鋼筋的工人。
他們看到我時,眼中閃過一恐懼和不安。
我知道他們心里害怕,畢竟這種事,一旦被發現,大家都吃不了兜著走。
但我太了解他們了,這些人太缺錢了。
“兄弟們,這次只要干了,報酬絕對比上次還厚!”
我拍著脯,信誓旦旦地說道,眼神中出一種志在必得的神:“你們想想,就這麼一次,頂得上你們在工地干幾個月的工資了。”
其中一個工人皺了皺眉頭,小聲說道:“可是……這風險也太大了,萬一被抓住……”
我不屑地笑了笑,打斷他的話:“怕什麼!只要我們小心點,絕對不會有事的。我都安排好了,買家那邊也信得過,只要把貨運出去,錢馬上就能到手。”
在金錢的下,他們猶豫了片刻,最終還是點了點頭,眼中的貪婪逐漸取代了恐懼。
就這樣,我們再次狼狽為。
很快,我手中又多了一筆錢,而工地的材料又了很多。
李工頭得知工地材料接二連三被盜后,整個人暴跳如雷。
他在工地里大發雷霆,把所有工人都召集起來訓話。
“你們都給我聽好了!這工地里接二連三丟東西,肯定是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鬼!我告訴你們,別以為自己做得天無,我一定會把這個人找出來,到時候,誰也別想好過!”
Advertisement
他一邊說著,一邊用犀利的眼神掃視著每一個人,最后,目落在了我上,停留了片刻。
我心中一,但還是強裝鎮定,臉上出一副無辜的表。
他看著我,臉沉地說:“你最近的行為很可疑,我警告你,別在我工地上搞事。從明天起,你不用看守材料了,去西邊的工地幫忙吧。”
我滿不在乎地聳了聳肩:“行啊,去哪兒都行,反正工資不我的就行。”
我心里清楚,李工頭肯定知道是我干的,但他不會把我怎麼樣。
當天晚上。
我攥著新領的安全帽,指腹輕輕挲著襯糙的帆布,帶著一陳舊與糙。
里面依然沒有朱砂符。
隔壁床鋪的老趙鼾聲如雷,那聲音在寂靜的夜里格外響亮。
月過工棚那一道道寬窄不一的裂,灑在老趙的床板背面。
在昏黃的暈下,我瞧見了用公畫著的殘缺八卦圖。那八卦圖上的線條歪歪扭扭,乾位多出一筆蛇形紋,顯得格外詭異。
這已經是我本月第六次更換宿舍了,而這也是我發現的第三十七辟邪符。
每一次看到這些辟邪符,我的心中都涌起一難以言喻的不安。
就在這時,手機響了,李工頭給我打來了電話:
“小林,明天你去七樓驗收模板。”
“如果你不去,你干的那些事,就別怪我上報了。”
“行。我去。”我笑著說道。
第二天下午。
我剛一踏上七樓,一難以言喻的森氣息便如水般洶涌襲來,瞬間將我淹沒。
這氣息冰冷刺骨,帶著腐朽與死亡的味道,直鉆心底。
我頭上的安全帽陡然間重得如同灌滿了鉛水,沉甸甸地在頭頂,得我的脖頸生疼,好似有一雙無形的大手,正試圖將我狠狠按進這黑暗的深淵。
Advertisement
上次被鬼嬰抓破的裂里,緩緩滲出粘稠的黑,那黑仿佛有生命一般,順著我的后頸蜿蜒而下,流進工裝服。
它所到之,皮都泛起一層皮疙瘩,接著,口傳來一陣灼燒般的劇痛。
那黑竟詭異地凝北斗七星的灼痕,滾燙的簡直要將我的皮灼燒穿,讓我不倒吸一口涼氣。
三十七承重柱像是蟄伏已久的遠古巨,靜靜地矗立在黑暗中。
從它們表面麻麻的蜂窩孔里,傳出陣陣令人骨悚然的竊笑。
那笑聲尖銳又刺耳,猶如無數尖銳的鋼針,直直刺向我的耳,讓我腦袋嗡嗡作響。
我強忍著疼痛,定睛看去,只見這些潰爛的手掌這次攥著的,竟是我上周倒賣出去的鋁合金窗框殘片。
折進來,映照出三十七張扭曲的人臉。
每一張臉上都寫滿了痛苦與怨恨,他們的眼睛里閃爍著幽綠的芒,死死地盯著我,要將我生吞活剝,把我拖無盡的黑暗深淵。
“第八…卯時…”
梁財的聲音,帶著無盡的痛苦與急切,突然在我的耳畔炸響,如同一聲驚雷,震得我耳鼓生疼。
我猛地轉頭,看向東南角的立柱。
只見混凝土表面浮現的不再是半張臉,而是整尸正在從柱里向外掙扎。
梁財的扭曲變形,皮呈現出一種令人作嘔的青黑,不斷有腐從他上剝落,散發出一刺鼻的惡臭。
他腐爛的右手食指赫然缺失半截,而傷口,竟然嵌著我口袋里的那枚指骨銅錢。
我心中一驚,瞬間意識到老趙給我的銅錢有問題。
在這一刻,一種被背叛的覺如水般涌上心頭,讓我又憤怒又難過。
猜你喜歡
-
完結55 章

失憶后我成了大佬的白月光
[追妻火葬場,試試就逝世] 容初離家那晚碰到一個男人,陰差陽錯之后發現對方竟然是身家千億的頂奢集團太子爺,宴岑。 她生下了那個男人的孩子,卻沒能留住他的心。 三年后,國際時裝周,HF界的新晉寵兒云初作為開秀模特,一時風頭無倆。 這位東方面孔的頂級超模,邁開她一步六位數美金的臺步,又美又颯,勢不可擋。 突然,一個軟萌的小團子上臺抱住她的膝蓋,仰臉清脆喊了一聲:“媽咪!” 全場嘩然。 容初:“!!!” 震驚到裂開的容初望向臺下,看到第一排西裝革履的集團太子爺正深深看著自己。 男人黑眸幽深,“榕榕。” “我終于找到你了。” 容初:“?” 你誰?? ** #勁爆!那個新一屆的秀霸超模一門心思攀龍附鳳,為當太子妃甘作后媽!!# 一片“嘔口區D區”聲中,太子出來發聲了:“不是后媽,親的。” 那個最大珠寶集團新上任的CEO也發聲了:【那位新一屆的秀霸超模,是我妹妹,親的[微笑]】 那個剛參加完頒獎典禮的影后隔著時差,半夜上線:【自備身家,不攀不附,請有心人士莫cue我妹謝謝[再見]】 有心人士宴某人:“…………” ** #勁勁爆!超模竟是失蹤四年的珠寶千金!突然回歸欲跟對家鄭少聯姻!# 聯姻消息一傳出,鄭氏股價毫無預兆地暴跌,市值蒸發愈百億。 始作俑者宴岑親登容家門。 “跟我結婚。不簽婚前協議,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一臺步值六位數的頂級超模×一分鐘賺六位數的頂奢太子爺 *男女主彼此唯一,HE;狗血瑪麗蘇,請自行避雷 *涉及時尚圈HF圈,私設hin多,沒有原型,作者瞎掰
20.8萬字8 14265 -
完結1955 章
一胎四寶:轉走爹地十個億
蘇童雪嫁給喬墨寒時,所有人都說,她撞了大運。貧民窟出身,一無所有,卻成了權傾帝城男人的妻子。她以為隻要她努力,終可以用她的愛一點點焐熱喬墨寒的心。卻沒想到在臨盆之際,被硬生生割開肚子,取出孩子,踢下懸崖!四年後,浴火重生的她回歸。男人卻將她堵住,牙咬切齒:“蘇童雪!你這個無情的女人!竟敢拋夫棄子!”蘇童雪懵了。難道不是當初這男人嫌棄厭惡到都要將她毀屍滅跡了?
184.5萬字8 45888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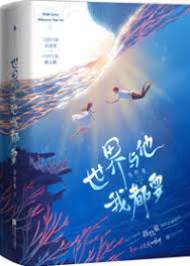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8147 -
完結177 章

前夫越界招惹
她一個姜家落魄的大小姐,跟一個窮小子結婚了,三年之后卻慘遭窮小子背叛。離婚沒多久,窮前夫突然搖身一變,成了帝國大佬。 她驚了! 直到有一天,前夫撞見她與別的男人說笑,開始瘋狂的趕走她身邊的爛桃花。 他抓著女人的手,極有占有欲的說。“我看老子的女人,誰敢招惹。” “不好意思啊,我對你這個老男人不感興趣,請拿開你的臟手,不要讓我的小奶狗看見了。” “看見了正好,讓他好好睜大他的狗眼看看,誰才是你的男人。”
35萬字8 1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