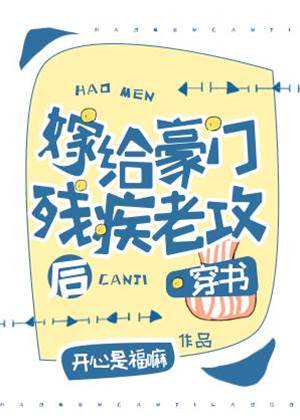《無聲野火》 第十六章 變態
三面無窗的房間,深灰地板,灰白墻面,靠房門這邊,一扇單面可視玻璃。
玻璃一塵不染,映著走廊墻壁壁燈,也映著一男一兩個人影。
孩兒扎高馬尾,穿一件橫條紋長袖T恤,下牛仔,帆布鞋。
男人短T,工裝短,板鞋。
孩兒怔怔地看著房。
男人側低頭,興致觀察孩兒反應。
房間里,從房頂四邊隙持續灌冷氣,卓文被綁著雙手雙腳,扔在房間中央。
薛一一不自覺抬手,上玻璃,指尖剛到玻璃,被冰涼驚醒,心地回。
僵地擰脖子,看向施璟。
他的臉、眼,全然一云淡風輕。
這就是…他說的玩兒?
施璟看著薛一一漂亮的眼睛,雙臂環抱前,慢吞婉轉的語調卻如銷尖鋒利的冰刃:“現在,,歸你。”
薛一一口緩緩起伏,轉頭看看房,閉著眼睛換一口氣,看向施璟,比劃:“那放走。”
施璟撐撐眼皮,食指在薛一一眼前搖擺兩下。
薛一一再看一眼房,卓文一頭黑發鋪著明顯的冰霜。
不知在里面呆了多久。
薛一一轉頭朝施璟比劃:“好像快死了。”
施璟大手握住薛一一后腦勺,掰轉過去:“看見手上戴的東西了嗎?”
卓文手腕上,除了麻繩,還有一塊類似手表的黑手環。
“生命監測儀。”施璟玩味兒口吻,“死了,就不好玩兒了。”
他說的好輕松。
好肆意。
仿佛這個世界,眼之所及,都是他的玩。
施璟有些重地拍兩下薛一一后腦勺,跟拍皮球似的,然后埋頭湊近,勾起角:“不就這麼跟警察說的嗎?是和你玩兒,只是玩兒過頭了而已。”
薛一一咬牙關,不知這些,施璟從何得知。
Advertisement
但細想,又覺得知道這些對他來說,并不是難事。
施璟很公平地問:“怎麼?可以玩兒你,你不能玩兒?”
公平不是這麼論的。
薛一一來不及反駁,施璟直背脊,抬手,打一個手勢。
隨著腳步聲,有人從昏暗走廊深走來,打開門,撿起不知從哪里接通的水管,擰開閥門,沖洗大白菜一般沖洗卓文。
應該是熱水。
冷熱替,房間彌漫一層水霧,恍如仙境。
但那扇玻璃窗,始終不沾水汽,視覺清晰無比。
房間門再次關上。
房,水霧漸漸消退,卓文再次浮現玻璃窗前,頭上冰霜消失,暫時‘活過來’。
睜開眼睛環視四周,抬不起的脖頸,絕的眼淚,不住打的子……
施璟單手扶著玻璃窗:“都說,帶你來玩兒的。”
薛一一看著房奄奄一息的卓文。
已經沒有往日的氣焰與高傲,弱勢得如同螻蟻。
或許,在邊這個男人眼里,們都一樣,都是螻蟻,沒有區別。
雖說,薛一一簽下和解書,是為了維護自己形象的偽善行為,但絕對,沒有冷漠到想過擔上人命。
活生生的人命。
沒有權利,也沒有能力擔人命。
薛一一一臉懇求,對施璟比劃:“求你放了,肯定知道錯了。”
施璟瞇瞇眼睛,猜不出意思。
薛一一拉住施璟擺,小孩兒要糖果般,請求姿態。
施璟垂眸,看一下那雙放肆的手,手腕勒痕瘀還未完全消散。
他抬起眼皮,提醒:“你還沒玩兒呢。”
薛一一搖頭,之以,曉之以理:“爺爺知道,會罰你的,不要因為我被罰。”
施璟咧一笑,很是輕蔑:“你玩兒你的,不用擔心我。”
薛一一:“我不喜歡玩這個。”
Advertisement
施璟傾,距離瞬間拉進。
他眼神銳利地在臉上游離,語氣埋怨:“那我不是白費功夫把弄來了?”
薛一一思索片刻,咬咬牙,轉走到門前,打開門,撿起地上水管,擰開閥門,象征沖一沖卓文。
做完這一切,如釋重負走出房間。
施璟懶散靠著墻,雙臂環抱,先開口:“薛一一,你玩兒我呢?!”
薛一一要說的話被堵,只能比劃:“要怎麼樣,才能結束?”
施璟微微仰頭,似在思考。
走廊墻壁壁燈,映出男人側面廓,刀刻般立,像一副藝品。
房門沒關,冷氣不斷,薛一一不由打一個寒。
施璟走向薛一一。
一把致小巧的瑞士軍刀出現在眼前,薛一一甚至沒看清施璟從哪兒變出來的。
他單手握著刀柄,指關節一,刀鞘落,又被他另一只手穩穩接掌心。
發著的赤白刀刃就在眼前。
薛一一不置信的瞪著雙眼,往后退。
像是早有預料會退,他手抓住的手臂,扭手腕,輕而易舉將轉半個圈扯進膛,正視房間里的卓文。
男人音淺淺:“我說結束,才能結束。”
眼前刀刃又近了幾分。
薛一一搖頭。
施璟抓起薛一一的手,將瑞士軍刀塞進手里。
刀柄冰涼的和深刻的紋路,清晰地告訴薛一一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害怕。
是真害怕了。
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后的人堅寬闊,沒有一點反抗之力。
掙扎不,急得眼淚奪眶而出,掛在下上,落在男人手背上。
施璟背脊一怔,蹙眉,握著薛一一手臂,利落把人轉過來。
鼻尖通紅,瓣咬著。
哭哭啼啼。
最煩人。
施璟吐氣道:“薛一一,沒人告訴過你,善良過頭,容易死嗎?”
Advertisement
他咬字清晰,一字一頓地忠告:“害、人、害、己。”
薛一一聽不懂這些沒有緣由的話,只顧著離自己的手。
瑞士軍刀應聲落地。
得虧施璟及時松手,否則刀刃能輕松切開薛一一半個手掌。
施璟看著這把骨頭:“不知死活。”
薛一一往后退兩步。
施璟垂頭,吐氣,單手叉腰,招手。
有人來,將卓文拖走。
施璟不悅地瞧一眼薛一一,彎腰撿起地上的瑞士軍刀,余看見薛一一搗雙腳,又退了小半步。
他不提起角。
將刀刃在鞋面正反刮蹭兩下,進刀鞘。
薛一一撇開臉。
以前,薛一一只是覺得施璟不重禮,不遵法,行事乖張。
現在,覺得他簡直變態。
甚至覺得,早該有這種覺悟才對。
猜你喜歡
-
完結1893 章

總有一天,你會喜歡我
三歲定終身,二十歲做他大總裁的貼身保鏢,這樣竹馬還能被別人騎跑,她這些年武學生涯算毛?悲催的是,從頭到尾被壓迫的都是她…… 五年後。 “媽咪!為什麼可愛的小白沒有爹地?” “我怎麼知道!去問你爹地!”夏鬱薰盯著電視裡的一對新人,頭也不回地說。 半個小時後,電視中的婚宴現場,奶娃娃抱著新郎大腿狂喊爹地。 男人死死盯著眼前袖...
168.6萬字8 34851 -
完結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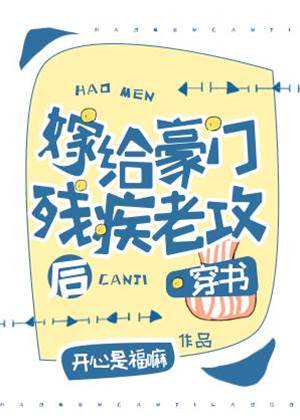
嫁給豪門殘疾老攻后
景淮睡前看了一本脆皮鴨文學。 主角受出生在一個又窮又古板的中醫世家,為了振興家業,被迫和青梅竹馬的男友分手,被家族送去和季家聯姻了。 然后攻受開始各種虐心虐身、誤會吃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會變成船戲之路。 而聯姻的那位季家掌門,就是他們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季靖延作為季家掌門人,有錢,有顏,有地位,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可惜雙腿殘疾。 完美戳中景淮所有萌點。 最慘的是自稱是潔黨的作者給他的設定還是個直男,和受其實啥都沒發生。 他的存在完全是為了引發攻受之間的各種誤會、吃醋、為原著攻和原著受的各種船戲服務,最后還被華麗歸來的攻和受聯手搞得身敗名裂、橫死街頭。 是個下場凄涼的炮灰。 - 原著攻:雖然我結婚,我出軌,我折磨你虐你,但我對你是真愛啊! 原著受:雖然你結婚,你出軌,你折磨我虐我,但我還是原諒你啊! 景淮:??? 可去你倆mua的吧!!! 等看到原著攻拋棄了同妻,原著受拋棄了炮灰直男丈夫,兩人為真愛私奔的時候,景淮氣到吐血三升。 棄文。 然后在評論區真情實感地留了千字diss長評。 第二天他醒來后,他變成主角受了。 景淮:“……” 結婚當天,景淮見到季靖延第一眼。 高冷總裁腿上蓋著薄毯子,西裝革履坐在豪車里,面若冷月,眸如清輝,氣質孤冷,漫不經心地看了他一眼。 景淮:……我要讓他感受世界的愛。
16.2萬字5 6189 -
完結402 章

幸孕:冷梟的契約情人
孿生姐妹,壹個是養尊處優的公主,壹個是流落他鄉的灰姑娘。灰姑娘終于翻身做了公主,卻是代其墜入地獄! 他,堂堂帝國的總裁,黑白兩道聞風喪膽的枭雄,在整個亞洲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擁有壹張天妒俊顔的他,身邊從來不缺女人。 壹紙契約,十八歲她作爲姐姐的替代品成了他的情人,壹再的忍讓和退步,只換來他更殘忍的羞辱和踐踏。 他,擁有無數FANS的天皇巨星,心裏卻只喜歡鄰家小妹清純如水的她。在相見,她已妖娆風情爲人情婦,重重誤會下,能否撥開迷霧。
100.2萬字8 104247 -
完結914 章

媽咪輕點虐,渣爹又被你氣哭啦
三年婚姻,卻被污蔑害死薄瑾御的孩子,八月孕肚被薄瑾御親手灌下墮胎藥,導致早產并被丟出薄家。五年后,她搖身一變成為頂級神醫,追求者無數。薄瑾御卻強勢的將她逼至角落,“那兩個孩子是我的親生骨肉?”沈寧苒笑了笑,“錯,你的親生骨肉已經被你自己親手殺死了。”薄瑾御將dna檢測報告拍在沈寧苒面前,拿上戶口本。沈寧苒,“去哪?”“復婚。”
190.4萬字8.57 101713 -
連載168 章

夫人提離婚後,商總戀愛腦覺醒
【虐戀 暗寵 雙潔 先婚後愛】夏恩淺的白月光是商頌,十年暗戀,卻從未有過交集。知道他高不可攀,知道他寡涼薄情,也知道他有未婚妻。一朝意外,她成了他的新娘。她從沒奢望,卻又想賭一把,最終,還是高估了自己。她流產,他在陪別人。她最愛的親人去世,他在陪別人。她被當眾欺辱人人嘲笑,他身邊護的還是別人。……當所有人都說她配不上他。深夜,夏恩淺丟下一紙協議,心如死灰,“商頌,你根本就沒有心。”男人死死攥著她要離開的手,眼裏翻滾著灼熱和偏執,嗓音嘶啞,“夏恩淺,沒有心的一直都是你……”
31.3萬字8.18 16026 -
連載289 章

日夜相對
在工作中,他們是上下級。在家里,他們住樓上樓下。每周有幾天,他們同床異夢。【雙潔+雙向救贖+成年人的童話故事】【女主精致利己假正經x男主斯文內斂真深情】
44.9萬字8.18 17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