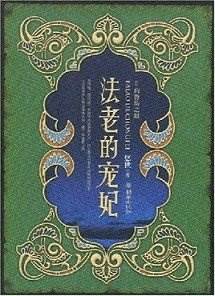《神醫嫡女》 第193章 誰跟你們是一家人?
小書一個勁兒地點頭,生怕羽珩聽不明白,又解釋道:“就是當朝的左丞相大人,我們爺是大人的侄子。”
羽珩納悶地看了看暈倒的這位爺,怎麼看都沒看出他跟瑾元長得有一點點相像之,再搜搜原主的記憶,老太太的確就瑾元一個獨子,沒道理瑾元再冒出個侄子啊?
這時,圍觀的百姓裡有人說話了,卻是笑那書:“真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了,在你面前的這位小姐就是家的兒,你家爺若真是相的侄子,那到還是致親呢!”
書一愣,這才仔細打量起羽珩,眉眼間到是有些瑾元的模樣,但家的小姐他也沒見過,不知道這是家的幾小姐。
見書發呆,又有人道:“該不是騙人的吧?你連家的嫡小姐都認不出來,還敢說你家爺是相的侄子?”
一聽說是嫡小姐,那書馬上就樂開了——“您是沉魚小姐?真的是沉魚小姐?”
羽珩皺眉看他,一言不發,到是邊的忘川說了句:“什麼沉魚小姐,這是府的嫡小姐。”
“府的嫡小姐不就是沉魚小姐麼?”那書一時沒反應過來,怔怔地看著羽珩,忽又想起聽說沉魚今年已經十四,過了這個年關就及笄了,可眼前這個孩怎麼看也不像快十五歲的樣子,不由得又問了句:“咱們說的是一個家嗎?”
羽珩點點頭,“當朝左相就只有一位,別無他人。”
“可是……”
“沒有可是。”站起,再看了眼那暈倒的年輕人,眉眼間到是能分辨出有幾分子皓的樣子。“你們是沈家的人吧?皇上有命,家不承認沈氏主母之位,沉魚自然也就不再是嫡。將人扶進百草堂吧,本縣主會替他醫治。”
Advertisement
那書沒太明白羽珩的話,怎的沉魚小姐就不再是嫡了?京城裡這嫡庶還可以隨意更換的麼?
但好在聽懂了羽珩讓他將人扶進百草堂的話,這才注意到前頭不遠就是一間診堂,頓時大喜,趕起去扶他家爺。
圍觀的百姓心地善良,紛紛過來幫忙,很快就將人擡了進去。
黃泉瞪著那年輕人,一臉的厭煩之,裡嘟囔道:“真不知道小姐怎麼想的,沈家的人就讓他凍死好了,救他作甚?”
忘川苦笑搖頭,“這麼多雙眼睛看著呢,若是任他死在百草堂門口,咱們這兩天的暖茶就也白施了。”
這幾日凍僵的不計其數,就連百草堂的夥計們都學會了如何救治,羽珩見人擡了進來便不再理,只囑咐黃泉:“回府去通報一聲,別的不用管。”黃泉答應著去了,便又回到了外面繼續分盛暖茶。
此時,玄天華正與淳王府過來的人說話,見羽珩回來了這才道:“阿珩,我得進宮去,父皇和母妃都派人來尋了。”
點點頭,“去吧,注意傷不能吃勁,回頭我把藥多調配幾副,著人送到七哥府上去。”
“好。”玄天華也不再多等,由下人攙扶著就上了馬車,臨走時說:“百草堂濟世安民,父皇早已得到了消息,丫頭,等著領賞吧。”
領不領賞的,羽珩到不是很在意,只是看著玄天華的馬車越行越遠,又擔心起玄天冥來。之前總想著過去看看,但如今想來,到是應該多相信他一些,不能因爲一場雪災,人就擔心得要跑到軍營裡去,這讓他的將士們看到了,指不定笑話什麼樣子。
想通這一層,便不再糾結於出城去大營的事,到是又看著百草堂外排得越來越長的隊伍開始憂心。
Advertisement
總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一碗暖茶解決不了最本的問題,百姓們需要的是更多災後資以及部份房屋的災後重建,而這些,則需要大量的金錢。
“忘川。”將手裡的碗給一名夥計,拉著忘川往邊上站了些,小聲道:“你再回一趟府裡,去找沉魚,就說我要你問問考慮得怎麼樣,並且告訴,那件事宜早不宜遲,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險。”
忘川點頭,也不問到底是什麼事,只是囑咐羽珩道:“那小姐您自己小心。”
“放心吧,還有班走呢,百草堂也有這麼些人,沒事,你快去快回。”
忘川見著急,趕就往府奔了去。這時,百草堂裡也有個夥計跑了過來,對道:“東家,剛纔那位公子醒了。”
“我去看看。”羽珩隨他進了堂,果然,那位疑似沈家爺的年輕人已經轉醒過來,只是面還有些蒼白,坐在榻上一聲一聲地嘆氣。“大個人,醒了就在這嘆氣,像什麼樣子?”頂煩這種不就愁眉苦臉天興嘆的男人,“悲天憫人有什麼用?有這工夫莫不如到前院兒去幫著分一碗茶。”一邊說一邊握住那人的脈,那年輕人嚇了一跳,就要把手回去,羽珩翻了個白臉斥他:“什麼?沒見過大夫診脈嗎?”
那人這纔不再掙扎,大氣都不敢出的看著羽珩。他的書就站在旁邊,也小心翼翼地低著頭不敢說話。
直到羽珩把手放開,小書這才試著問了句:“我家爺怎麼樣?”
“沒事了。”冷著臉,“回頭把診金和藥錢付了,再到掌櫃的那裡另抓些藥,回去吃幾天就行。”
“還要銀子?”小書納悶地問:“你不是家的人麼?家開的藥鋪怎麼還收自己人的錢?再說——”他指了指外頭那些被百草堂收治的人們,道:“我可是都的說了,那些人全是你們這裡救治的,分文不取,還給飯吃,怎的到了我們這兒就要收銀子了?”
Advertisement
羽珩一瞪眼,不幹了:“憑什麼不收?百草堂開門做生意,都不給錢我拿什麼養活這麼多活計?”
“我們是一家人!”
“誰跟你是一家?”羽珩本來就煩了沈家的人,如今這小書還扯上一家不一家的話,簡直就是了的底限,“我姓,你們姓啥?”
“我家爺姓沈!”
“沈家跟我有什麼關係?”面逐漸冷了下來,“我堂堂家嫡,居然要我認個小妾的孃家人是一家,大順朝什麼時候頒的這一條例律?我堂堂濟安縣主,還要你個奴才來教給我誰跟誰是一家?”
越說聲音越大,直嚇得那小書全都多嗦。
濟安縣主?要說家嫡,他還可以理解,畢竟剛纔這藥鋪的夥計已經給他普及了一下京城最近發生的一些大事。但卻唯獨忘了說羽珩已經被封爲縣主,鬧得這小書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吱唔了好半天,這才指著外頭的人說:“那爲什麼他們可以不給錢?”
羽珩挑眉,“我樂意。本縣主收錢看心,他們來的時候正趕上我心好,可一見到你們沈家人,本縣主的心瞬間就低落了。”
小書還想再說點什麼,卻被那年輕人攔了住,這一直沒說話的人總算是開了口,對書道:“花錢看病天經地義,快快將診金付給人家。”
爺發了話,小書再不好多說,一臉不願地去前頭付銀子。羽珩看著那年輕人,開口問了句:“你是沈家老幾的兒子?”既然說是侄子,應該就是沈氏那幾位哥哥家的孩子了。
年輕人想起來與說話,但子又實在虛弱,試了幾次也沒起來,無奈只好繼續坐著道:“在下沈青,是沈家的長孫。”
Advertisement
“老大家的?”在腦子裡將沈老大的樣子過了一遍,到是沒有太深的印象。
沈青點頭,“家父的確是沈家長子,但在下一直在外求學,已經多年沒有回過老家,這次上京是特地來拜會姑父的。”
羽珩搖搖頭,糾正了他的法:“你姑姑沈氏只是我父親的一個妾,你這聲姑父是萬萬不得的。”
沈青微怔了下,卻也沒爭辯什麼。當年沈氏妾擡妻位時,他已經是個半大年,自然懂得人倫理,也對家的做法並不贊同。但畢竟他是外人,無權評說家之事,如今沈氏被皇上親貶,說起來,也並不委屈。
“您是家的二小姐吧?”沈青看著羽珩道:“你小的時候我們曾見過,許是小姐不記得了。”
羽珩的確不記得了,原主的記憶零零散散,再加上原來那子,別說是個外姓的人,就連自己家人長什麼樣都模模糊糊,想容從小就跟在後,不也只記得個包子頭圓圓臉?
見羽珩並不怎麼與他說話,沈青也識趣地閉上了,直到那書回來,後還跟著個人時,沈青才終於鬆了口氣,衝著來人了聲:“姑父。”
羽珩眼一瞪,沈青立時就是一哆嗦,這纔想起剛剛的警告,於是趕的改了口——“大人。”
瑾元一聽沈青這反反覆覆的改口,就知羽珩一定是爲難了人家,不由得道:“你沈青表哥從小在梧縣老家的時候就跟著爲父讀書習字,大一些了就一直在外省求學,說起來,算是爲父的半個學生。”
“那就先生或是師父都好的。”看著瑾元,認真地道:“還有,兒必須要提醒父親,您讓我認一個妾室的孃家人爲表哥,那您置姚家於何地?”
瑾元一臉沉地與之對視著,這兒說話句句打臉,他都想不明白外頭那些緣何與之好,就不怕被嗆白?
可再心中有氣又能如何?羽珩說得沒錯,家中表親就只認主母的孃家,沈氏爲妾,沈家的人的確是不該與之攀親的。
“罷了。”他擺擺手,轉而對沈青道:“你就我一聲老師吧。”
沈青恭敬地答:“學生明白。”心裡卻也對家如今的局面做了一番分析,想來他的那沉魚表妹如今的日子過得也是不好,這位嫡小姐太厲害了,還頂著個縣主的頭銜,沉魚表妹那樣弱的人,還不得被欺負了去?
猜你喜歡
-
完結916 章
神醫棄女:邪王嗜寵小狂妃
醫學世家大小姐一朝穿越成平伯侯府不受寵的庶女,嫡姐陷害她嫁給大乾最醜陋的冷麪戰神——安王爺。傳說他性情殘暴,陰晴古怪,更是從來不近女色,人人對他聞之色變。性情殘暴?不近女色?她懷疑地看著眼前越貼越近的某人……“本王隻黏你!”“……”
139萬字8 54099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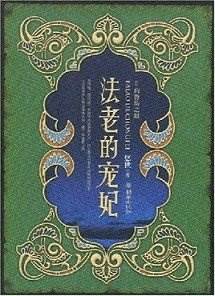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714 -
完結412 章

農女有空間:拐個將軍去逃荒
大慶末年,災難頻生!東邊兵禍,西邊旱情!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唐果兒一朝穿越,就趕上了逃荒大軍,黃沙遍野,寸草不生!左手是麵黃肌瘦的弟弟,右邊是現撿的胡子拉碴的大個兒拖油瓶!又看看自己弱不禁風的小身板! 隻想仰天長嘯一聲! 好在自己空間在手,吃喝不愁,看她怎麼帶著幼弟在這荒年裏掙出一番天地來! 呆萌女主:噯?!那個大個兒呢?! 腹黑將軍:你在問我嗎?
74.3萬字8 1171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