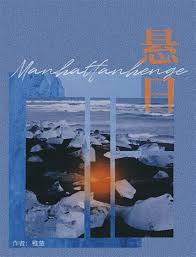《縛龍為后》 4
這讓燕鳶沒來由地到懊惱:“誰說我要一個人走了,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此話一出,不僅是龍,就連燕鳶自己都愣住了。
他本就是打算騙玄龍回宮再找機會挖龍心的。可方才他竟好像真的舍不得他似的,還為此生氣。
自己肯定是魔怔了。
雙雙對視了片刻,燕鳶率先回過神來,出手握住玄龍拿著筷子的手,笑道:“我們既做了夫妻,自然是要在一起的,難道你不愿與我相守到老嗎?……”
玄龍將‘相守到老’四字在心中默念,耳莫名發燙起來,淡定垂眸:“自是愿意。”
半個時辰后,萬尺高空之上,一條通純黑的巨龍在云層中穿梭,背上馱著一位容貌絕的人族男子。
隨著離皇宮越近,燕鳶的心思便越沉重,他騎在玄龍背上,玉白手指輕輕上龍斷了半截的右角,忍不住心疼道。
“阿泊,為何你頭上的角斷了一只?……”
“時被砍斷的。”玄龍輕描淡寫道。
燕鳶心頭發:“誰?”
玄龍:“我娘。”
燕鳶深深擰眉:“為何?”
“不知。”玄龍沉默半晌,說:“許是不喜歡我。”
他有好些兄弟姊妹,娘個個都疼,偏偏就不喜歡他,發起瘋時便用鞭子他。
那日喝醉了酒,執著長劍砍斷了他的龍角,將他逐出了龍族。
后來他沒再見過娘,便也沒機會問為何了。
為何要那般對他。
“疼嗎?……”燕鳶嚨發梗。
“不怎麼疼。”玄龍的嗓音低沉,平靜得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燕鳶想說幾句好聽的話哄他開心,可怎麼都說不出口,只得彎下子去溫地吻了吻玄龍的斷角,艱道。
“你還有我,我喜歡你。”
Advertisement
再多的,就不敢說了。
等那日到來時,真相太過殘忍。
殊不知燕鳶已經足夠殘忍,玄龍表面看起來對很多事無所謂,燕鳶說的每句話他都會認真記在心里。
“嗯。”
從未有人認真待他,燕鳶待他好,愿意親近他,他便當真了。
況且深燕鳶這件事,本就是不需要什麼道理的,那是一種刻在靈魂深的本能,就像他臉上業火灼燒的疤痕一樣,生生世世,不朽不滅。
第六章 拔鱗救人
皇城上方一道白閃過,兩個人影霎時出現在帝王寢殿,乾坤宮。
燕鳶急著去見自己心心念念的皇后,將玄龍安頓在寢宮偏殿便匆匆出了門。
他平安回宮的消息很快傳了個遍,待燕鳶到鸞殿的時候,太醫院的人已經候著了。
大紅喜緞尚未摘下,氣氛卻蕭條抑,床上昏睡的男人看起來比幾十天前還要蒼白,清潤的臉龐消減了不。
燕鳶一見寧枝玉這般模樣便紅了眼眶,緩緩在床沿坐下,握住他冰涼的手,啞道:“阿玉,你苦了。”
“朕很想你……”
床上的男人不理睬他,燕鳶也不惱,在床邊靜坐了許久。
他曾經發誓今生要好好保護寧枝玉,絕不蹈前世覆轍,如今人在他眼皮子底下病這般模樣,他如何能不著急難過。
小半炷香后,燕鳶淡淡出聲道。
“各位卿,可查出病因?”
太醫們哀哀嘆氣,喪氣地垂著頭。
“宗畫,你說。”燕鳶扭頭看向其中一位著朱紅袍的太醫。
宗畫便是當日向燕鳶提出龍心可醫百病的那位,他年紀輕輕已是太醫院一把好手,生得眉眼如畫,與名字很相匹配,醫上更有超過太醫院院首之勢,這也正是為何燕鳶如此相信他的原因。
Advertisement
然而此刻,就連宗畫都是一副為難模樣,他雙手扣,伏道:“回皇上的話,若還是尋不到龍心,皇后娘娘恐怕……撐不了太久了。”
燕鳶心頭一陣揪,想起玄龍那般信任自己的模樣,皺眉沉聲道:“……難道除了挖龍心,就別無他法了嗎?”
宗畫沉默須臾:“若實在尋不到龍心,尋些龍鱗來也是好的。”
“龍鱗?……”燕鳶愣道。
宗畫:“正是。”
“龍鱗效果雖不如龍心那般可徹除病,一勞永逸,但也有抑制頑疾的功效,越靠近心口位置的龍鱗,效果便越好。”
“若連服一月,皇后娘娘便能醒了。”
燕鳶眉頭舒展,眼中喜憂參半:“當真?”
如此一來,不僅玄龍不用死了,還能救阿玉。
龍鱗那種東西想來應該就如人的指甲那般,沒了還能長,痛便痛些,總比挖龍心好……
拔了鱗還能再長,挖了心,世上便再也沒有寒泊了。
“此療方乃是臣在家傳的醫書上親眼所見,理應無誤。”
燕鳶點頭,沉道:“朕知道了。”
“你們都退下吧,朕想與皇后單獨待會兒。”
……
乾坤宮偏殿不如主殿那般奢華,卻也是雕梁畫棟,寬敞無比。
玄龍頭一回接燕鳶從小生長的地方,向來孤冷乏味的他難得生出幾許好奇,忍不住觀察起周邊的環境來。
原來那人是在這樣的地方養出來的,難怪驕奢了些。不過在玄龍看來燕鳶怎麼樣都是很可的。
大劫將近,玄龍越發到自己靈力漸弱,不過是飛行了不算長久的一段距離就到很疲憊,他見殿中有張床,便過去盤打坐,誰知坐著坐著就睡著了。
天漸暗,靜了許久的殿響起推門聲,玄龍瞬間醒來,警惕地睜眼朝門口看去。
Advertisement
是燕鳶回來了。
那人不知何時換了明晃晃的龍袍,頭帶玉冠,魄修長,他本就白皙,此刻看來更是尊貴非凡。
他信步走到玄龍邊,在塌邊坐下,自然地抱著他的腰纏上去,將臉擱置在玄龍肩膀,低笑著問:“阿泊,可有想我?”
玄龍任他抱著,冷冰的雙瞳中出現不易察覺的:“嗯。”
原是在演戲,聽到對方這樣回答,燕鳶心竟是抑制不住地高興,不自地湊到他耳邊低聲說:“我也想你。”
“嗯。”玄龍的角彎了彎。
燕鳶驚住了,怔怔收回圈在他腰間的手,一臉不可思議地著男人英氣非凡的側臉,心臟砰砰跳得巨響:“……你剛剛笑了。”
玄龍聞言扭頭看他。
著男人綠松石般冰寒漂亮的眼睛,燕鳶出神道:“這是你第一次對我笑……”
玄龍眼中泄出幾分茫然。
他以前沒笑過嗎?……
似乎是這樣。
以前沒有值得他開心的事,自然沒理由笑。
但現在不一樣了。
這個人說喜歡他,愿意關心他……
“你笑起來真好看。”燕鳶無法抑心想要親近玄龍的沖,湊近他認真說:“以后要多笑笑。”
玄龍哪里有被如此夸過,面上一陣薄熱,不自然地扭開了頭:“嗯。”
片刻后,邊的人忽然環住他的腰,玄龍下意識扭頭去看,便和燕鳶在了一起,后者一個傾將他倒在榻上。
那日燕鳶騙玄龍說要與他做夫妻,本是為了折磨他一番好找機會挖龍心,誰知龍心沒挖到,燕鳶卻著了魔似的對他的食髓知味,時不時便著他胡來一番。
燕鳶知道自己這樣不對,但這種東西從來都是很難控制的,他在心安自己,等寧枝玉醒來,他必然會與玄龍斷個干凈。
如今不過是為了穩住玄龍,才做這些多余的事。
而在這種事上,玄龍從來不會拒絕他,即使燕鳶的技實在差極了,除了尺寸可觀之外毫無優點,除了痛還是痛。
結束之后,玄龍又是那副臉泛白的虛模樣,燕鳶一臉納悶地看著他,抬手替他了額角的冷汗,張道:“阿泊,你是不是很難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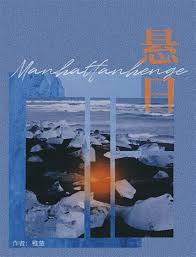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