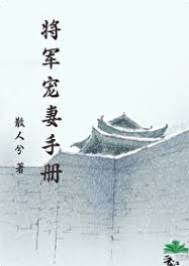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麻煩》 第130章 百子橋
珊娘他們回來的第二天,恰是元宵節。
一早,珊娘還在賴床,就聽到樓下傳來袁長卿和侯瑞侯玦說話的聲音。來三和一問才知道,卻原來是侯瑞侯玦竟想到了一去,拿著前些日子淘換到的花燈來討好珊娘。偏正好袁長卿過來珊娘起床,兄弟二人便拉著袁長卿在樓下賞起燈來。
等珊娘下了樓,就只見地上一地的紙屑,哥哥侯瑞正在撕著一只花燈上著的彩紙,弟弟侯玦則撅著屁跪在書案旁的一張椅子里,看著袁長卿伏案畫著什麼東西。
“這是怎麼了?”珊娘繞開那一地的紙屑,湊到侯瑞面前看了一眼他手里已經了一副骨架的花燈,笑道:“好好的燈,你把它撕了做什麼?”
“還不是你家那口子說的,這燈畫得太難看了。”侯瑞笑道。
珊娘臉一紅,回頭看了一眼袁長卿,見他正認真作畫,沒在看著這邊,便飛快地在侯瑞腦袋上拍了一掌,直打得侯瑞沖一陣瞪眼兒,偏不敢發作,著鼻子小聲道:“都嫁了人的人了,也不端莊些,竟還手!”
珊娘也是一瞪眼兒,作勢又要打他,低喝道:“什麼時候你都是我哥哥!”
侯瑞本能地往后一躲,嘀咕道:“還知道我是你哥哥呢,竟欺負我!”
珊娘收回手,又回頭看了一眼仍在畫畫的袁長卿,便問著侯瑞:“聽說家里替你相看著,你沒中意?”
侯瑞的臉紅了,翻著眼道:“你們人家,除了這點事,還能不能想點其他事了?!”
珊娘道:“好啊,那我問你,你以后打算做什麼?也不能在書院里讀一輩子書啊!”
這話題侯瑞愿意講,便丟開手里撕得七零八落的燈籠,對珊娘道:“我還真想過。我想出海去。”
Advertisement
“啊?!”珊娘嚇了一跳,那聲音忽地就大了起來。
“噓!”侯瑞趕豎起一手指,道:“不過你得替我保。”
珊娘忙道:“你怎麼竟真打起這個主意來了?!可是那時候在那個雙燕船上興起的念頭?!”
“也不是那個時候,”侯瑞道,“以前我就有這樣的想法,只是看到真正的船,我才確定,我真想上船。”又皺眉道,“怎麼?你以前不是贊同我的嘛!”
以前那只是說說而已,他又沒有真要上船去!珊娘也皺了眉,道:“以前你只說要出去看看,那我自是贊同的。但如今你是真要出海!那海上風大浪大的,上了船,你的命就全不由你了,別說老爺太太,就是我也不會同意!你上了船,你快活了,再沒人管你了,可你我們怎麼辦?整天替你提著個心,吊著個膽?!”
侯瑞看著,張了張,道:“人在家里坐,還禍從天上來呢,且又不是所有出海的人都回不來了……”
“還說!”珊娘惱火地又拍他一掌,“大過年的,就不能說點吉利話?!”又道,“你趁早歇了這心事吧,老爺那里再不可能應的!”
“我知道……”侯瑞泄氣道。
見他沒有堅持,珊娘松了口氣,道:“你好武,要不,明兒去考個武舉吧?”
“再說。”侯瑞煩惱地揮揮手,一抬頭,見那邊袁長卿正提著筆看著他們這邊,便揚聲笑道:“畫好了?”
見他不再提這件事,珊娘也轉了話題,過去看著袁長卿的畫道:“你們做什麼呢?”
侯玦搶著道:“姐夫嫌我那個跑馬燈畫得太拙了,要重新畫一個呢。”又抬頭看著珊娘道:“想不到姐夫畫得這麼好。”
Advertisement
珊娘早知道袁長卿琴棋書畫都有一手的,倒也不覺得驚訝,只低頭看向書案上的畫紙。還沒看出個所以然,就袁長卿手蒙了的眼,笑道:“等我們做好了你再看。”說著,推著轉開,“快去收拾一下,我們出去吃早茶。”
“我也要去!”侯玦立時道。
等珊娘換了大裳回來時,那走馬燈已經糊了起來。見從樓上下來,袁長卿便笑道:“好了,可以了。”
于是侯玦從椅子上跳下來,指揮著六安等人把門窗都給關了,袁長卿那里則點了那盞重新糊了畫的走馬燈。
隨著蠟燭點燃,那燈芯漸漸轉了起來。珊娘這才看到,原來袁長卿畫的是一匹奔馬,馬后時不時飛過來一只雀兒啄著馬的耳朵,那奔馬不堪其擾地搖著頭。而隨著燈籠里蠟燭燃燒的溫度越升越高,那馬則越跑越快,雀兒也越啄越快,倒像是馬兒在拼命要逃開那只雀兒的捉弄一般。珊娘忍不住笑了起來,抬頭對袁長卿道:“你可真促狹!”
正笑著,忽然聽得外面傳來老爺的聲音,“這大白天的,關什麼門啊?”
“老爺來了。”侯玦笑著撲過去開了門,見老爺太太都在院子里,連全哥兒也被他娘抱著過來了,他便過去拉著全哥兒的手,對老爺太太道:“快來看姐夫畫的跑馬燈。”
老爺進來一看,頓時一陣贊嘆,又習慣地拍著桌子道:“我怎麼就沒想到?往年都嫌外面做的燈糙,其實我們改一改也就了雅的。”
侯瑞笑道:“要不老爺也給畫一個吧,我這燈還著呢。”說著,他提起他那盞只剩下一個框架的跑馬燈。
“行!”老爺來了勁頭,忙回頭命田大上街再去買幾盞回來改造,太太趕阻止著他道:“做兩盞玩一玩也就罷了,多了就沒那個趣味了。”
Advertisement
老爺聽了忙道:“有理有理。”又回頭看著袁長卿笑道:“原當你是個書呆子,原來還有趣的,比你老師強。”
袁長卿笑道:“老爺不是說要出去吃早茶的嗎?回來再畫吧。”說著,看了一眼珊娘。
珊娘此時手里正拿著塊糕要往里送——確實也了,不然也不會一大早就劈頭蓋臉地教訓了哥哥一通——偏袁長卿那麼一看,所有人都調轉視線看向。頓時,拿著那塊糕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便惱怒地瞪了袁長卿一眼。
偏這一眼又老爺看到了,笑話著道:“對對對,去吃早茶!再晚些,我們珊兒就該得要吃人了!”說得眾人又是一陣笑。
在鎮子上有名的館子里吃了頓早茶后,一家子又去老太爺老太太那里打了個轉兒。老太爺向來是個只管自己的,連面兒都沒見就把一家子給打發了。老太太則是明里暗里把五老爺又給敲打了一通。珊娘后來才知道,老太太一直在質疑著五老爺手里哪來的閑錢給珊娘備下那麼一份嫁妝。五老爺也不瞞老太太,偏老太太不信他能靠賣畫嫁兒,只當他是有什麼財路不肯告訴,母子二人的關系竟因此又更僵了一層。
元宵節,是燈的節日。對于人來說,許更喜歡猜燈謎,但對于孩子來說,則更喜歡提著燈籠招搖過市,何況如今侯玦還得了一盞全天下獨一無二的跑馬燈。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侯玦急急點亮那盞袁長卿改造過的奔馬燈就跑出了府門,站在臺階上回頭沖著門跳著腳地道:“老爺太太,姐姐姐夫,快點啊。”
老爺扶著太太出了府門,卻是本就不去管那跳著腳大喊大的侯玦,只低聲安著仍有些不安的太太。太太則回頭看著騎在侯瑞脖子上的全哥兒,問著老爺:“真的不要嗎?”——每年燈會上都有走丟孩子的事,全哥兒如今話還說不周全呢,太太實在有些擔心。
Advertisement
侯瑞脖子上架著全哥兒,手里則提著老爺畫的那盞趣十足的青蛙撲螞蚱的走馬燈,沖太太咧笑道:“太太放心,有我呢,定不會全哥兒有閃失。”
老爺也道:“還有家人們跟著呢,放心吧,我們只轉一圈,走走百病就回來。”
見老爺太太和哥哥弟弟都出來了,偏珊娘和袁長卿還沒出來,侯玦便急地又沖著門跳起腳來,大聲著:”姐姐姐夫,快點啊!”
“來了來了,”珊娘連聲應著,又道:“倒是你,別跑,看栽了牙!”說話間,扶著袁長卿的手從門里出來。
眾人回頭一看,頓時全都是一愕。
只見門口高懸的大紅燈籠下,正并肩站著一對璧人。子上裹著件遍地繁花金彩繡的大紅斗篷,那翻起的斗篷邊緣鑲著圈雪白的狐皮,生生襯得那張藏在風帽下的小臉一片瑩潤白皙。的旁,男子則是一簡單素雅的玄衫,那利落的箭袖配著束的腰,更顯得他長玉立,猿背蜂腰。
這一大紅一玄黑,一高大一小,竟是相映趣,也實是養著人眼。老爺忍不住贊嘆道:“回頭這一且先別急著換下來。”
“為什麼?”珊娘扶著袁長卿的手下了臺階,疑問道。
“得畫下來啊!”老爺笑道,“不然可惜了的。”
珊娘這才意識到,原來老爺是在打趣和袁長卿,不由紅了臉。誰知袁長卿卻順水推舟地應道:“那就辛苦岳父了。”頓時不客氣地指下用力,擰了他一把。偏袁長卿是個練武的,真要繃了胳膊,竟怎麼也擰不他。
二人手里做著小作,卻并不妨礙袁長卿和五老爺說著話。
這翁婿二人從畫說到字,從字說到文壇畫壇上的人風流,再說到每年春天京里的各種文人雅集,老爺忍不住慨道:“我也就是那年應著你老師之邀去過一趟京城,可只那一回,便我用無窮。說起來,到底是這梅山鎮上太小了,便是想找一兩個同道流,到底進益有限。”
袁長卿笑道:“豈止是岳父您用無窮,您當年在文匯苑潑墨揮毫的那幅畫,至今仍掛在苑中任人評點呢。有無數人想學著您的畫風,終究不如您的灑。”
“唉,不提了,”五老爺憾地揮揮手,“若不是老太太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催,我就留在京城不回來了。若有機會我跟著那些大家多學一學,許我的技法也不會這麼多年都沒個長進了。”
袁長卿忽地看了一眼正和太太說著話的珊娘,回頭對五老爺笑道:“如今珊兒嫁到京里,老爺倒是有理由和京里常來常往了。”
五老爺心里一,頓時看了袁長卿一眼。翁婿對了個眼兒,不由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五老爺拍著袁長卿的肩道:“你很好。”
“什麼?”珊娘正好聽到這句話,便回頭問著老爺。
老爺立時大言不慚道:“如今我越來越覺得,我替你挑的這個婿不錯。”——他這會兒倒是忘了,當初哪一個咬牙切齒堅決不肯點頭同意的了。
而袁長卿那里竟也看著珊娘用力一點頭……
珊娘不由一陣無語,一回,拉著太太便快步離了這兩個厚臉皮的男人。
兩個厚臉皮的男人相互對視一眼,老爺低聲音道:“難得今兒元宵,你帶著珊兒去走走吧。”
作為一個懂事的婿,袁長卿頓時秒懂,老爺這是嫌珊娘霸占著太太呢。于是他趕過去,找了個借口哄著珊娘離了眾人,等珊娘回過味來時,五老爺一行人早走遠了。珊娘忍不住橫了袁長卿一眼。
袁長卿則微彎著眼角,握了藏在斗篷下的手,二人在人流中一陣緩步慢行。漸漸的,二人竟越走越慢,等走到某條暗巷時,袁長卿的眼飛快地往左右一看,驀地地挾著,將推進了暗。珊娘正待要,他的頭已經低了下來,狠狠咬住的。
珊娘吃了一疼,微一張,便他的舌溜了進去。明明平常總是四平八穩的一個人,偏偏在這種事上總像個急鬼,竟是怎麼喂都喂不飽的模樣。他急切地咬著,吻著,吮著,弄得又是疼又是麻又是的,只覺得渾發熱,雙腳虛,附著他,生怕他一松手,便會丟臉地力跌倒。偏的近,令他越想近于,于是那舌漸漸便失了分寸,吻得愈發的深了……直到某傳來一陣腳步聲。
二人一驚,這才從激中回過神來。袁長卿猛地抱,腳下一旋,便帶著上了樹。看著一對同樣看燈的小夫妻躲進他倆才剛躲過的地方,做著他們才剛做過的事,珊娘驀地就紅了臉,才剛要閃開眼,卻袁長卿掰過的臉,將按在樹干上又是一陣熱吻……
等神智再次恢復清明時,樹下的那對小夫妻已經走開了。袁長卿抵著的額,啞著聲音道:“還有八天。”
回娘家住對月的日子是有規矩的,最長只能住九天。袁長卿這是在算著他們分開的日子……
“你!”珊娘一陣惱,手在他腰間狠擰了一把,怒道:“鬼!”
袁長卿痛得哼哼著,卻依舊不肯放開,湊到的耳旁無賴道:“可我就是想你,想要你……”
等夫妻二人重新回到人流中時,珊娘的臉仍是紅紅的。正慶幸著天黑沒人看到,忽然就聽到后有人著的名字:“十三,十三!”
珊娘一回頭,驀地窘了。再想不到,在最不想遇到人的時候,竟遇到了人,且還都是閨中的友。
林如稚和趙香兒、游慧三個手拉著手地跑過來,林如稚一臉得意地道:“看吧,我就說我沒看錯!”又問著珊娘:“你不是說月底才會回來的嗎?早間接到你的子時嚇了一跳。”
說話間,那三個人便以理所應當的架式,直接將袁長卿到一邊,圍著珊娘一陣嘰嘰喳喳,“你是什麼時候到的?什麼時候走?京城怎麼樣?”活潑的趙香兒更是直接湊到珊娘的耳旁逗著,“做新娘子的覺如何?”
珊娘頓時又紅了臉。
堵在袁長卿和珊娘中間的游慧卻忽地覺到脖子后面一陣生寒,扭頭看去,只見袁長卿正目清冷的看著們。打了個哆嗦,立時反應過來,忙手拉開另兩個好友,笑道:“瞧你們兩個,看到十三高興得昏了頭了?!今兒是什麼日子?這又是什麼地方?有話我們明天再說,走了走了!”說著,一陣風似地拉著林如稚和趙香兒慧跑了。
遠遠的,珊娘還聽到林如稚茫然答著游慧,“今兒是元宵啊,這里是百子橋,怎麼了?”
林如稚自小不是在梅山鎮上長大的,自是不知道梅山鎮的風俗,珊娘卻是深知的。驀地的一怔,扭頭看了一眼后的橋,又飛快地看了一眼袁長卿——他,懂得這橋的意思嗎?
顯然,向來擅長觀察的袁長卿是知道的。
“來,我們也數數。”他笑著拉起珊娘的手,帶著往百子橋過去——當地的風俗,元宵節時夫妻走百子橋,是求子的意思。數著過橋的腳步,若是雙,便是兒,若是單,便是兒子……
珊娘僵在橋邊,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
袁長卿拉著出一步,見沒,不由一陣詫異,扭頭看向,“怎麼了?”他問。
“我……我……”珊娘說不出口心里的不安,只慌地閃著眼。
袁長卿卻自以為明白的擔憂,上前一步,低頭看著聲笑道:“不過求個吉利而已,又不是現在就生。”又道,“你還小著呢。”
這是他倆頭一次說到孩子的事。珊娘忽然意識到。同時也意識到,便是再怎麼沒有信心做一個合格的母親,這件事便如要嫁他一樣,是逃不開的事……
既然逃不開,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便是去面對這件事……既然的婚姻已不同前世,許面對兒時,也能做個不一樣的母親呢?
珊娘攥著袁長卿的手,和他一起默默數著腳步。
“雙數。”松了口氣,抬頭看著袁長卿微笑道。
雙數,預示著是個兒。而前世時,頭一胎生的是兒子。一點不同,許也預示著許多的不同……
猜你喜歡
-
完結475 章
廚女當家:山裡漢子,寵不休
一朝穿越成食不裹腹,家徒四壁的農家貧戶,還是一個沖喜小娘子。 陳辰仰天長嘆。 穿就穿吧,她一個現代女廚神,難道還怕餓死嗎? 投身在農門,鄉裡鄉親是非多,且看她如何手撕極品,發家致富,開創一個盛世錦繡人生。 唯一讓她操蛋的是,白天辛苦耕耘賺錢,晚上某隻妖孽美男還要嚷嚷著播種種包子。 去他的種包子,老孃不伺候。
87.3萬字7 49745 -
完結1071 章

權寵天下:本候要納夫!
忠遠侯府誕下雙生女,但侯府無子,為延續百年榮華,最後出生的穆千翊,成為侯府唯一的‘嫡子’。 一朝穿越,她本是殺手組織的金牌殺手,女扮男裝對她來說毫無壓力。 但她怎麼甘心乖乖當個侯爺? 野心這東西,她從未掩藏過。 然而,一不小心招惹了喜怒無常且潔癖嚴重的第一美男寧王怎麼辦? 他是顏傾天下的寧王,冷酷狠辣,運籌帷幄,隻因被她救過一命從此對她極度容忍。 第一次被穆千翊詢問,是否願意嫁給她,他怒火滔天! 第二次被穆千翊詢問,他隱忍未發。 第三次,他猶豫了:讓本王好好想想……
102萬字8 40383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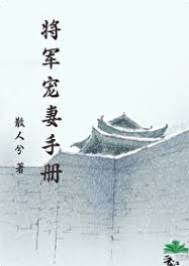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