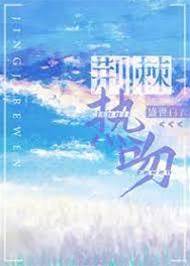《大國醫》 第八十八章 父母
接下來一周,陸爸爸在畫圖, 陸則和裴舒窈在暗渡陳倉。
因為是在裴家父母眼皮底下, 兩個人牽個手也覺得刺激, 可惜他們這幾年時不時形影不離地膩在一起, 裴正德和伍心慈對他們關系的轉變一無所察。
這讓陸則和裴舒窈有種干壞事竟沒人發現的失落。
七天轉眼即逝,陸爸爸要在機場和助手會合,飛下一個目的地去。
陸則開車送陸爸爸到機場。
兩個人一起從停車場往里走,一路話都不多,到遠遠見到自己助手了, 陸爸爸才對陸則說:“你師妹很好。”
陸則一怔,看向陸爸爸。
陸爸爸說:“你和我不一樣。”他的眼睫很長, 在機場玻璃頂灑落的日中輕輕了, 落下淺淺的影。面對自己唯一的兒子,陸爸爸說出了藏在心里的話,“你,對好一些。”
這些年陸爸爸偶爾也會想起曾經時常跟在自己后跑的明,那是個從小被養著長大的孩兒,本來應該嫁給一個疼的男人, 被人悉心呵護著過一輩子。
可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他。
他們結婚之后,他常年在外,連孩子出生都不在邊。
變得越來越不快樂。
家人不認同, 丈夫不在邊,一個人工作、一個人生活、一個人帶著孩子磕磕絆絆地過日子,連小孩生病都沒人能商量。
那樣的婚姻, 本就不會讓人快活。
對于前妻和兒子,他心里是有愧的。這種愧疚一開始并不明顯,隨著邊的人逐漸有了家庭、有了兒,才變得越來越鮮明。
陸則沒想到陸爸爸會是第一個看出來的人。
他對陸爸爸說:“爸爸放心,我會對好的。”
Advertisement
陸爸爸點點頭,表示自己相信他,不再多說,邁步走向助手所在的方向。
正好趕上某個航班登機,一群人熙熙攘攘地朝同一個方向走去,阻隔了陸則的視線。
等人都走過去了,陸則才重新看見陸爸爸和他助手的背影。他不是多愁善的人,站在原看了一會,轉去停車場找自己的車。
“陸師兄?”
陸則正要開車門,驀然聽到有人在后喊自己。他轉頭看向對方,只見一個相貌弱麗的孩站在那,有些怯生生地看著他。
陸則頓了頓,禮貌地說:“你好。”
孩說:“對不起,陸師兄,我可能給你造了困擾。”
“沒有。”陸則毫不猶豫地說。
孩子本來有很多話要說,聽到這話后卡殼了。
“你沒有給我造困擾。”陸則耐心地把話說得詳細一些,“不必和我道歉。”
這孩就是師弟們前兩年選出的系花,屬于男人非常容易系花上的類型,不過陸則記住倒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被副院長兒子追得,臨時拉住他向他表白。
這樣的事陸則一向不摻和,也并不在意副院長兒子明里暗里的小作,反正只要影響不到他,他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
倒是那個副院長那個胖兒子出去和人飆車摔斷,休學了一個學期,到現在陸則都沒再見過他,也不知有沒有瘦下來。
陸則自認為自己非常文明禮貌又,和系花師妹說完話就上了車。
作為一個已經有朋友的人,陸則沒有問對方是不是一個人、需不需要他載上一程,干脆利落地把開車離開機場。
自從江老回了醫院,陸則幾乎是一整周連軸轉,好不容易到休息日,送完陸爸爸,他又倒回去接裴舒窈,找裴舒窈去實地看看他們未來的據點。
Advertisement
以后他們想在這邊開講座、搞研究或者單純安安靜靜看看書都可以。
衛父送陸則的醫院那一帶剛拆遷完,到都只剩下些地基殘,瞧著有些荒涼。不過據市政放出的規劃圖,這一帶會大力發展新城區,將來這片地可以算是新城區的中心,升值空間大得很。
兩個人在推了房屋的空地上轉悠。
其實現在什麼都沒有,也沒什麼好逛的,但這算是他們確定關系后第一次單獨出來約會,陸則覺得還是該挑選一個有意義的地方。
裴舒窈對陸則挑的約會地點沒有意見,馬上要飛首都,哪怕只是隨意在街上走一走,心里也很高興。
房屋雖然推了,遠卻還留著些樹木,原本建了房屋的地方也還堆著些廢棄建筑材料,視野不算開闊。
兩個人下了車,沿著原有的蜿蜒道路走了一小會,正謀著無聲無息地把手牽到一起,忽聽前面傳來一陣凄慘的哭聲。
陸則和裴舒窈對視一眼,毫不猶豫地抓住裴舒窈的手把拉到自己邊。
兩個人一起循著哭聲找過去,只見一個小孩被個人抄著子打。小孩的頸上有著一道猙獰的傷疤,像是燒傷,仿佛傷了嚨,說不出話來,只能凄厲地哭。
陸則皺起眉頭。
那個打人的人神兇惡,一點都沒有為人母親的慈。哪怕小孩已經在討饒,還是抄著子往小孩上打:“你出去討點錢回來,你就給我討了五塊錢,還在這里敢躲著懶!你個賠錢貨,是不是想死老娘?我告訴你,我把你養這麼大,就是讓你孝敬我的!”
陸則松開裴舒窈的手,上前一把抓住人手里的木。
人抬頭看向陸則。
Advertisement
看到陸則的著和長相,人兩眼一亮。也不搶陸則抓在手里的子,只擰著小孩的耳朵自認萬種風地朝陸則一笑,“這位小兄弟是要路見不平嗎?要我不打也行,你給施舍幾百塊,我保證的不打。”
陸則松開手里的子,看了眼被人揪著耳朵的孩子。
這孩子目里有著恐慌和乞求,既期盼陸則能救,也害怕陸則說幾句就離開、人會變本加厲地打。
很難想象會有人這樣的對自己的孩子。
陸則把小孩從人手里解救出來,目落在人上。
“我懷疑不是你的兒。”陸則轉頭對裴舒窈說,“報警吧。”
人臉一變,厲荏地怒罵:“你胡說八道什麼?這十里八鄉誰不知道是我兒?我把從娃娃拉扯到這麼大,你是哪來的頭小子,空口無憑就敢說不是我兒!”
陸則說:“哪怕是你的兒,你這樣對也已經足夠撤銷你的監護資格。”
小孩要是及時去治療,傷口肯定不會這麼猙獰可怕,嚨也不至于毀這樣。
說話間,裴舒窈已經默契地報完警。
人沖過來要搶小孩,小孩卻像是終于找到救星一樣畏怯地躲到了陸則和裴舒窈后。
這邊的靜把在不遠那株大樟樹下打牌的人給驚了,過來看到兩個生面孔,不由說:“年輕人你不是這里人吧?”
雖然屋子拆遷了,但前面的廣場還留著,他們還是溜達過來老地方打打牌聊聊天。對這一帶的人大多知知底,他們看著人和那小孩直搖頭,七八舌地說起小孩家的況——
“勸你還是別管閑事,上次有個大學生來采風時好心報了警,警察過來調解過,回頭還不是一天三頓地揍。”
Advertisement
“們家就們娘倆,一年到頭沒個親戚上門的,這麼小一娃娃,不跟著媽還能跟誰?”
“瞧你們兩個都是小年輕,不知道世道艱難。這年頭最不好管的就是閑事,管得了這一次,難道你還能管一輩子?”
“對,別人的家事你們能怎麼管?別平白惹了一。”
小孩本來滿含希冀地手攥裴舒窈的角,希這次有人可以救自己,聽著這些“老鄰居”們的話后手慢慢吹了下去,原本就含在眼里的淚簌簌往下掉。
人冷笑看著,在心里琢磨著等一下要怎麼給這敢讓自己沒臉的死丫頭一個畢生難忘的教訓。
這邊因為拆遷出了幾樁事,警察接到報警后來得很快。
聽說是這母倆的事,警察面難,這個人實在難纏,不工作,房租和吃飯都是打發兒出去乞討湊的,一不高興還打孩子出氣。
他們甚至懷疑兒的燒傷是故意弄出來了,真是太慘了。
可們家沒別人,小孩只這麼一個媽,孩子爸爸、祖父母、外祖父都聯系不上,他們實在沒辦法,上門調解更行不通,這人會變本加厲地打兒。
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的母親?
陸則見年輕的警察面為難和憐憫,那人則一臉得意地立在原,毫無悔意、毫不驚慌。
陸則看向低頭啜泣的小孩。
既然遇上了,當然沒有不管的道理。裴舒窈蹲下,掏出一方手絹給小孩眼淚,等小孩止住了哭意,才問:“如果你說不出話,就點頭或搖頭,可以嗎?”
小孩點頭。
裴舒窈問:“是不是經常這樣打你?”
小孩點頭。
裴舒窈說:“你還愿意和一起生活嗎?”
人狠狠看,目里滿是威脅。
小孩渾一僵,在裴舒窈和的注視中猛地搖頭。過太多白眼,也挨過太多毒打,所以可以分辨出這兩個人是不一樣的,他們是好人。
他們也許真的可以幫。
小孩眼淚又涌了出來,不停地搖頭,向裴舒窈表達自己到底有多不愿意繼續和這個該稱為母親的人一起生活。
人見敢搖頭,沖上前就要甩一個耳,口里直罵:“你個死丫頭,反了天了你!”
陸則輕松抓住人要逞兇的手。
作者有話要說:
小陸:決定來一個有意義的浪漫的約會!
小陸:?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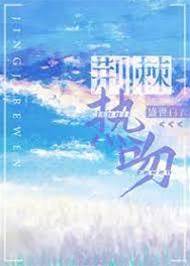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