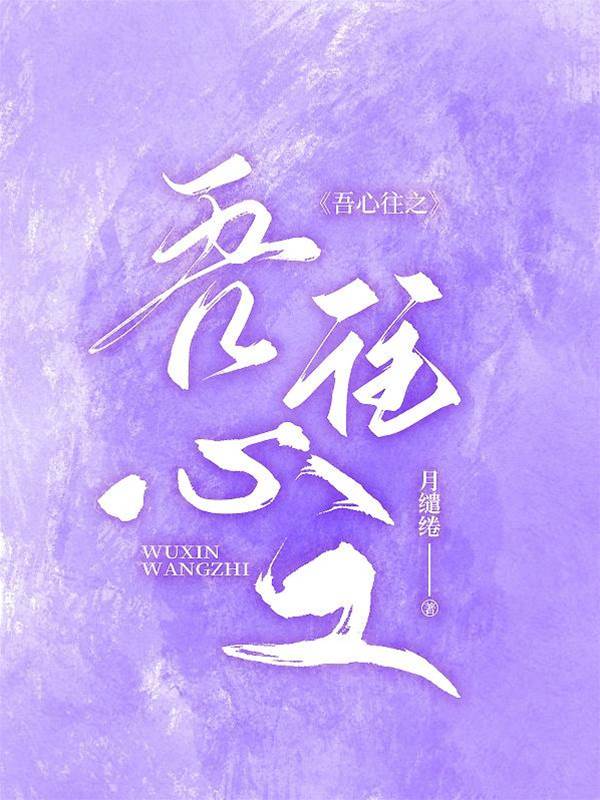《在暴戾的他懷里撒個嬌》 第45章 軟飯
醫務室里, 在醫生和寂白的強烈要求下,謝隨掉了上, 讓醫生為他進行全面的檢查。
寂白并沒有回避, 站在病床邊, 打量著謝隨的上半。
他上充實, 平時穿著服或許看不出來,不過了服卻能明顯到塊狀的力量, 腹部的六塊腹非常漂亮,人魚線一直蜿蜒到角以下, 極了。
甚至連立于旁的年輕護士都忍不住驚嘆,高中生居然能夠練出這樣的材, 真是見啊。
謝隨上的淤青就比臉上要嚴重許多了, 腹部有, 背后也有, 前的一塊淤青都已經變紫了。
僅看這些目驚心的淤傷, 寂白都可以想見當時的戰況有多激烈。別開了目, 不敢再多看一眼,太難了。
醫生仔細檢查了謝隨上的傷勢, 叮囑道:“都是皮外傷,開一些化瘀的藥每天。”
寂白很不放心,問道:“醫生,他是跟人打架的傷,確定沒問題嗎?臟有沒有損,需要進行詳細檢嗎?”
“是皮外傷, 要是臟有問題,他現在已經站不起了。”
醫生看了看寂白,對謝隨說道:“以后別出去跟人打架斗毆了,你看看,讓朋友多擔心啊。”
謝隨聽到“朋友”三個字,低下頭,角含蓄地抿了笑。
寂白心糟糕頂,哪怕聽到醫生說謝隨沒大礙,但看著他上這大片的淤青,還是覺得特別難。
醫生離開的時候叮囑謝隨,外敷的藥每天都要,不能落下。
謝隨自然不敢怠慢,上就算了,他角這一塊淤青必須盡快化開,不然還真沒辦法跟小白一起出席宴會。
醫生離開以后,冷冰冰的醫務室里,就剩了寂白和謝隨兩個人。
Advertisement
謝隨心里沒底,不太敢看孩的眼睛,他手過了自己的衛外套,準備穿上,寂白卻忽然扯住了他的服:“你等一下。”
聲音悶悶的,帶著濃重的鼻音。
謝隨眼睜睜看著孩坐到了病床邊緣,和他面對面地坐著,斂著眸子,著他前殘留的大片傷痕。
“疼不?”
“疼什麼疼,完全沒覺。”
謝隨是要死撐面子的,那天被揍得都他媽快要飛升了,但他堅決不會承認。
寂白擰開了藥管,對謝隨說:“先臉,你放低一點。”
謝隨看著瑩潤的手指尖綴了白的藥膏,意識到是要給自己上藥,有些寵若驚。
寂白見這家伙像是傻了似的,索手將他的腦袋按下來,然后小心翼翼地將藥膏在了他角的位置。
謝隨著孩的指頭一圈一圈地著他角傷口,藥膏含著薄荷香,味道清涼,令他的鼻息通暢了不。
孩作輕,生怕疼了他似的,非常小心,黑漆漆的杏眼專注地凝著他角的傷口。
謝隨凝著孩櫻的,不自地又湊了過去。
連著被吻了兩次的寂白宛如小鹿一般敏銳,看他眼神不對勁,立刻反應了過來,偏頭避開他。
“謝隨!”
謝隨像是不控制似的,手按住了的后腦勺,將往自己邊攬,寂白將撐在他的膛,擋開了他的強吻。
“你再這樣,我不管你了!”
男孩這才像是回過神,立刻松開了,眨了眨長睫,說道:“剛剛就是想湊近看你,沒別的意思啊,別想多了。”
“……”
信他就鬼了!
謝隨看著孩得緋紅的臉頰,心變得有些愉悅。
Advertisement
寂白用力拍了拍他口的淤青,疼得他“嘶”了聲:“你太狠了吧。”
“沒你狠。”沒好氣地說:“轉過去,先涂背。”
謝隨乖乖地背過,孩將藥膏抹在掌心,用掌腹的力量,輕輕地在他背部大片的淤青上。
這些淤青到還是會有覺,謝隨的子下意識地了,不過他什麼都沒說。
寂白到他的疼痛,頓了頓,然后湊近他,邊涂抹藥膏,邊替他吹拂著。
謝隨著的涼意拍在他的肩胛骨,清涼又舒服。
“小白突然對我這麼好,有點不太適應。”
孩沒有應他,只是溫地替他著藥膏,謝隨低下頭,自顧自道:“那套西服,真的很好看,掛在櫥窗里我一眼就看中了。”
“我不會一直窮下去,你信我,我能配得上你。”
......
謝隨到后孩的作忽停,他側頭了。
孩低著頭,咬著白的下,劉海下,閉著眼睛,眼淚滲出了眼角,沾粘著細的睫,泛著水。
單薄的肩膀栗著,極力抑著,沒有哭出聲來。
謝隨的心“砰”地一下炸開,碎得稀爛。
寂白的手還落在他邦邦的肩胛骨邊,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哭腔被帶了出來,把嗆著了,咳嗽了兩聲,然后別過臉去。
謝隨忍不了了,他翻蹲到的面前,抓著的手,慌張地說:“我不講了,你別哭!”
寂白使勁兒掙開他的手,不過謝隨地抓著,沒有松開。
“小白,我再也不說這種話了,好不好。”
他以為寂白是被他的話弄哭了,其實并不是,寂白已經忍了好久好久,只是在那一瞬間驟然發了而已。
Advertisement
重生回來,沒有真心實意地掉過一滴眼淚,因為眼淚是最沒有用的東西,是弱者的武。
寂白要當強者,強者是不會掉眼淚的。
但是當看到謝隨上這大片的瘀傷,前世今生所有的悲傷和委屈,一腦涌上心頭,終于不住了。
謝隨不知道寂白心里的想法,他以為是自己講話把弄哭了,他手忙腳地用袖替掉臉上的淚痕,心疼得眉頭都蹙了小山。
寂白兀自哭了一下,便收住了緒,將他拉了起來坐在邊,繼續用藥膏替他拭傷口,一言未發。
謝隨垂眸著孩。
眼周紅撲撲的,睫被眼淚沾黏著,鼻息明顯重了很多。
謝隨從包里出紙巾,遞到面前,地問:“你要不要擰鼻涕?”
寂白將他手里的打掉了,原本想繃住,結果還是忍不住笑了。
他是個什麼魔鬼啊!
謝隨見笑了,心終于才輕松一些,他牽起寂白的手,按在自己口的位置。
“小白,你是不是心疼我?”
寂白沒有說話,的手緩緩地展開了,著他膛的淤青,隔著熾熱而致的皮,能到腔里那顆沉沉跳的心臟。
“你以后不要去打拳了。”寂白這句話說得分外認真,有咬著牙,一字一頓地重復:“不-要-去-了。”
謝隨無可奈何地嘆了聲:“你隨哥要掙錢啊。”
寂白斂著眸子,抿著,黑漆漆的眸子凝著他口大片的淤青:“謝隨,我養你。”
謝隨被“我養你”三個字給逗笑了,他低頭笑了很久,牽扯上的傷又有點疼,但他還是忍不住。
這小丫頭片兒...開什麼玩笑呢。
不過當他看到眉宇間認真的神,毫沒有玩笑的意思,角的笑意僵住。
Advertisement
良久,他低沉地喃了聲:“。”
這他媽說真的啊!
“寂白,你知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還是他第一次連名帶姓地喚的名字。
“我養你。”
謝隨咧咧:“自顧不暇的你,拿什麼養我。”
寂白認真說道:“你只管學習就行了,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學都沒關系,我...我會努力,我會為寂氏集團的繼承人!”
說出這話的時候,不只是謝隨,連寂白自己都驚住了。
從來沒有想過要和家里的姊妹兄弟爭奪什麼,他們的明爭暗斗和毫沒有關系,的初衷從來都是靠自己的本事獨立,離那個吸的家庭。
為寂氏集團的繼承人,完完全全就是另外一條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寂白不知道怎麼就說出了這句話,心里埋下的種子在這一刻破土發芽,為自己的野心到不可思議。
為繼承人,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謝隨的命運,能讓他們都過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這談何容易,寂氏集團旁系支脈眾多,家里兄弟姊妹中佼佼者更是不,這條路注定是...刀口。
謝隨他媽都傻了。
寂白不好意思地回過,將衛團扔到他的上:“你先穿服吧。”
謝隨拿著服,怔怔地反應了好一陣,然后向寂白,略帶欣喜卻又不可置信地說:“你他媽不會是想嫁給我吧?”
寂白沒看他的表,背過說:“你才幾歲你就想娶媳婦了。”
謝隨快速地給自己穿上了服,又拉了拉的袖:“我不想娶媳婦,但我想娶你。”
“哎呀。”寂白紅著臉甩開他的手:“你這小孩,滿腦子裝的都是什麼呢,想點正經事不行嗎。”
謝隨角的笑意漸漸漫開了,他將寂白拉到自己邊,兩個人并排地坐著,他知道寂白臉皮薄,于是不再說什麼。
微風吹拂著輕薄的紗簾,從隙中漫了進來,周遭籠著一層和的暖意。
靜寂的醫務室里,兩個人的心跳都快得不可思議,空氣有一曖昧的氣氛漸漸發酵了。
良久,謝隨突然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他轉過頭向寂白,不可置信地說:“我他媽是不是變吃飯的了?”
寂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起離開。
吃不吃。
**
教室走廊一側的窗戶邊,蔣仲寧忐忑地探出頭,著漸行漸近的謝隨。
他將外套拎在肩膀上,口罩也懶得戴了,眸子低垂著,淤青的角掛著一詭異的微笑,不知道在肖想著什麼。
蔣仲寧忐忑地喚了聲:“隨哥,沒事吧。”
謝隨睨了他一眼,沒有理他,高貴冷艷地回了教室,照例翻出了英文書。
看了幾個單詞,他角又彎了——
這小丫頭片子,都還沒長齊,還要養他呢。
叢喻舟趴在桌上,看著一個人坐那兒詭異微笑的謝隨,角了,干嘛呢這是...
“對了,我可能短時間不會去拳擊室了。”
兩個男孩詫異地著他——
“什麼?不去了?”
“真的假的?”
謝隨翻著英文單詞書,隨口說:“小白不讓我去,再說,快期中考了,我得復習。”
倆人看謝隨的目,跟他媽見了鬼似的。
蔣仲寧愣愣地問:“不是吧,隨哥,你玩真的啊,為了期中考這種東西,不去打拳了?”
叢喻舟說:“豬啊,人家的重點在前面那一句好不。”
蔣仲寧回想前面那一句是:“小白不讓我去了。”
看著謝隨這一臉欠揍的甜表,兩個男孩仿佛是意識到了什麼。
“你倆這就好了?”
“嗯。”
蔣仲寧大喊道:“行啊,玩得這一手苦計,666。”
叢喻舟了然地說:“還是小白心里有隨哥,不然你去使個苦計試試,看人家搭理你不。”
謝隨心相當愉悅,由得這二人科打諢開他的玩笑,也不生氣,向窗外蒼翠連綿的山隘,喃道——
“是,疼我。”
還要養他呢
**
那幾日,寂白每天都會把謝隨到空寂無人的小花園里,給他的傷口上藥。
上的瘀傷就算了,背上的那幾塊他不到的青紫,他這麼要面子,估計也不會別人幫忙,只能寂白每日監督著給他上藥。
叢喻舟看著謝隨每天下午最后一節課,提前半小時就開始守著教室正前方的掛鐘,一分一秒地數著,只要下課鈴打響,他第一個沖出教室。
謝隨子野,想讓他答應做違背自己意愿的事,難如登天,譬如上藥,之前幾個兄弟好說歹說,他死都不肯去醫院看看。
他骨頭,覺得自己能扛,沒有病痛和折磨能讓他屈服。
寂白不過一句話,瞬間折斷了謝隨的骨頭。
這可怕的。
……
謝隨一路狂奔跑到小花園,寂白已經坐在木椅上等候著,手里拿著一本古詩詞小冊。
垂著頭,側臉和,鬢間幾縷發被挽在了耳后,長長的睫覆蓋下來,蓋住了深褐的瞳子,看上去嫻靜溫雅。
謝隨看到邊的櫻花樹開得正盛,順手折了一段夾著綠葉的櫻花枝,走到寂白畔,將花枝遞到的眼前,晃了晃。
幾片白的櫻花瓣掉落到了古詩詞的小冊子上。
寂白驚喜地抬起頭,見了年清淺微笑的英俊臉龐。
謝隨將花瓣抖在了的頭發上。
“哎呀,你干什麼。”
“看著特。”謝隨自顧自地干著“好事”。
寂白推開了他的手,拍了拍自己頭發上細碎的花瓣,說道:“胡攀折是要扣行分的。”
謝隨鼻息間發出一聲輕笑,渾不在意——
“你信不信,教務主任的小黑本上,老子的分數早就負了。”
“你好意思講啊。”寂白嗔他道:“掙不夠行分,小心不能畢業哦。”
謝隨上了座椅,蹲在孩邊:“都他媽騙人的把戲,你還真信這個。”
“信啊。”寂白眸子宛如漾著水紋,清澈極了:“當好學生,不好嗎?”
“有什麼好。”謝隨說:“你喜歡被管著?”
寂白闔上了古詩詞的小冊子,揚長了調子,漫聲道:“我從小就被管著,如果沒有人管我,可能還會不習慣吧。”
那可巧了,謝隨從小沒人管,想做什麼做什麼,想怎麼活就怎麼活,恣意放縱又...孤獨。
“假如沒人管你,最想做什麼?”他問寂白。
“我最想...”孩低頭看著指間的櫻花瓣,思忖片刻,說道:“我想了服,去最最清澈見底的大湖里游個泳。”
像魚兒一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謝隨角咧了咧:“你這...好歹穿一件泳。”
“......”
“只是幻想而已,干嘛當真!”
謝隨笑了起來,似乎陷了某種沉思。
“謝隨,你在想什麼?”
“沒想什麼。”他矢口否認。
“你想了。”寂白拍了他一下,嗔道:“你想了!”
“好,好,我想了。”
他在想不穿服...該是什麼樣子。
寂白起想走,謝隨連忙拉住:“哎,給我上藥吧,月底快到了,我角這淤青,還沒消。”
孩將藥膏扔他手里:“自己涂。”
謝隨擰開藥膏,像牙膏一樣了一條在手上,直接擱臉上拍,寂白連忙拉住他:“誰讓你著麼多,是不是笨蛋!”
猜你喜歡
-
完結84 章

晨昏游戲
懷歆大三暑期在投行實習,對年輕有為、英俊斯文的副總裁驚鴻一瞥。——男人溫和紳士,舉止優雅,連袖口處不經意露出的一截手腕都是那麼性感迷人。足夠危險。但她興趣被勾起,頗為上心。同時也意識到這段工作關系對自己的掣肘。某天懷歆濃妝艷抹去酒吧蹦迪,卻…
32.1萬字8 6555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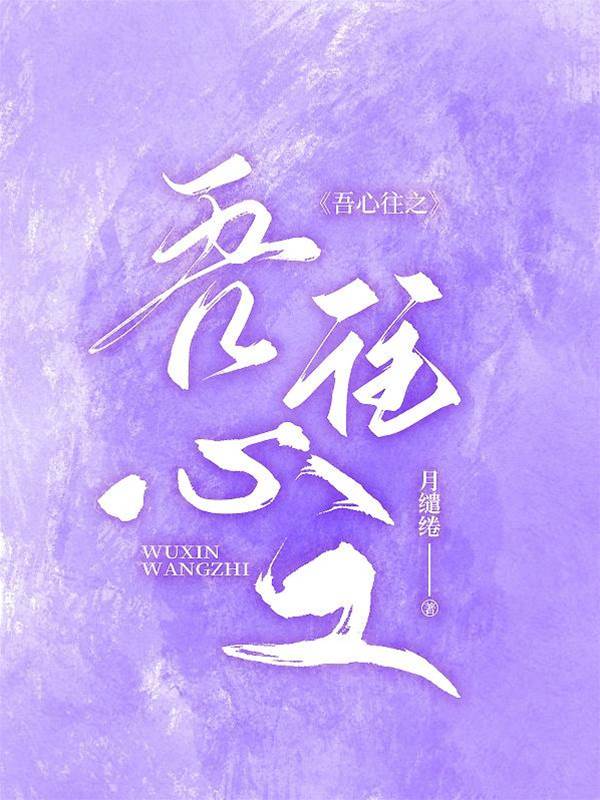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
完結740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和我圓房了
(1v1甜寵)她被渣妹算計,與陌生男人共度一夜。五年后,她攜子歸來,為了復仇,成了聲名顯赫紀家長孫的沖喜新娘。新婚夜,她被低調神秘的商界大佬宋時璟逼迫失身,才結婚就將植物人老公給綠了?直到后來,她才知道孩子的爹,商界大佬,竟都是她的植物人老公!
139.5萬字8.18 67920 -
連載380 章

陸少,你的閃婚妻子又跑路了
【先婚后愛+雙潔+追妻火葬場+帶球跑】【身世成迷的服裝設計師】VS【腹黑禁欲的京圈太子爺】 【處女作,輕點噴 評分剛出,后續會漲】 初戀突然提分手消失,親生父親變養父,母親的死因另有蹊蹺,所有的問題一下子全都砸向了慕南嫣。 她會一蹶不振?你想多了,她直接忘記前男友,擺脫慕家人,開啟了自己的新生活。 ** 慕南嫣去面試設計師助理,可是面試的基本要求居然是沒有整過容還必須是雛,誰能告訴她這和工作有什麼關系? 一場奇怪的面試,讓毫無關系的兩個人產生交集,為了各自的利益,兩人成為契約夫妻。 “慕南嫣,你居然敢給我戴綠帽子,你把我當什麼?” “陸逸然,我們離婚吧。” “你休想。” “慕小姐,你懷孕了。” 慕南嫣看著頭條新聞 【京圈太子爺與女子半夜出入酒店,疑似新歡。】 “陸逸然,此生我們不復相見。” 慕南嫣揣著孕肚跑了。 慕南嫣以全新的身份出現在了陸逸然面前 “陸總,好久不見。” “慕南嫣,怎麼會是你?” 曾經高高在上的京圈太子爺開始了他的追妻之路…… 本以為這次兩個人可以再續前緣,女主初戀突然回國,面對兩人,慕南嫣該何去何從?
70.6萬字8 1521 -
完結89 章

是你要換親,我成豪門千金你哭什麼?
上一世,蘇家公司倒閉,父母跳樓身亡,妹妹被首富收養,而我被普通司機收養。 所有的人都以為我這輩子完了,會一直活在淤泥里。 妹妹一定會錦衣玉食,享盡人間富貴,卻沒想到,她入豪門的第一天,就被傅氏豪門所有的人討厭。 甚至最后將她嫁了個變態殘疾人,落得個死無全尸的下場。 而我平步青云,成為炙手可熱的影后,甚至一度登上福布斯榜,擁有完美的婚姻。 這一世,妹妹飛快的跑向普通貨車司機,想搶走我上一世的人生。 得逞之后,她朝我得意一笑。 “姐姐,這一世,傅氏豪門還是留給你吧!” 我笑而不語,她重生,我亦是重生,能在一個普通司機家中翻身,走上那炙手可熱的影后位置。 還能嫁給權勢大人物傅霆之,哪有那麼容易… 很快,妹妹哭著回來求我,“姐姐,我們換回來好不好?”
16萬字5 8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