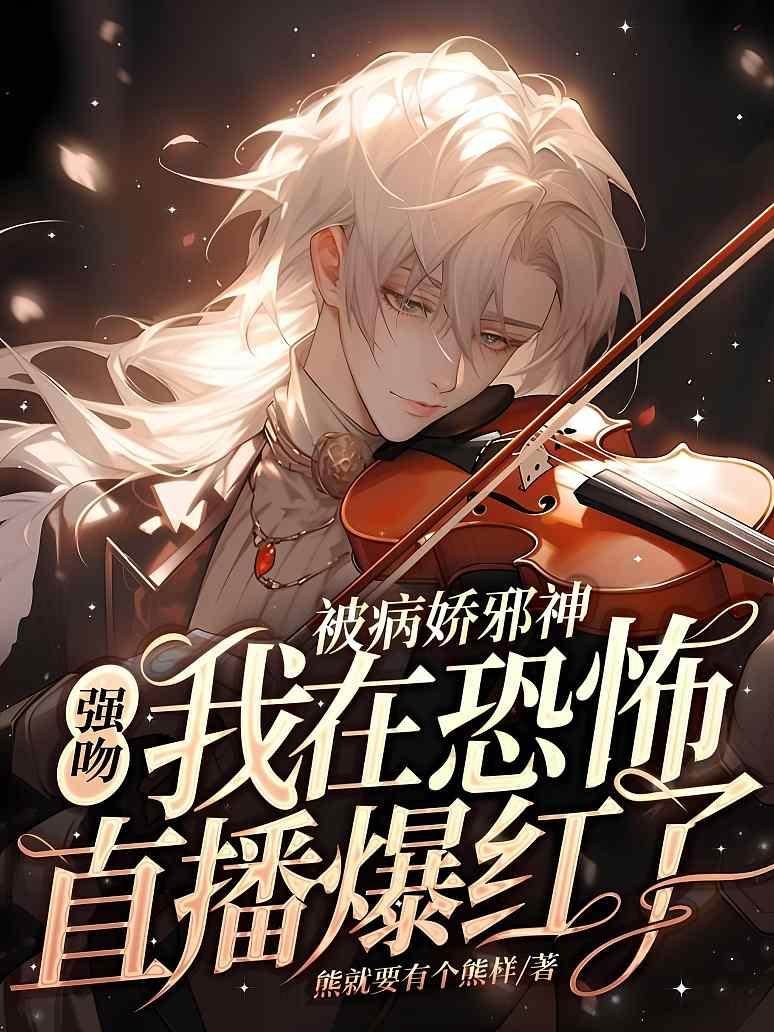《閨中記》 第122章
趙黼因關心切,見這般“曖昧”形,又驚又惱,便忙跳進房中,皺眉喝道:“崔云鬟!”
云鬟恍若未聞,也不答腔。
白樘轉頭看向他,神卻依舊沉靜清肅,只雙眸之中有些極淡的憂急疑之,淡聲道:“世子回來了?”毫無任何心虛不安之意,人也依舊未。
趙黼對上他寧靜無波的目,不知為何心頭那火氣也隨之冰了一冰,便沒有先前那樣高熾了。
嚨里那句話轉來轉去,出口之時,卻變了:“是怎麼了?”忙三兩步上前,便扶著云鬟肩頭,細看究竟,卻見雙眸泛紅蘊淚。
白樘見他護住了云鬟,才將按在云鬟肩頭的手撤開,順勢后退。
此刻清輝來至門邊兒,向行禮道:“父親。”
白樘一點頭,回頭看看兩人,便邁步走了出來。
清輝見他來到前,便把方才在行驗所里同嚴大淼趙黼三個所推的話說了一遍。
白樘定睛看了清輝半晌,眸中出幾分和之意:“這都是你想出來的?”
清輝道:“是世子跟嚴先生一塊兒所想,不知如何。”
白樘微笑:“甚好,你能想到這許多,很難得了。”
清輝得了贊揚,卻并不覺格外喜歡,因又看了一眼屋,見趙黼正俯打量云鬟,一邊兒低低在說些什麼,清輝便問道:“此又是怎麼了?”
白樘眼皮一垂,因道:“我方才同說了……這兩件案子的。”
清輝道:“崔姑娘因此不適了?”
白樘先是搖頭,旋即又點了點頭:“大概如此。”
此刻云鬟已經起,趙黼正道:“咱們走可好?”神里竟滿是關切,毫沒有先前的惱意。
清輝是知道他的,本以為他要如竹似的炸上一番,不想竟能在瞬間住怒火,化作一江春水,不覺有些驚奇。
Advertisement
這會兒云鬟抬頭,卻見眼前,兩側木格子窗著微,朱紅掉漆的門扇開著,白氏父子兩人就站在門檻之外,背后是靠院墻的幾棵梧桐樹,翠葉玲瓏,隨風微微搖曳,而那人跟桐樹都是一樣的端直清正。
——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
剎那間,心底竟無意識地泛出這一句。
那邊兒,白樘遙遙地看了云鬟一會兒,便問:“你好些了麼?”
云鬟道:“是。”
白樘道:“你不必懼怕,且再仔細想一想,若有所得,便來告知我。既然有世子相護,必然是無礙的。”
趙黼有些疑地著他,云鬟卻只是低眉垂眸:“是。”
不知為何,趙黼心里復又不自在起來,便握住云鬟的手道:“好了,走了。”對白樘一點頭:“白侍郎,告辭了。”
白樘拱手:“世子慢走。”清輝亦行禮相送。
眼見兩人形漸漸消失廊下,趙黼的手始終并未放開云鬟。
清輝雖七竅玲瓏,對男之事卻一竅不通,便問道:“父親,為何世子對崔姑娘如此不同?”
白樘道:“大概是年心,貪玩鬧。”
清輝道:“父親當真這樣想?”
白樘道:“怎麼?”
清輝沉默片刻,終于道:“崔姑娘心慈,只世子別害了。”
白樘意外:“為何竟這樣說?”
清輝搖頭:“孩兒不知。”
白樘輕笑了笑,并不探究此事,才進門,清輝忽然又問:“方才父親只跟崔姑娘說了案?”
白樘道:“不然呢?”
清輝道:“只是……”方才臨窗一瞥,那一幕雖讓趙黼火冒三丈,可在清輝看來,卻只覺心驚。
也不知為什麼,那一剎那,在他心底想起的,竟是三年前蔣府案之后,白樘借他之手把蔣勛請來府中……詢問蔣勛時候的那形。
Advertisement
雖不知如何會想這許多,但他有天生之,自是隨而發的罷了。
話說趙黼領著云鬟出了刑部,仍上了馬車。趙黼打量著,便問道:“你方才在里頭,是怎麼了?”
云鬟道:“沒什麼,我一時有些頭疼。”
趙黼想了想,道:“白侍郎真個兒把所有都跟你說了?你、都知道了?”
云鬟道:“是,都知道了。……不過我不知的是,既然此事跟我相干,世子為何竟瞞著我呢?”
趙黼道:“這案子詭異的很,我自然是怕你驚,倒不如讓他們悄悄地解決了好,誰知仍然不免。”
云鬟問道:“世子如何就知道他們會解決呢?”
趙黼想著白樘為人,笑說:“那可是刑部的白閻王,還有什麼是他無法的不?”
云鬟見他提起坊間對白樘的諢號,搖頭低聲道:“這個號不好。”
趙黼道:“好不好的,都是別人的罷了,又不是我給他起的……既然他跟你說了,那你又跟他說了些什麼?你可是答應過,要跟我說實話的。”
云鬟無法作答,索閉了雙眸,將子往車壁上倚靠過去。
此刻,雖人再車中,耳畔卻有輕輕地翻開書頁的聲響,一如那個午后,在王府的藏書閣,心慌意地找一本書。
不知翻了多久,終于才找到想要的,可是一時卻又不敢打開,通戰栗,手指都有些發抖。
云鬟自知道在上會有事會發生,自重生之后,偶爾思量前,越發明白:仿佛正是因為此事,才害了江夏王府,害此后種種。
是以在還未回京之前,就已經在為此事暗做準備。
之所以不愿回京,一來是因崔侯府并沒有令掛念的,二來,是為了避開昔日的那眾人,欠人的,人欠的,一筆勾銷最好。
Advertisement
而提也不能提的,就是這件事,這個“劫”。
只是想不到,趙黼從中作梗,竟讓的計劃打,仍是無法避免地回了京城。
自崔印忽然提出要送去家廟時候,已經心中微微有些波,只是并未就能往這上頭來想。
而趙黼突如其來的“橫一腳”把帶來世子府,更是讓不著頭腦。
直到那日,白清輝跟季陶然前往世子府,季陶然口中無意吐出一個“西城”,趙黼刻意支開……
后,當白季兩人因“又出事了”匆匆離去之后,他竟不自覺地握的手。
冥冥之中一線念,終于讓認真想起前生這一大劫關來。
那年才十四歲,約聽聞京城發生了幾件兒連環殺人案,因傳的不甚厲害,故而日子照常。
不料忽然,崔侯府發付去家廟居住,借口卻并非今世這個,而是因崔老夫人病了,故而送去給老太太祈福。
誰知,才在家廟住了半月,便出事了。
云鬟因深信自個兒的記憶,所以知道前世這一劫發生的詳細時間,——距離如今還有一年多的時候呢,因此起初并未聯想到此事。
可一旦想通之后,便打心底發起寒來。
后知后覺才發現:差點兒竟鑄大錯。
怎麼竟忽略了——比如由儀書院的案件,豈不是也提前了一年發生?既然如此,的劫難自也可能提前!
因想通了此事,竟汗倒豎,心神不屬,是夜,在世子府才又不夢前世之事,幾乎無法自噩夢中蘇醒。
可是細想,林稟正之所以提前一年犯案,是因為手白清輝跟蔣勛之事,但是“鴛鴦殺”……自問從來不曾沾手過任何。
既然如此,又是什麼促使了這兇殘的殺手也提前行了?
Advertisement
云鬟思來想去,無法明白,可卻也知道,躲避并不是辦法,因此才求了趙黼,相見白樘。
只因知道:能解決此事的,只有白樘。
回憶停在藏書閣里的那一刻,玉指微著翻開書頁,卻見跟先前寫得麻麻的字跡不同的是,這一頁上,只寥寥數行字。
某年某月某日,西城案,北門橋案,長安坊案。
——以上刑部結案,封,不祥。
當時看著這幾行字,心中又是悵然,又是微驚。
云鬟仿佛知道是誰一手將此案下,也只有他有此能耐,把這般驚天大案蒙在刑部之中,甚至連這江夏王府的冊之中,都無法記錄詳細。
不敢信是為了,但是卻覺著,那人之所以如此做,是跟不了干系。
話說回來,雖然時間都已經起了變更,可前兩案發地點,卻是沒有變化。
云鬟所能做的,僅此而已。
當按捺心頭恐懼,竭力回思往事,說出第三個可能的案發地之后,看見白樘的雙眸仍若深海,只是依稀有一道,如月沒。
云鬟約知道白樘的心意,可是不能說的是:其實白樘很不必這樣贊賞似的看著,因為就算沒有崔云鬟說這一個線索,以他之能,也遲早會破案。
畢竟前世,在危難之間,將從那兇徒手中救出的人,——正是他,刑部侍郎白樘。
云鬟閉眸沉思,面上雖看似平靜,心底卻有滔天波瀾。
不防趙黼在對面兒,卻趁機看了個飽。
竟還是不肯跟他說明白,他心里當然仍有些余惱,不過看著這張臉兒,目描摹過這般眉眼口鼻,卻反而把那余下的惱怒翻做了心花微開。
他挑著,含笑觀,手探出去,便輕輕握住云鬟的手腕。
的腕子還很細弱,卻如上好的羊脂白玉雕,他正翻來覆去打量,便聽云鬟道:“世子在看什麼?”睜開雙眸,把袖子一扯。
趙黼只得若無其事般嘆道:“你忒瘦了,崔侯府一定給你東西吃。不過不用怕,跟著我多住幾日,包管就養好了。”
云鬟輕聲道:“我好的很,相信白侍郎會很快破案,我自回侯府去,不必勞煩世子了。”
趙黼聽話頭不對,又抓住的手問道:“你如何這樣肯定?你跟白樘到底說了什麼呢?”
正在此刻,卻偏聽見馬車外有人聒噪道:“敢問車是晏王世子殿下麼?”聲音竟帶著些哭腔。
那車邊侍衛道:“什麼人攔路?還不滾開呢?”
那人因哭道:“若真是世子爺在里頭,還求世子爺救命!”
趙黼心里不耐煩,喝道:“滾!”
云鬟看著他,言又止。外頭那人又哭道:“求世子救命,救救我家公子,他給恒王世子擄去了,恒王世子說要弄死他呢!”
云鬟心中震,微微開車簾。
趙黼也聽出異樣,因探頭過來,往外一看,卻見路邊上跌跪著一個小幺兒,頭臉上帶著傷,鼻青臉腫的,向著馬車哀哀求告。
許是見了趙黼面,那小幺兒跪著撲上來:“世子救命!”又拼命磕頭。
云鬟看的心里不忍,咬了咬,看向趙黼。
趙黼正冷哼道:“老子又不是觀世音菩薩,難道還對你有求必應麼……”話未說完,對上云鬟的眼神,那目清澈之中,泛著幾許依依之意。
趙黼咽了口唾沫,道:“做什麼看著我?你心你去,前兒因你那薛哥哥,才得罪了我二叔,我可不想跟他們一家子杠的太死了。”
云鬟還未說話,那小幺兒因聽見了,便道:“正是因為世子救了我們公子,恒王世子才不忿的……”
趙黼聽了這句,因道:“停車。”
馬車這才停了下來,趙黼道:“你哭了半天,你們家公子是誰?”
那小幺兒連滾帶爬上來:“我們公子是暢音閣里唱花旦的薛小生,因為前日恒王來請,給世子殿下留下了,不料今兒恒王世子到了樓里,說我們公子忤逆恒王,不由分說把人拖走了。”說話間,淚水漣漣。
云鬟這才知道原來是薛君生!驚不小,忍不住道:“世子……”
趙黼掃一眼,懶懶道:“做什麼?用到六爺的時候,就好聲好氣的,等用完了,就一腳踹到不知哪里,擺出一張從不認得六爺的臉?這回我可不上當了。”
云鬟因見那小幺兒已經了傷,可見薛君生境危險,當下道:“我并沒有那樣。”
趙黼微睜雙眸,哼道:“沒有?那你方才是怎麼樣?我問你跟白樘說了什麼,你可理過我?”
云鬟知道他是故意發難為難,便低頭道:“你想怎麼樣?我向世子賠禮可好?”
趙黼道:“賠禮是個什麼,我可不稀罕。”
云鬟呼了口氣,探手握著他的手腕:“世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趙黼瞄了一眼的手,卻又鼻孔朝天道:“老子又不想仙佛,不稀罕不稀罕!”
云鬟見他始終不為所,便撒手要出去。
趙黼眼疾手快,一把將拉住:“你做什麼?”
云鬟道:“我救人去。”
趙黼道:“你怎麼救?”將打量了一回,道:“先前說我二叔葷腥不忌,可知我這位哥哥,也是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你這樣過去,簡直就是羊虎口,他高興還來不及呢。”
云鬟紅了臉,卻淡淡道:“我求別人幫忙就是了。”
趙黼眼神一變:“你求誰去?”
云鬟本有幾分賭氣,忽地見他有些變,心中一,就說:“小白公子面冷心熱,多半肯援手。”
趙黼嗤之以鼻,冷笑道:“他雖然肯,只怕也白忙一場。不中用。”
云鬟飛快一想,鄭重道:“還有一人,必然會幫。”
趙黼斜睨,疑心要說的是白樘。
不料云鬟道:“靜王爺必然使得。”
趙黼大吃一驚:“你說什麼?”
云鬟道:“我可以求靜王爺出面兒,想恒王世子雖不怕六爺,可面對靜王爺,應該還是不敢造次的。”
趙黼擰眉細看:“你幾時跟我四叔認得了?”忽地想起上回王妃邊兒雙喜的話“好多人夸贊呢,比如恒王妃……還有靜王爺”,一時狐疑不定。
云鬟淡淡道:“這個就恕我不能告知了,還要去求靜王爺呢。”
趙黼見又要走,咬牙發狠將拽了回來,喝道:“你敢去求別人?”
云鬟不防,竟撲倒在他上,便嗅到他上淡淡的味道,如此激烈而悉,簡直像是前世里穿過來一只手,狠狠打在心頭一樣,手忙腳要爬起來。
趙黼偏又把拉住,盯了看了半晌,忽地笑:“知道了,你是使壞故意激我呢?”
車廂本就不大,他偏靠得這樣近,呼出的氣息微微暖,上那凜冽之氣也越發濃了幾分似的。
云鬟按捺有些慌的心意,垂眸道:“并不是,救人如救火,哪里敢玩笑。”
趙黼眼神變幻:“縱然你有手段說服我四叔,那也得需要時候,再說這會子他也未必就在王府,再三耽擱,只怕有十個薛君生也不夠殺。”
云鬟擔心的正也在此,趙黼眸中含笑,挑道:“求我啊,方才不是說要去求靜王麼?”
云鬟不得他如此眼神,這般口吻,轉頭道:“方才已經求過了,是世子不肯答應。”
近距離瞧著,可以看清外頭進來,照在半邊臉頰上,那晶瑩如玉,近乎明,鬢邊細細地絨發,浸潤芒中,很引人眼。
趙黼目晃,呼吸不由急促了幾分,心里仿佛也窩著什麼,輕輕。
云鬟察覺,眉尖蹙起:“世子?”
趙黼忙撒手,后退回去,自也靠車壁坐了,垂眸暗中調息。
外頭那小幺兒仍聲聲地求告,街邊上已經有許多看熱鬧的人圍了過來,云鬟吃不準他究竟是何心思,忍不住喚道:“六爺……”
趙黼聽溫婉一聲,子微微一,額頭便冒出汗來,雖閉眸不語,耳朵尖兒卻已經紅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36 章

我把驚悚世界玩成養成游戲!
一股神秘力量降落地球,誕生了另一個驚悚文明世界。 每個人十八歲都會被強制送入驚悚遊戲世界。 當所有人沉浸在恐懼之中,夾縫中求生時。 秦諾卻發現自己能通過左右鬼的情緒,獲得系統獎勵,並且每完成一次副本,就能在驚悚世界建立自己産業。 於是, 陰泉餐廳當傳菜員、 死亡醫院當主治醫生、 冥間酒店當服務員、 恐怖高校當教課老師…… 當秦諾瘋狂去完成一個個副本時,最後突然發現,自己竟成了鬼界巨擘。
196.1萬字8.08 50457 -
完結300 章

等到青蟬墜落
七年前的一個深夜,刑警李謹誠在城中村神祕失蹤。 陳浦是李謹誠最好的兄弟,爲了找到他,七年來不談戀愛,不享樂,不升職,打死不離開城中村。 後來,陳浦所在刑警隊來了個新人,是李謹誠的妹妹。 —— 有一天,當我再次目睹青蟬從枝頭墜落,欣然走向那些螳螂身後。 我決定成爲捕獵者。
48.7萬字8 2410 -
完結503 章

靈魂禁區
夜幕掩映,物欲橫生。她是游走于生死邊緣人人覬覦的性感尤物,他是游手好閑,坦率輕浮的富二代。愛與欲的紐帶兩兩個人緊緊聯系,一場關于死亡的游戲,從今日起,惡魔給你一個別樣的機會。恭喜收到死亡游戲的邀請,這是來自地獄的邀請。經歷了人世間的痛苦離愁,原以為一切會拉下帷幕,很可惜這才剛剛開始。
131.6萬字8 315 -
完結7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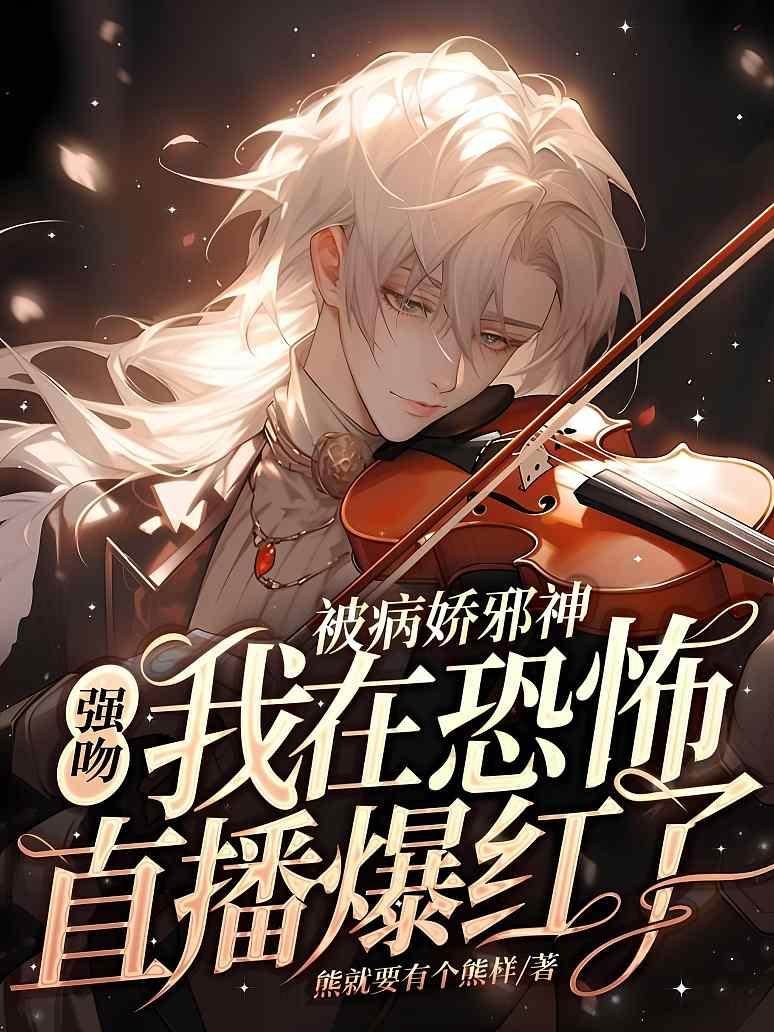
被病嬌邪神強吻!我在恐怖直播爆火了
桑榆穿越的第一天就被拉入一個詭異的直播間。為了活命,她被迫參加驚悚游戲。“叮,您的系統已上線”就在桑榆以為自己綁定了金手指時……系統:“叮,歡迎綁定戀愛腦攻略系統。”當別的玩家在驚悚游戲里刷進度,桑榆被迫刷病嬌鬼怪的好感度。當別的玩家遇到恐怖的鬼怪嚇得四處逃竄時……系統:“看到那個嚇人的怪物沒,沖上去,親他。”桑榆:“……”
123.3萬字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