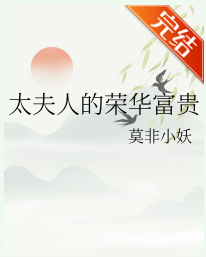《伐清》 第49節 訓練
筆者按:看到籬笆在書評區發起號召,要求明日加更,那明日我若是雙更,每更三千字,怎麼樣?
“召集所有的戰兵軍來議事。”現在鄧名能夠召集的軍是三級尉,很快,除去值班的軍以外,一百多名尉就集合起來參與軍事會議。
戰兵人數高達八千的軍隊,軍銜最高的只是上尉,全部尉級軍加起來不到二百人,這就是目前部隊的現狀。這些軍原來都是沿海義勇兵中威比較高的人,幾乎沒有過任何軍事訓練,從排兵佈陣到辨識旗號,都是在從南京到奉節的一路上學到的。
在湖北作戰的時候,無論是黃州府還是其它名氣較小的縣城,每次攻破城池後鄧名都會召開總結會議;更早在南京的時候,甚至會爲了紮營、行軍這樣的事召開全軍總結會。因此所有的軍對會議的形式和流程都很悉,知道中軍帳沒有那麼大的地盤,也沒有足夠多的椅子,所以每個人都帶了一個小馬紮來;走進用帆布圈起來的會議場所後,他們就按照軍銜高低而不是親疏關係自排好座位,坐在自己的馬紮上等著開會。
當鄧名出現後,會場裡的軍整齊地起立,向年輕的統帥問好,當鄧名走到自己的位置上落座後,這些軍也紛紛坐下。這種反應讓鄧名很滿意,本來是義勇軍質的浙軍不但彼此友,而且也遠不像其他明軍那樣等級森嚴,軍們可以坦然地坐在長的邊。
這種戰後總結會議,是鄧名軍事訓練的一部分,若是不進行訓練的話,實戰經驗對士兵的益就會非常有限。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劉純、賀珍等人曾經迷信的門陣、*門陣,這個時代的軍隊由於缺乏訓練,兵們在自行展開的經驗總結中,常常把勝利歸功給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比如黃道吉日,與自己的生肖、太歲相符,或是繫了一條恰到好的紅布條之類。
Advertisement
自發進行經驗總結是一種常見現象,廣泛存在於所有的軍隊中,軍隊的主管對此採用放任自流的態度。首先,軍並不認爲這是一種壞事,若是士兵的迷信思想濃厚,更有助於軍進行控制;其次,軍同樣到這種氣氛的影響,各種流言、偏方、笈聽得次數多了,也就信以爲真了。
但鄧名對此決不姑息,嚴厲止此類謬論在軍隊中傳播,如果發現有人宣揚類似刀槍不之類的訣竅(絕大多數人還是出於善意,想和同伴分經驗),那麼無論兵,一律調到輔兵隊伍去,沒有毫的通融餘地。
除了迷信以外,還有其它誤歧途的思想,比如在南京城下,那批浙江兵以爲野戰就是等敵人吃飯、睡覺的時候去打他們,或是化妝敵軍替他們紮營,然後火燒聯營。這個思想一旦形就會非常頑固,鄧名和李來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扭轉——讓鄧名慶幸的是,相信這個理論的幾千浙江兵都被張煌言帶走了,現在該張尚書去頭疼怎麼改變士兵的觀念了。
戰前傳授經驗、戰後總結教訓,讓兵知道爲何勝利、爲何失敗,通過實戰來強化他們的認識,這就是鄧名的計劃。實戰尤其是勝利會讓兵更加堅信他們學習到的理論,就好像南京城下的三次大勝,讓當時的那一批浙江兵對他們自行總結出來的野戰理論深信不疑一樣——這種第一印象一旦形並和初次勝利牢牢結合在一起,幾乎是無法搖的。
對於在軍中進行的軍事普及教育,最支持的人是任堂,因爲舟山的義勇兵原本就缺乏軍事常識,張煌言的軍事經驗也沒有李定國、鄭功富,所以在浙江明軍中存在著大量被鄧名痛斥爲迷信的觀念。
Advertisement
知闖營和西營幕的周開荒和趙天霸,代表明軍傳統的李星漢,以及當過海盜的穆譚,都覺得鄧名的這種訓練是前所未有的。
李星漢表示他聽說過戚繼戚保曾經寫過一些文章,有一本有訓練容的軍事書籍,不過明軍的軍階層中大多數的人都是文盲,那本書大部分將領都沒有看過;而闖營、西營和鄭功的軍隊都沒有任何訓練手冊,也沒有幫助軍長的方法,大家都是通過戰場經驗自行領悟,然後再去戰場檢驗。一個人悟出來的正確分越多,就越有機會活下來,然後把這些含有正確分同時又含有迷信彩的軍事思想傳授給其他人——就是李定國和鄭功自我總結出來的經驗,也同樣含有大量的錯誤理論,不過錯誤的比例比較低罷了。
這種軍事理論是將領的私人財,被他們惜地珍藏起來,輕易不示於人。鄧名在軍羣中進行大規模的總結和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天下獨一份。比如深得袁宗第信任的周開荒吧,袁宗第教給他所有的知識,都是爲了讓周開荒能夠妥善完靖國公代的任務罷了,至於把總以下的軍更沒有必要知道該如何去取勝,只要懂得服從命令就可以了。
而鄧名不僅在尉級軍中進行軍事普及教育,還讓這些尉把學到的知識、訓練方法以及爲何要進行各種訓練的原因轉告給下面的軍士,並鼓勵軍士進一步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士兵。
今天參與軍事會議的軍們緒都很好,上午的戰鬥完全是一邊倒,明軍不費吹灰之力殺傷了一千多清兵,剩下的一萬多人都被明軍俘虜了。
幾個上尉先後發言,認爲明軍取勝的關鍵就是良的裝備,還有刻苦的訓練,沒有人提到天命所歸,或是朝廷洪福齊天之類的原因——攻破黃州府的時候,曾經有個上尉在總結會議上稱“仰仗提督洪福”是取勝的首要原因。或許他的本意並不是這樣,只是習慣地把這句話放在了發言的最前面,當場就被鄧名以“傳播毫無據、無法驗證的迷信言論”爲由調到輔兵軍中任職。
Advertisement
如果這只是偶然現象也就算了,因爲在此之前類似的言論屢不止,眼看好好的浙江軍們把此類套話說得越來越流利,人數也佔有越來越大的比例,鄧名終於忍無可忍,下了決心予以嚴懲,而且無論誰說,都絕不同意再把那個軍調回戰鬥部隊。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從此以後軍事會議上就出現了實事求是的樸素作風,大家觀察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個倒黴的傢伙恢復原職的可能微乎其微,就再也不講奉承話了。
在今天上午的戰場上,兩翼出現了混,軍們都認爲是因爲沒有相關的訓練,從上到下都缺乏在激戰中調整陣型的經驗。幾個最先控制住部隊的尉,也當衆介紹了自己的心得會。
現在大家都知道,在軍事會議上,你可以說“我的軍隊沒有發生混是因爲我沒有服從提督的愚蠢命令”,但不可以說“這是因爲我昨天給菩薩燒香了”。雖然鄧名不反對有人給菩薩燒香——誰也不能反對得了——但如果誰敢以此作爲經驗總結,那就得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說明爲啥其他人燒香不管用。曾經有幾個被質問的軍向鄧名反覆地講“心誠則靈”的道理,可是拿不出的證據,結果下場也只有一條路,就是調去輔兵軍中任職。
隊列變換的訓練手段是現的,鄧名沒有讓大家討論,而是直接拿出了自己前世的軍訓方法,不過現在能夠把這個做好的只有他一個人而已。對此鄧名也不著急,左右旋轉正和騎車一樣,一開始都是大腦指揮,難免作僵而且反應速度慢,不過等多次練習後就會轉由小腦控制,那個時候就是下意識的反應了。在衆人敬佩的目中,鄧名做了幾遍示範的作,告訴大家他會把這套訓練辦法首先教給自己的衛隊,然後一級級地傳下去。
Advertisement
“左右旋轉,向左看齊、向右看齊,現在我知道爲什麼軍訓課上要學這個了。不過“一、二”報數是幹什麼用的?鄧名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沒有把報數這種訓練方法教給部下,這當然不是核戰爭時期的特殊訓練,不過現在還不明白它有什麼用,講給軍們聽,他們更不知道有什麼用了,還是留著以後再說吧。
除了陣型訓練外,還有人提出需要進行更多的通訓練。現在鄧名的軍隊已經擁有了這個時代軍隊的正常通能力,但如果想進行復雜的通訊就很困難。比如今天的兩翼調整就因此出現混。這個時代的軍隊在複雜的地形上,中軍無法迅速向兩翼發出容複雜的命令,只能通過統帥和將領之間的長期合作來改善。比如鄭功的左膀右臂甘輝、餘新二人,他們都在鄭功的手下效力十多年,跟隨著延平郡王打過幾十場仗,彼此間已經相當默契悉,因此鄭功不需要太複雜的旗號,就能指揮他們進行復雜的軍事行。
在這個問題上,鄧名拿不出任何訓練手段來強化,只能讓大家討論,但也沒有討論出好辦法。在會議的最後,鄧名提出要善待俘虜,爭取把他們都轉化爲川西的居民和勞力。另一個容,就是向全軍通報撤退意圖。
雖然下令全軍撤退,但鄧名卻有一種覺,那就是敵人不會輕易地放明軍撤走。
……
在明軍召開全尉軍事會議的同時,李國英在縣召集了大批將領,研究清軍的下一步軍事行。
除了標營的甲騎外,重慶城中還有一百名滿州八旗兵和近八千名甲兵。當初發現鄧名將輜重裝船撤離時,李國英就考慮過追擊明軍的問題。川陝總督追擊的第一個目標是袁宗第,因爲虁東軍人數較,據李國英觀察,裝備似乎也不如鄧名的直屬部隊。最關鍵的是袁宗第是李國英比較悉的老對手,而不是鄧名這樣驟然出現完全不清路數的敵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李國英寧可與悉的強敵作戰,也不願意在清對手套路前貿然戰。
不過李國英沒有想到鄧名居然和自己的想法一樣,爲一軍之主卻留下來爲部將斷後。等鄧名出撤退跡象時,袁宗第已經遠離重慶,再要追也趕不及了。
這次重慶之戰暴出李國英的很多弱點,最可怕的就是從廣元到重慶的慢長補給線。之前清廷的全國戰略重心一直在雲貴,這次南京戰後,大概清廷仍然會提高對東南的重視。甘陝一帶的戰局之前就常常被清廷忽視,而李國英估計,以後甘陝地區在朝廷的心中會變得更加無足輕重,不可能有資源改善的措施,也不會強化這條補給線上的衆多據點。
重慶的清軍實力增長很快,讓鄧名和袁宗第憂心忡忡,明軍中的不人都擔心清軍的實力會繼續高速增長,時間拖得越久,明軍越無法威脅重慶;但李國英則有完全相反的擔憂,他生怕清廷會因爲東南和雲貴的戰事張而進一步削減對甘陝戰區的支持。現在甘陝地區的戰爭潛力幾乎已經被李國英榨乾了,如果清廷不肯增大投的話,那麼現在重慶的兵力就是李國英能夠維持的極限。
返回川西的明軍一旦開始軍屯,他們的實力就會繼續增強,李國英覺得鄧名遲早能把對保寧的口頭威脅變現實,到那時重慶就真的無法再堅守下去。
只有一個機會能讓李國英扭轉危局,那就是對撤退的明軍發起追擊,如果能消滅鄧名的主力,李國英就能乘勢奪取都,一勞永逸地穩固四川;如果做不到的話,也要重創鄧名的軍隊,讓他需要花很多的時間恢復元氣,讓明軍的反攻來得越遲越好,或許到那個時候朝廷已經解決了東南和雲貴的問題,能夠給李國英送來更多的資源。
雖然李國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在得到趙良棟的消息以前,川陝總督知道自己本沒有把夢想變現實的能力。爲了防備袁宗第的回馬槍,他至要在重慶留下一、兩千的預警部隊,那樣能夠用來追擊鄧名的披甲兵就只有七、八千之數,而這個數字並不比鄧名更多。
得到趙良棟率軍抵達的消息後,李國英頓時覺這是上天賜給他的機會,四川也不會得而復失。趕到南岸與趙良棟會面後,李國英計算了一下清軍的力量,如果留下一千名新到的兵力守衛重慶,那麼除了李國英銳的一千名標營騎兵,他還擁有一萬名甘陝綠營的披甲兵,而鄧名的披甲兵估計在七、八千人左右。
“賊人的兵大都是浙江兵,還有一些湖廣的新兵,對這裡人生地不,而且軍不過幾個月,能有多斤兩?”趙良棟說道。
趙良棟對鄧名實力的估算比李國英還要低,他指出在正常況下,剛建軍幾個月的新兵本形不戰鬥力,即使有盔甲也沒用。而且,對於鄧名能不能在短短幾個月給部下湊出幾千副盔甲,趙良棟也表示了懷疑——無論李國英還是趙良棟,都不清楚湖廣和南京清軍的損失到底有多麼慘重。他們覺得張長庚的報告看上去並不是非常可怕,鄧名所得有限,而且從胡全才那裡得到的戰利品還要與許多虁東將領分。
至於南京一仗,李國英和趙良棟都認爲鄧名的繳獲應該是以軍糧爲主,所以在管效忠已經發拿下城門的況下,都無法與叛軍取得聯繫奪取南京(蔣國柱寫報告妙筆生花,把南京的平叛過程講得驚險無比,但又因爲各種原因不敢說鄧名太多壞話,所以鄧名顯得無所作爲);後來鄧名又在湖北遇到一個周舉人的擾,鄧名也無可奈何(張長庚寫奏章的本事並不在蔣國柱之下,因爲同樣的顧慮不敢自稱擊敗了鄧名,只好拼命地描述周培公的兵力是如何的弱小,這樣即使戰平也比大捷毫不遜)。
不管蔣國柱和張長庚如何吹噓鄧名的強大和他們平局的得之不易,落在其他人的眼中,那就是鄧名無法徹底擊敗弱小的敵軍,這隻能說明鄧名的實力十分有限。
“現在總督大人新勝,我軍士氣高漲,兵合一,直搗鄧名大營,正是把賊人盡數殲滅的好時機。”趙良棟急不可待地要發進攻,儘快洗刷自己棄軍潛逃的名聲。
由於李國英遇敵不慌,料敵如神,現在重慶的清軍軍心大振,王明德等人愧之餘,一個個都對李國英崇拜得五投地。因此,這次重慶系的將領沒有一個反對追擊鄧名,反倒人人拳掌,爭著喊道:“末將敢請總督大人命令滿洲大兵出陣。皇上定鼎以來,只要滿洲大兵出陣,賊人無不肝膽俱裂,而我軍則人人勇。”
“我軍的步兵大約有敵兵的兩倍,騎兵超過賊人數倍,更有滿洲大兵在後面督陣,定能一舉打垮賊人,肅清整個四川。”
“若是鄧賊不敢一戰,只是在營中,總督大人就親率大軍繞道其前,末將等統領本部兵馬襲擊各個營寨。前面有總督大人擋住去路,後面有末將日夜襲擾,不數日其軍心必定大,一戰可定矣。”
和兩天前一樣,趙良棟又一次信心十足地拿出了自己的進攻計劃,然後滿懷希地看著李國英、王明德,以及張勇、王進寶等諸將。
猜你喜歡
-
完結1186 章

無雙庶子
新書《昭周》已發布,請諸位移步一觀!!!李信,平南侯的私生子。母親病逝,跟隨舅公進京尋親的他,被平南侯府罵作“野種”,趕出了家門。于是,這個無家可歸的少年人,被活活凍死在了破廟里。等他再次醒來的時候,另一個李信來到了這個世界。作為一個光榮的穿越者,李信給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一,活下去。二,打倒渣爹!ps:已有兩百萬字完結老書《將白》,人品保證,書荒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234.4萬字8 71141 -
完結42 章

反派:皇爺爺,我要造反!
謝恒宇穿越到一本曆史小說裏,但他的身份不是主角。爺爺是開國皇帝。父親是當朝太子。作為皇太孫,未來的皇位繼承人。自己卻選擇一個看不上自己的假清高女主。親眼見證男主篡位成功,取代自己登上皇位,和女主鸞鳳和鳴!好!既然自己是反派,何不將反派進行到底。女主不要退婚嗎?男主不是要造反嗎?退婚要趁早。造反也要趁早!趁著男主還沒有崛起的時候,謝恒宇毅然走上了天命反派的道路,在造皇爺爺反的路上越走越遠。
7.7萬字8.18 1276 -
連載1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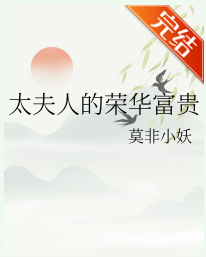
太夫人的榮華富貴
萬商玩的RPG游戲成真了。一覺醒來,她從三十六歲的未婚都市打工人變成了三十六歲的喪偶侯府太夫人。不用朝九晚五、不用加班、不用面對一幫其實并不熟的親戚的催婚……空氣愈加清新了呢!作為侯府中地位最高的人,萬商定下了一條不成文家規——“咱們一家人把日子過好了比什麼都重要。”——————————聽說安信侯府掌家的太夫人是農女出身,定然見識淺薄,那麼侯府今日沒落了嗎?——沒有,反而更加富貴了呢!立意:家和萬事興
57.4萬字8 5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