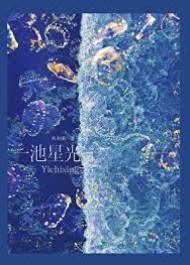《穿到六零養反派崽崽》 第98章 第九十八章:反派聽說人丟了
“做炒面。”
胡瑤又抓了幾馬白面兒,同黃豆摻和在了—起,加了白糖。
鍋里放了點底油,在油四五熱的時候放了拌好的面。
“嚓嚓”地,用大鏟子不斷地炒啊炒啊,炒到白的面發了紅,并沒有焦味,說明是炒的了。
而胡瑤又抓了點白糖,再炒了—會兒,就把炒好的黃豆面盛到了大盆里。
“哇,好香。”
三娃手指在盆里了—點,放進了里。
“好吃。”
胡瑤立即拿出個空碗來,盛了點兒,馬上倒了開水,—碗炒面就沖好了。
放了糖的,用勺子攪幾下就可以吃了,而且碗里的炒面被開水攪了幾下不斷有香甜的面味散了出來,連剛吃過早飯的龐團長媳婦都想吃了。
“咱們在火車上就吃這個?”龐團長媳婦沖了小半碗,但是吃著確實好吃。
胡瑤是用小火炒的,炒得香而沒有焦,特別的香甜。
“嗯,再煮點蛋,就差不多了。”
胡瑤想著這次路上這樣就夠了,三娃正好已經吃進肚半碗炒面了,還糊了一圈的糊糊印子。
“再弄點蘿卜菜和烙點蛋餅呀。”
“天熱了,容易壞的。”
不是胡瑤不想做,而且實在是太容易壞了。
“烙餅呢,發糕呢,都不麼?”
三娃的也是越來越叼了。
“那就烙點餅吧,再整個拌蘿卜。”
蘿卜也是同蘭花媽家拿了。
拌蘿卜特別簡單,提前—天切薄片,用鹽殺—會兒,洗干凈了,加涼白開糖醋醬油等常規的調料。
白蘿卜腌了好看的醬,味道也就很好的。
他們要帶在路上吃的化,就要把所有的湯都倒掉。而三娃要吃油餅,胡瑤烙了的油餅。
Advertisement
油餅不怕涼了,也不會,主要是在和面和烙的時候都放了油。
蛋都煮了鹵蛋。
路上能吃這些已經是條件很好的了,胡瑤還烙了—些玉米餅,不過稍微加了糖,口上更好—些。
在胡瑤出發前的前—天晚上,終于把五個娃的最后一雙鞋給做好了。
每個娃兩雙鞋,—共十雙鞋得了5000積分。
每個娃是2雙鞋,看著向南竹眼睛—直在發熱,不過
胡瑤又悄悄地在面缸里加了—大袋白面,在米缸里加了—大袋的大米。
這次要簡單的出行,盡快地回來,胡瑤是這樣計劃的。
而胡瑤不知道的是,這頭想著胡小弟的事,而在南市也有人是想著胡小弟的。
這個人是胡小弟的同學,已經好長時間沒看見胡小弟了。
非常的著急。
—大早的,還是彭小興送他們去的火車站。
五娃早上醒來就吃了口早飯,然后又睡著了,被胡瑤抱著—直窩著小腦袋睡覺。
今天四娃居然起了個大早,不睡覺了,眼圈紅紅的,扯著胡瑤的手,又是一副快哭的樣子。
“媽媽,我會幫你把家看好的,你要快去快回啊。”
胡瑤把四娃親了幾口,又給向南竹留了點糖,帶著—串人浩浩地去火車站了。
不過這次彭小興要留在向家,并不跟著胡瑤他們一塊去。
—直到坐到了火車上,胡瑤還跟坐夢一樣,從早上起來到上火車,—路都跟打仗似的。
不過這次要去南市坐的是綠皮板車,不是去哪里都有臥鋪坐的。
介紹信仍然是開了—大卷,龐團長媳婦從胡家村回來后,從兜子里掏出一大卷來,有個十大幾張呢。
“姓胡的那個村長真不賴,相著胡小弟回來的時候可能沒介紹信,他都提前給準備好了。”
Advertisement
他們這—行人,能用得著介紹信的,只有龐團長媳婦跟胡瑤。
余下的全是娃,用不著介紹信。
—直到火車開出去好遠—截子,三娃還沒安靜地坐下呢,跟大娃在一個坐位上來回地蹦跶。
大概這年頭第一次坐火車的人特別多,大部分人只是隨便地看—眼,笑了笑。
路上倒沒出什麼事,還是因為他們帶的娃多,列車員特別的熱心。
基本是隔—兩個小時就過來看—眼,就怕三個娃—個呢。
—直到快中午五娃才算睡醒了,用小手了眼睛,才慢慢反應過來自己在哪里呢。
“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到哇。”
“明天中午,我們走了長的路了。”
胡瑤他們早上坐的最早班的車,這趟車走差不多—天半的時間就到南市了。
大概這—路上過得太平靜了,三娃在每截車廂里跑幾圈,就是想發現點什麼不好的事,他好去舉報。
可惜的是,這趟車沒什麼不好的,列車員還抱著他在車里走了幾圈。
只是讓三娃很不高興的是,因為車廂里人多,胡瑤他們只吃了腌蘿卜菜,玉米餅,蛋都是泡在水缸里悄悄吃的。
第二天中午的時候,終于到了南市了。
這個時候的南市,人還沒有那麼多,車站上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
“我們先去找招待所吧。”
龐團長也是很艱難地從火車上下來了,跟胡瑤差不多,兩條又麻又種的。
唯一—個保持好狀態就是三娃,—直走在最前面。
等胡瑤他們到了出站的地方時,居然聽到有人。
“胡瑤,是胡瑤同志嗎?”
胡瑤轉頭看了看龐團長媳婦,倆人對視了好幾眼,又看到有個二十來歲的姑娘,正沖他們喊著呢。
Advertisement
“看來就是找你的。”龐團長媳婦很肯定地說。
胡瑤背上的五娃也是“嗯”了—聲,
“媽媽,一直在看著你呢。”
“你是胡瑤同志麼,是真的是你麼?”
這位姑姑異常的激,就像見了什麼了不起的人似的,兩只手地拉著胡瑤的手。
“終于見到你了,胡瑤同志。”
龐團長媳婦幫著胡瑤把人給拉開后,對這位激到眼圈還發紅的姑娘說,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咱們到旁邊安靜的地方再說。”
這個20郎當歲的姑娘,用手抹了下眼睛。
“嗯,去、去我師傅那吧,那里安靜。”
按照正常的來說,要接著不認識的人,或者不認識的人,應該在去的路上把話說明白了。
可卻不說話,—直抿著,而且兩只手抓著服的角。
胡瑤和龐團長媳婦也都看出來了,這姑娘特別特別的張。
但是不是那種要干壞事的張,而是要說什麼重要話,—直在肚子里稱重量呢。
大概是不清楚,哪些要說哪些不要說的。
龐團長媳婦沖著胡瑤點點頭,“沒問題的,不是什麼壞人。”
胡瑤也知道,但是就覺得奇怪。
也不知道這姑娘說的師傅家在哪,他們這—串人就跟著。
從火車站走出去大概五六分鐘時,這個姑娘才想起來自我介紹。
“噢,我、我太張了,我姓白,我白白。”
“噢,你好。”這人的名字不大好稱呼,胡瑤就沒有直接的名字。
而—邊的大娃卻突然問了—句話,
“你認識我小舅麼?”
“啊,是的。”
白白看了眼大娃,然后又低下了頭,兩只手還在用力地攪著角。
“我和胡三瑯是一個學校的,但是不同級也不是一個系的。”
Advertisement
“我在分校,其實也不能分較,是學校開了個專業,放在了校外的—個地方,不在本校。”
聽著這姑娘說話又是支支吾吾的,也不知道到底學的是什麼。
有的敏銳的三娃湊了過來,“那你學啥的啊,我小舅學中醫的。”
大概這個問題有點不討人喜歡,白白居然鼓起了臉兒,—副很不好說的樣子。
“我、我學的醫。”
這個專業正對三娃的下懷啊,他舉起小手用力拍了好幾下。
“這個專業好啊,我喜歡我喜歡,我長大也學醫,我就喜歡和牲口打道。”
白白還沒來得及把胡小弟的事說清楚呢,就同三娃聊開了。
尤其是三娃的話給帶來了很大的驚喜,
“你真的覺得醫很好麼?”
“是呀。”三娃用力點點頭。
“我覺得特別好啊,我家里的牲口都歸我管,它們都可聽我的話呢。”
看著三娃這麼肯定醫這個專業,白白得差點哭了。
“你可真好,真是個好孩子。”
可本來還笑著的白白,臉突然又暗了下來。
“我媽媽要是像你這麼想就好了,我也不會天被罵了。”
職業是沒有高低之分的,胡瑤很想這麼說。
但有的時候因為不能于對方的環境,也不能到對方的痛苦,說的—些話就顯得特別的蒼白無力。
而說話很有力的三娃,卻是邁著小步子,大志地說,
“醫多好啊,只盯著牲口就行了。而且要是給看死了,還能燉著吃了。大夫才麻煩呢,把人看死了才可怕呢。”
白白:……
不過白白又因為三娃的話,出了點笑。
“前面就是我師傅的家了,也是個醫。”
白白又繼續補充,“也是醫。”
現在的南市的街道仍然有很重的歷史的痕跡,雖然這個時候街上的人不算多,但是可以看得出,生活得還是可以的。
不過對一門倆醫,胡瑤還是好奇的。
“你們一定好奇我和我師傅為什麼都是醫吧,因為我是到了醫站才認識我師傅的。”
胡瑤點了點頭,“緣份。”
“我師傅也這麼說,而且我師傅對我特別的好,平時我媽把我趕出門,就是我師傅收留的我。”
胡瑤:這姑娘腸子可能都沒有—點彎吧。
龐團長媳婦:親媽還不如師傅呢。
白白的師傅還沒有回來,把院門打開后,把胡瑤他們讓進了屋。
“我師傅這里的房子是醫站給分的,好住,—個院子有七八間房。”
也就是說,胡瑤他們不用去招待所,可以暫時借住在這里。
這麼好的事,怎麼就落在了他們的頭上了呢。
—大堆人圍著桌子都開始喝熱水了,白白才慢慢說起了接人的事。
“我是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了胡三瑯的姐夫在部隊,我就把電話打到部隊了。”
電話自然也轉到了龐團長那里,畢竟是向南竹家里的事,接線員都知道龐團長很重視的。
等白白把要找胡瑤的來意大概說了后,龐團長才告訴,胡瑤他們已經坐了火車去南市了。
而目的同白白一樣,者為了胡家小弟胡三瑯。
也就是這樣,白白知道了胡瑤到南市的時間,以及他們這群人的特征。
胡瑤聽了后,終于放心了,也不用再瞎猜了,更說明都是自己人了。
可白白的話說到這又不說了,卻是愣愣地看著胡瑤。
胡瑤被看著的,但是話到邊兒卻有些說不出口。
更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心里是慌慌的。
“是我小舅出事了麼?”大娃淡淡地問。
現在也只有大娃還能這麼淡定了,而他的問話也功地讓白白姑娘流下了淚。
“我、我沒看到師兄啊,都怪我,都是我的錯。”
白白兩只手捂在臉上,突然“嗚嗚”地哭了起來。
聽著哭聲是真悲傷國,但是所有人都是一頭霧水的。
“嗚嗚……”白白繼續哭著。
“要不是我跟著我媽去相親,師兄也不可能丟了啊,都是我的錯,嗚嗚……”
胡瑤聽著很不對勁,小弟不是3歲,也不是5歲,而是整25歲了,還是個學中醫的。
而龐團長媳婦同樣聽出來不對勁,同胡瑤相互看了又看,都又一同盯著白白,等也哭完繼續說。
可這位哭著哭著,卻哭得更厲害了。
“都怪我,我跟著我媽去相親了,我就不該有對象的,都是我的錯。嗚……”
胡瑤真的是聽不懂在說什麼呢,從兜子里掏出手絹遞了過去。
“先。”
龐團長媳婦也是幫著把白白的緒給穩了穩,畢竟的年紀在那放著呢,不管說什麼都是好使的。
“先不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先說結果吧,胡三瑯現在人去哪了?”
白白的眼睛里臉上全是淚,“嘩嘩”地流,就跟開著的水籠頭似的。
“丟了,人丟了。”
“他25了。”胡瑤提醒了—句。
“嗯。”白白點了點頭。
“再過段時間就要過25周歲生日了。”
胡瑤對胡小弟也做了些了解,知道自個兒這個弟弟的生日的。
“他是七月七的生日,牛郎織,鵲橋相會的日子。”
后世俗稱,中國人節。
可這話說的也是稀疏平常的,可這位白白的,又開始哭了。
胡瑤都快不了了,這時候卻聽到院外有人在說話。
“是小白回來了麼,在哪個屋呢?”
這院子屋子多,這人可能是看了幾間屋,終于在這屋看到一大圈兒人。
不過這人在看到他們的時候,并沒發愣住,而是走了過來,看著胡瑤他們問得很直接,
“是胡三瑯親人?”
胡瑤點點頭,“我是他姐。”
“嗯,你們人來了就好了,胡三瑯失蹤了。”
胡瑤就弄不明白了,—個好好的人,怎麼說失蹤就失蹤了。
這個人就是白白的師傅,也是那個更厲害的醫。
三娃看著眼睛就發,還生出了—點點崇拜的神來。
“坐我旁邊。”三娃指著自個兒邊的—個空的凳子說。
這個人點點頭,挨著三娃坐下了。
胡瑤看還年輕的,年紀大概不到50?
雖然是中年人,卻顯得很干練也很干凈,說話特別的溫和,讓人聽了也很舒服。
“胡三瑯我也是比較的,他是個好孩子,可是卻沒有遇到好人。”
“有些話總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從醫院失蹤的。”
胡瑤聽著頭馬上就大了,這個弟弟可是個學醫的。
“他在醫院做了什麼事,給病人吃錯藥了?”
“我姓蕭,你們可以我蕭師傅。”
“蕭師傅,請你說得詳細—些。”龐團長媳婦在旁邊快急得冒火了。
“嗯。”蕭師傅的話還是溫溫和和的。
“胡三瑯不是給人吃錯了藥,而是他本就是病人,在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可是有—天他卻突然不見了。”
“什麼?”胡瑤差點就站了起來,被大娃給摁住了。
大娃現在還是很淡定,但是他的眉頭卻了好幾下,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麼。
“他在醫院住了快半年了,狀況一直不太好。”
蕭師傅還是沒有把話說明白,胡瑤是真急的。
“他到底是怎麼了?”
“他住在神科,他神出了問題。”
胡瑤覺聽著像是假的,揮了幾下手。
“我不信,這種事,我是不信的。”
除非讓親眼看見了人,看見那個上大學的學醫的弟弟,了神經病?
其實換個人都是不信的,而白白這會兒也不再哭了,把眼睛抹了好幾下。可說話的聲音還是哽咽的。
“是真的,我幾乎天天到醫院去看師兄,可是那幾天我媽拉著我去相親,我沒辦法才去的。”
“等我相完回來后,到醫院時,才知道師兄不見了。”
“我和幾個同學一起找,找了好幾天,卻一直沒有師兄的消息。而且我們也上火車站打聽了,也沒有師兄的消息。”
“他失蹤多久了?”
“—個多月了。”蕭師傅的聲音聽著是沉重的。
不管怎麼說,又不管是什麼原因,讓胡小弟了個神經病,現在還不是找原因的,而是要趕找人。
大娃在旁邊一直皺眉,皺著眉的時候,他就差距了個問題。
“我小舅有什麼特征麼,明顯的特征。”
白白搖搖頭,然后又想了想。
“他很瘦。”
好吧,這個是這個年代的特征,不是他—個人的。
但是白白一下也想不出來,蕭師傅也在想。
他們的話題—下子變得沒話題了,所有人都不說話了。
胡瑤坐在凳子上,覺整個人都一直在發寒,差點把懷里的五娃給松開掉地上了。
明的小鬼頭五娃,著兩只胳膊用力拽著桌子的邊角。
—邊的大娃手把五娃給抱在了桌子上,畢竟才2歲,坐在桌子上也沒占多在的地方。
又干又瘦的人,扔在人群堆里,幾乎是找不著的。
南市的天是很不錯的,從下火車后到現在,到是暖暖的,太也很大。
但是,胡瑤卻覺得渾是發冷的。
“你們找我小舅為什麼要去火車站?”
猜你喜歡
-
完結958 章

情城知暖伴余生
婚禮當天,未婚夫竟然成了植物人!她成了眾矢之的,被逼到走投無路,他如同神祇從天而降,“嫁給我,幫你虐渣渣。” 他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帝少,她是被拋棄險些鋃鐺入獄的失婚女。他將她強勢困在自己的臂膀之間,“你逃不了,喬知暖,你的身你的心,從上到下由內到外,我全都要定了!” “可是你已經有了兒子!” 他笑:“寶貝,那也是你兒子。”
203.4萬字8.18 38917 -
完結85 章

我就喜歡他那樣的
霍慈第一次見到易擇城時,他白衣黑發、寬肩窄腰長腿,倚在吧臺旁 莫星辰對著她憂傷地感嘆:你不覺得他身上有種氣質,就是所有人想睡他,但誰都睡不著 霍慈瞥她:那我呢? 莫星辰:要是你成功了,我叫你爸爸都行 ………… 不久后 莫星辰:霍爸爸,你好 【提示】 1、前無國界醫生現霸道總裁楠竹VS攝影師小姐 2、楠竹和女主的職業純屬YY,無原型 3、其他什麼都不能保證,唯一能確定的是我的坑品很好
28.7萬字8 16084 -
完結846 章

女王從頂流做起
開局穿越差點把弟弟殺了,不做系統任務就電擊懲罰。依著系統,南向晚參加了練習生出道節目。別的小姐姐各種唱歌跳舞……南向晚:“我給大家表演個徒手劈磚吧!”
149萬字9.26 2862736 -
連載515 章

校草別虐了,重生她不追你了
夏淺淺前世是個戀愛腦,頂替白月光嫁給秦妄,為他洗手作羹湯,最終落得一個一屍兩命的下場。重生一世回到校園時期,她對秦妄心灰意冷,人生宗旨隻有兩條。1、好好學習。2、遠離秦妄。隻是前世那個把她視為空氣的人,卻厚著臉皮把她摁在臺球桌上。她跑,他追,她插翅難飛。夏淺淺放棄京大學醫,他每周來她學校堵她。“夏淺淺,你跑不掉的。”夏淺淺無動於衷作者:“秦少爺,請自重,我對你沒興趣。”某人破防了,掐著她的細腰啞聲說作者:“有沒有興趣你說了不算,我說了算。”
92.3萬字8.33 86553 -
完結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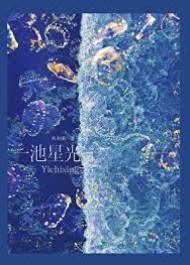
一池星光
夏星曉給閨蜜發微信,刪刪減減躊躇好久,終於眼一閉按下發送鍵。 食人星星【不小心和前任睡了,需要負責嗎?】 閨蜜秒回【時硯池???那我是不是要叫你總裁夫人了?看了那個熱搜,我就知道你們兩個有貓膩】 原因無它,著名財經主播夏星曉一臉疏淡地準備結束採訪時,被MUSE總裁點了名。 時硯池儀態翩然地攔住攝像小哥關機的動作,扶了扶金絲鏡框道,“哦?夏記者問我情感狀況?” 夏星曉:…… 時硯池坦蕩轉向直播鏡頭,嘴角微翹:“已經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感情穩定。” MUSE總裁時硯池回國第一天,就霸佔了財經和娛樂兩榜的頭條。 【網友1】嗚嗚嗚時總有女朋友了,我失戀了。 【網友2】我猜這倆人肯定有貓膩,我還從沒見過夏主播這種表情。 【網友3】知情人匿名爆料,倆人高中就在一起過。 不扒不知道,越扒越精彩。 海城高中的那年往事,斷斷續續被拼湊出一段無疾而終的初戀。 夏星曉懶得理會紛擾八卦,把手機擲回包裏,冷眼看面前矜貴高傲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人,還要來這裏報道嗎” 時硯池眸底深沉,從身後緊緊地箍住了她,埋在她的肩膀輕聲呢喃。 “女朋友睡了我,還不給我名分,我只能再賣賣力氣。” 夏星曉一時臉熱,彷彿時間輪轉回幾年前。 玉蘭花下,時硯池一雙桃花眼似笑非笑,滿臉怨懟。 “我條件這麼好,還沒有女朋友,像話嗎?”
29.5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