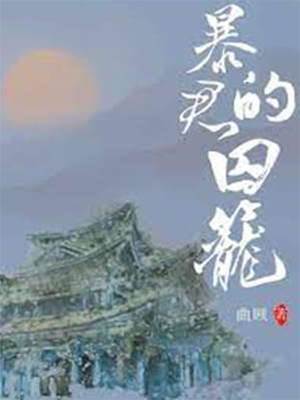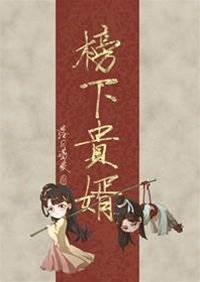《逃婚王妃:夫君別追我》 第484章 :墨玉流光的番外5
一陣吃疼,卻不能勝過我的心痛,視線瞥到玉笛上的穗帶,閃過一抹痛恨,于是我從腰間取下染的玉笛,看了一眼,五指收攏握住,越握越,咔嚓一聲,玉笛斷兩段墜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激起幾聲清脆的聲音。
我本已經有了裂痕的心,此刻隨著玉笛斷裂再度被撕碎,我用左手捂著口,陣陣刺痛讓我能夠麻痹,因為只有痛到麻痹才不會令我覺到活著這般苦。
蒼白的臉,鮮紅的手。
漆黑的殘影,破碎的笛!
真相如同死亡的刀刃,是怨真兒的自以為,還是怨太深?是恨機的不純,還是怪一死了之?錯與生死的距離,已然漸漸遠了。我心里很很,如果當初我知道這其中的由,我會這般深五年嗎?如果當初解釋開這一切都是個誤會,是會結束,還是會幸福?然而一切都不會存在如果,我怨,本沒有對象,即便心里很痛,可依然還是會心疼真兒,會自責,會惱火,錯位的也是,如何可以說戒掉就戒掉,說沒有發生就不會存在。
“哈哈哈哈哈哈哈!”
樹林里響著一聲高過一聲的嚎嚎大笑,是哭是笑就是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有口的痛提醒我很難,很痛苦。
之后我再醒過來的時候,我命令將真兒的尸從冰閣運到清風嶺,葬仇人找的墓,當我再次看見真兒的尸的時候,我去下了我一直佩戴在上的黑玉佩,過去將手中的玉放到冰棺里真兒的左手上,因為棺木被打開,一寒氣中夾雜著一腐臭。兩塊玉石詭異的閃了一下,然后便再也看不見任何反應。我不想下輩子再遇上真兒,我雖然還但是我的心已經不想再去。
Advertisement
我看到那悉的容葬黃土之后,我一個人下了清風嶺,我看到的眼神,我知道明白的,他懂我是要割舍掉對孟真兒的一片癡,放棄了來生相守的期。
我走進了玫瑰城門口,看到城中東北角一個書生攤開畫軸,拿起桌子上的酒壺喝了幾口,筆墨游走。古巷的憂郁,一子懷抱琵琶輕輕彈唱,奏一回斷腸的古曲,抬起畫面如此的麗。
我走到書生的攤子面前,“給我畫一副像吧!”
說完放下一定銀子。
書生激的看了一眼我,沒有多余的言語,揮毫潑墨很快畫好遞給我。只見畫面上,墨般長發垂及膝,眉可聚攏風云,目若朗月。形略顯清瘦,上流這一種坦然的氣息,頭上用一銀帶系著,松松的甩在腦后,上是一件紫衫,站在那里,背景選用的潑墨,取得是夜背景,畫像上的他面淡然,宛如云一般似幻似真,角淡淡的漣漪看不出悲喜。真的就跟當初形容的那般,只是如今我的心。經殘了。
“公子還沒有找你錢呢?”
“不用找了,你的畫值得。”
街上賣的小曲,仿佛隔空變換到那里,一切模糊又清晰,然,我卻跟以往不同了,我不悲不喜,穿過人群,走過浮華喧鬧的街道,我回到小三酒樓的廂房。攤開手中的畫像,碾磨執筆在右下角寫道:原來悟徹方寸,自在本心,窮識源流,方得大覺。
我去了翠云寺,在翠云寺的北面,一座隔開來的小院,桂花開滿枝頭,卻沒有折花人。
旁邊種了一棵菩提樹。想必院子的小,更顯得菩提樹碩大無比。雖然馬上就要深秋了,但它還是那麼拔蒼翠。墻上的壁畫因風雪的侵襲,也彩斑駁模糊不清了。屋傳來一聲一聲敲打木魚的聲音,伴隨著長夜清冷。月過窗戶照在一和尚袍的我上,我面前桌子上香煙繚繞,檀香或許是寂寞了,兀自四散開。
Advertisement
我停下手中的木魚,轉了一個,拿過桌角放的經書翻閱,八個篆字“波若波羅多心經”印眼底,翻開第一頁放在膝蓋上。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不異空,空不異,即是空,空即是,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
我三個月前來到這里,想要出家,卻被主持拒絕,說我塵未清,不能接我向佛之心,更別提要戒沓碟。我最后也只被領到這個院子,說是:若是三年,依然不改初衷,就接我為佛門之人。
“呵呵,三年,就是十年,一輩子,不在,他也不會出這院子。”
對于主持的話,我心底不由苦笑,想必是支持也害怕我的勢力吧,許是那天富貴山莊的爹娘找到這里,我就做不主持了吧!我想的很清楚,這輩子紅塵終究紛雜,我又何苦不忘!
回了回神,雙眸看了看窗外閃爍星辰,一眼便收斂眸子,左手再度翻過一頁,“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盤。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朦朧夜的籠罩下,屋里揣佛理的人跟古老的屋子,就像是一道虛渺的影像。我雙手合十,盤膝而坐,這還是那個聞名天下,就連天子也不敢與之側眉的我嗎?不不是了。這座古老的寺廟后的小院,顯得分外沉寂。
當我離開翠云寺的時候是我二十九歲,告訴我死了,被楊思如害死了。我才知道我沒有放下,原來我一直都想去見,都想要擁有,可是我再見到的時候,卻只是一冰冷的尸。
Advertisement
我憤恨的用鞭子狠狠的打著楊思如那賤人的尸首,我直接對乾坤國的皇帝施,我要讓楊家犬不留。
他出殯的那一天,我親自抬起的靈柩,將抬進地下,就像真兒一般長眠,永遠也不會再睜開那雙清澈的眼睛,呼喚我的名字。
死去半年之后,我回海外的家中,看了一下我的父親,還有那個當初抱回來的那個孩子,我的義子墨玉龍,要求我跟它回去,我離開的時候帶走了我的表妹,我將我的產業全權給了,而且做主讓迎娶了表妹南宮云溪。
如果這輩子我做的最對的一件事,只怕就是讓表妹忘記我,忘記我這個注定被上天捉弄的男人。看到表妹甜甜的笑,看著表妹幸福的親吻著,我從心底替開心。
在之后,影帶著元寶還有他們兩歲的孩子想要勸我放棄出家,我也只是讓他們好好生活,珍惜現在所擁有的,而我重新回到了翠云寺的小院子,這一次我了戒,剔去了一頭墨發。
我三十一歲的時候,我已經出家一年,跟影寫信告訴我,沒有死,的魂魄還活著,就是瑤池國太子妃北堂雪鴛,我笑了,心頭的石頭剝落了,而我是真的心無塵埃了,我拿著木魚一下一下的敲著。
我三十三歲的時候,北堂雪鴛來了,我知道這個里的靈魂是的,我沒有懷疑,我也沒有打開門,在外面站了兩個時辰,我在里面站了兩個時辰,我們隔著門也只說了不到五句話。
我怕我一開門,我沉靜的心會再起波瀾,而君子淵照顧的很好,我很放心,就讓我的心伴著青燈吾佛。
走了,而我也伴著梵音我走過了剩下二十年,五十三歲,我合上了經卷,死在小院的菩提樹下,我的一生,一生都在下雨。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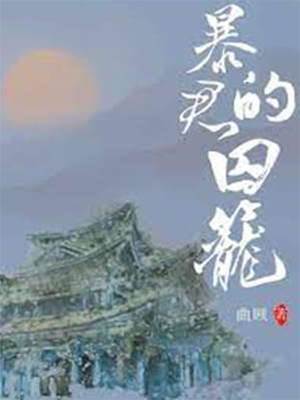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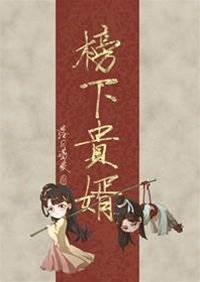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