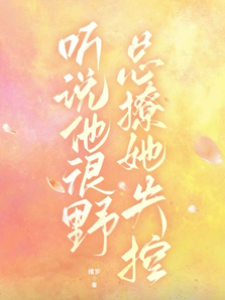《女主光環被奪之后我重生了》 第047章 姐弟
掛在樹上了的秋梨,潤肺生津,梨雪白,水飽滿。
顧謹謠削了三個,切小塊放在碗子端出去給孩子們和紀蘭。
相了兩天,兩個孩子也沒那麼怕紀蘭了,雖然也不會靠近,但不排斥,隔著一點距離還會跟說話。
只是紀蘭很回應,要麼發呆,要麼傻笑。
“姐,吃梨。”
顧謹謠將裝梨的碗遞到紀蘭面前,自己還拿了一塊放進里,在教。
紀蘭也不知道在想什麼,轉頭看著顧謹謠發呆。
顧謹謠見不吃,很快就將碗拿開了,進屋里了一雙用舊布料做的夾棉大手套。
紀蘭的手長滿了凍瘡,又紅又腫,這兩天顧謹謠給抹了雪花膏養著,還做了這雙手套。
“這個,套上。”
顧謹謠像教小孩子一樣教,紀蘭呆滯的眼神看著這雙手套,終究還是流出了一些別樣的。
那一閃而逝,不過顧謹謠還是看見了。
剛剛紀蘭的神……
“快戴上吧。”
顧謹謠將手套遞過去,打算幫戴上。
這時,一直沒的紀蘭將手套拿過去了,放在眼前看了看,一揚手,扔了。
顧謹謠:“?”
來到這個家里第一次發脾氣,再配合自己剛剛看到的神,顧謹謠覺得這個紀蘭,怕不是真的有點“問題”。
顧謹謠也沒惱,默默撿起那雙手套,放到房間的床頭去了。
快天黑時,趙小鋼回來了,拉回一百斤大黃米、五十斤花生,還有二十斤白芝麻。
這些東西都是趙小鋼用他的洋車子拉回來的,顧謹謠見他累得滿頭汗,分了幾個梨給他解。
東西卸下,顧謹謠將花生拿出來,扛到隔壁的小春家,讓幫忙去一下殼,五十斤給五錢。
Advertisement
他們家人多,晚一點就能拿到花生米。
五錢剝五十斤花生,這當然使得。
農村人最不值錢的就是力氣,晚上大家都沒事可做,燈下一坐,一邊嘮嗑,一邊做事,家里十幾個人,半個小時就剝完了,還能賺半斤豬錢,何樂而不為。
后村,顧家三房此時也在剝花生。
顧柳鶯也是個會算本的人,只是有三房一家子人可以用,干嘛還要出那五錢。
每當個時候田春花就忍不住抱怨,依附著二房做生意,平時不要免費當服務員,地里的活也要幫忙干,有點什麼事還得讓他們加班加點弄。
三房只有四個人,五十斤花生得弄兩三個小時,手都疼了。
田春花:“投這麼大,花生糖跟芝麻糖也不知道做出來能不能賣。”
顧謹謠的米花糖賣得好,大家有目共睹,可花生糖跟芝麻糖還沒試驗過啊!
這次顧柳鶯要做糖,的確拉三房合伙了,但是合伙有合伙的規矩,顧柳鶯投技,本就跟三房四六分。
做糖可跟做豆芽不同,豆芽就是一點綠豆黃豆的事,這次做這個是要用細糧,是要花錢的。
而且這個錢一點都不便宜。
田春花擔心的,前怕虎后怕狼,本不是做生意的人。
顧勇國就勸,先試一次,要是賣得不好,他們就不干了。
而且,聽二丫頭說,大丫頭的糖源斷了……
次日。
前村后村都飄滿了菜籽油的香氣。
顧柳鶯在做糖,顧謹謠也在做。
只不過一個是直接上手,一個還在試驗。
加了神仙水的花生糖跟芝麻糖,出爐之后那味道讓人罷不能。
可最近吃多了加神仙水的東西,顧謹謠還是能品出點點不同,這就跟用料,跟人的手藝有關。
Advertisement
試了三次,盡量保證商品完。
雖然有神仙水在,但只要有一丁點偏差,都要試著去改變,去學習,而不是拿著好東西就消極怠慢,只知道坐其。
東西試驗功,原料也準備好了,顧謹謠并沒有立即上手做,還是跟之前一樣,準備明天早起趕個新鮮。
夜里。
案臺上的面條搟好,灶膛里就暫時停火了。
堂屋跟灶房里都點著燈,一家人坐在燈下,靜靜地等著,等紀邵北歸。
今天,周六。
從縣里坐最后那班車回鎮,再步行回村,怎麼樣都天黑了,而且現在冷,黑得也比以往要早。
其實他們也可以先吃,可紀邵北一周才回來這麼一次,一家人總想著有個圓滿。
男人的腳程快,這次他們并沒有等多久,院門外就傳來響,紀邵北回來了。
他還是穿著那軍大,背上挎著軍綠的舊布包,大步進門時剛毅、沉穩、像一陣風。
顧謹謠從灶房迎了出來,“回來了。”
紀邵北看著,腳步停了一下,“嗯。”
“我燒了熱水,放下東西過來洗下臉和手吧。”顧謹謠說道。
“好。”
紀邵北的聲音沉沉的,細聽之下能覺到一笑意。
他的心不錯,可當踏進門檻那一刻,原本那點笑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瞬訝然。
“姐?”
坐在桌前的人穿著藍棉襖,頭發齊肩,除去神有些不對,看起來跟普通人沒多大區,甚至比天需要干活的婦人還要干凈整潔。
如若不是記憶里的那個影子,紀邵北本沒辦法將眼前的人跟紀蘭聯系在一起。
多年過去了?
五年了!
是的,紀蘭瘋掉已經五年了。
Advertisement
五年里紀邵北休假回村都會過去看,盧家聽到他回村的風聲會專程將人收拾一下,等到他過去的時候勉強看得過眼。
其實紀邵北都知道,姐姐在盧家過的什麼日子,臟污不堪,活得像個乞丐。
曾經,他也準備提前退伍,帶姐姐回紀家好好照顧,可那個時候的紀蘭就會發病,趕他,罵他,躲在盧家的角落里本不愿意跟他離開。
對于這個堂姐,紀邵北心是無奈的。
紀蘭十五歲才去盧家,小時候他是帶著長大的,姐弟義深厚,長大后,活著艱難,他卻無能為力。
回首往事,關于紀蘭,他都非常自責。
當初,要是他晚一年當兵,或是不去當兵,或許就不會有這些事了。
可這個世界里,沒有要是、如果、或許。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疾風吻玫瑰
江南葉家,書香門第,家風嚴謹。 獨女葉柔,溫婉恬靜,克制自律,從沒做過出格的事。19歲那年,葉柔遇上一個與她全然不同的少年——江堯。 他乖張、叛逆、恣意、頑劣,明目張膽地耍壞......眾人皆雲他不可救藥。只有葉柔覺得那是一道強光,不可逼視。她做了個大胆的決定,追求江堯。江堯為拒絕這個乖乖女,曾百般刁難,其中一條是:“想做我女朋友? 一輛頂配的WRC賽車,我明天就要。 ”當晚,葉柔偷偷典當自己的嫁妝,給他換回一輛WRC跑車。
26.2萬字8 31483 -
完結335 章
分手時孕吐,禁欲總裁徹底失控
安漫乖順的跟在江隨身邊三年,任他予取予求,他想當然的認為她是他手里的金絲雀,飛不出掌心。轉眼,他跟謝家千金訂婚的消息轟動全城。她心碎提出分開,他卻不以為然,直言我沒玩膩之前,你給我乖一點!他跟未婚妻恩愛曬的人人稱羨,背地里卻又對她糾纏不止,不給她名正言順的身份,卻又不肯放過她。直到一日,她隱瞞懷孕消息,不告而別。任他滿世界瘋找,再無音訊。再相遇,她已經是私募基金高級合作伙伴,千億家族的唯一繼承人,唯獨不再是他江隨的女人。他再也沒有往日的高傲跟矜持,跪在她跟前哀求“這一次,求你別再丟下我……”
64.1萬字8 12300 -
完結495 章

閃婚后,顧夫人她卷錢跑路了
初次見到姜思顏,顧寒川誤以為她是自己的相親對象。于是他直奔主題: “第一,結婚后我們分房睡。” “第二,每個月給你三萬塊的生活費。” “第三,在外面不準打著我的旗號胡作非為。” 姜思顏眉頭輕挑,“第一,性功能障礙就不要耽誤別人的性福。” “第二,每個月三萬塊著實是多了點,你可以留下二百五自己花。” “第三,我想問問,你誰啊?” 坐過來就逼逼叨叨的來了個一二三,神馬玩意? 看著罵罵咧咧離開的女人,顧寒川笑了…… 后來,兩家聯姻的消息一出,頓時轟動整個京都。 畢竟這倆人都不是省油的燈。 一個是臭名遠揚的千金大小姐。 一個是手腕狠辣的豪門大佬。 這二人結合,還能給他人留活路麼? 夜晚,路邊停下一輛紅色的超跑,一輛黑色的大G。 從黑色大G中走下來的姜思顏,稍有嫌棄的看了眼紅色超跑內的男人。 “確定非我不可?” 顧寒川語氣寵溺的道,“錢都砸出去了,難道你想讓我人財兩空?” 姜思顏微微一笑,“那你可別后悔!”
83.8萬字8 5892 -
完結233 章

和我媽敵蜜兒子的地下情
【娛樂圈+京圈豪門+港圈豪門】天才鋼琴作曲家x物理科研人才 【簡介1】 談愿聽聞,隔壁的那棟別墅搬來一戶新鄰居 這家人來自港城,說著一口港普,女主人穿得花枝招展,脖子和手指上碩大的珠寶快閃瞎裴女士的眼 暴發戶?這是談愿的第一印象 后來,他房間的窗戶斜對的隔壁亮起了燈 學習時、打游戲時、躺在床上時,總能聽見悠長動聽的鋼琴聲,是他沒聽過的曲調 他從窗戶窺探對面紗簾下女孩彈琴的背影 乖巧,這是談愿的第二印象 再后來,他撞見女孩和一個同齡男生的爭執 兩人說著港語,他不大聽得懂,女孩的聲音里的無情拒絕卻讓他覺得動聽 叛逆,這是談愿的第三印象 最后,這姑娘在談愿心里的印象越來越多 似是要將他的心填滿 談愿不想承認、又不敢承認 在他終心直面內心時 這姑娘,就這麼消失了 獨留他惦記這麼多年 【簡介2】 整個京圈都知道裴婉女士和何昭昭女士不合 京圈貴婦與港圈名媛互相瞧不上 連帶著談愿和阮昱茗都不準有接觸 裴女士嫌棄何女士的“壕”放 何女士看不慣裴女士的“端莊” 裴女士不喜歡阮昱茗的花邊新聞 何女士瞧不上談愿是理工直男 直到阮昱茗和談愿的地下情曝光后 兩人驚訝:“您倆什麼時候變閨蜜了”
44萬字8 111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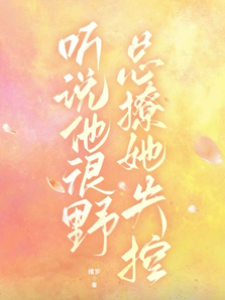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