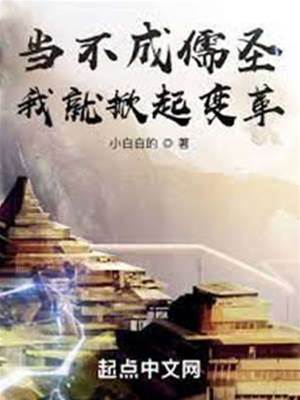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我非癡愚實乃純良》 第1081章 走一趟
“我也想學珍大哥,在家里著書立傳。”
王珰睜開眼,趴在床上不起來,里含含糊糊道。
碧縹早已起來了,正坐在床頭刺繡,聞言也不驚訝,竟是一本正經地問道:“相公想著什麼樣的書?”
“這倒是沒想好。”王珰打著哈欠稍想了想,道:“寫一本《蟋蟀經》如何?你說笑哥兒能答應嗎?”
他又在床上翻了一圈,抱著被子舍不得松手,道:“這事也是真怪了,珍大哥想干嘛就干嘛,笑哥兒就從不管他。”
“珍大哥畢竟是晉王兄長,豈有弟弟管哥哥的?”
“哼,我也是兄長啊。”
“相公若是再不起來,上衙又要遲了。”
“反正是又要遲了,又何妨多遲一天?”
“相公不怕被罷,可怕被發配到哪里辦苦差不是麼?”
王珰翻而起,出牙,驚奇道:“好碧兒,你怎麼知道我怕這個。”
“你昨夜夢話說的。”
“是嗎?那這是大兇之兆啊。”
王珰嘟囔著爬起來,懶洋洋地站在那任碧縹帶婢子給他換了服。
又有婢子拿了兩封信件進來,道:“爺,你的信。”
王珰也沒空看,往懷里一收。
吃早食之時,又聽府里傳來吵鬧聲,王珰頭也不抬,問道:“今日又是吵什麼啊?”
不必說他也知道,是孟古青和王思思吵起來了。
果不其然,碧縹道:“孟古青說要到南苑看老虎,思思不讓去。孟古青又說以后是思思的三嫂,是長輩,把思思惹惱了……”
“爹和大伯也不管管,一天到晚的吵吵吵,煩死了。”王珰嘆了一口氣,又道:“大哥也不怕那蒙古丫頭把思思帶野了。”
“相公,你要遲了。”
王珰漸漸了有了神,終于到了遲到的慌張,作快了不,可惜趕到衙門時果然還是遲了。
Advertisement
今日好在他來得不算太遲,上午時他的部堂大人蘇明軒又召集所部員議事。
王珰支著腦袋無打彩地聽著蘇明軒在上面長篇大論,莫名又覺得有些困。
他想起來懷里還有兩封信沒看,于是又趁著這會開始看自己的私信。
一封是周先生寫的,王珰看過之后咧著笑了笑,想著有空了再回一封。
接著拆開另一封看了一會,他卻是愣了一下,暗道不好,心里認定王笑肯定又要來找自己的麻煩。
果不其然,才到下午,便有晉王親衛找到王珰,道:“晉王召王大人過去。”
“唉……”
~~
王笑之前多在建極殿務公,如今干脆在東暖閣邊又收拾了一間公房出來。
王珰向來是對這地方避之唯恐不及,今日卻沒逃掉。
他心里慌得很,臉上卻帶著笑容道:“笑哥兒,這地方不錯啊。”
王笑卻懶得與他廢話,徑直問道:“收到周先生的信了?他怎麼樣?”
“他過得很好啊。”王珰道:“他回了山東,在兗州住下來,娶了個妻子,生了個孩子,鄰里都很敬重他,平時就制琴,空了就游山玩水……”
“沒人去打擾他吧?”
“沒有。”
“銀錢夠用嗎?”
“夠,我大哥前段時間剛給他送過一大筆銀子。”
王笑點了點頭,算是結束了這個問題。
王珰才松一口氣,又聽他問道:“我早就讓孫知新、胡敬事他們進京來了,人呢?”
“這我就不知……不知道他們腦子里哪筋錯了。”
“是嗎?”
“好吧。”王珰老老實實道:“胡敬事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去年年末,他們遇到一名西軍將領名李如靖,其人率軍過境,秋毫無犯,且宗太沖、顧寧亭先生亦在他軍中。”
Advertisement
王笑冷然一笑,道:“我看,不僅是宗太沖、顧寧亭吧,鄭元化之孫鄭昭業早前逃出南京城便是向西投奔了西軍,是嗎?”
“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王珰道:“信里只說去年年初,江南政變之后宗太沖就到了李如靖軍中,與這次又遇到孫知新、胡敬事等人,他們湊在一起,說是‘相談甚歡,乃平生知己,暢聊數日不覺疲憊’,最后決定到李如靖的封地上做一點事,就……就不來京城了。”
“這人的封地在哪?”
“涼山。”
“把信給我。”
“哦。”王珰應了一句,一邊把信遞過去,一邊又道:“笑哥兒,信上……有些說你不好的話……這個,但也沒有怎麼說,就是說你‘為人主,忘卻大志’,這個……你也別太生氣。”
“沒什麼好氣的。”王笑接了信,也不馬上拆開,手指在信封上敲了敲,道:“胡敬事上次接走周先生,好在他沒有挾制周先生,否則他現在已是個死人了。”
“哦,他不是那種人,他只是想給周先生……自由。”
王笑其實話還沒說完,卻被王珰打斷了,白了他一眼,又道:“我放過他與孫知新一次,他們卻覺得我在縱容他,越來越放肆。”
王珰道:“是,他們太放肆了,我們馬上要剿滅獻賊,他們居然從賊。這樣吧,我修書一封,讓他們勸降那李如靖,戴罪立功,晉王覺得如何?”
“不必了。”王笑道:“秦山河病了,我打算調唐節往西蜀平賊……”
王珰心說“你跟我說這個干嘛?”同時心里已升起一種不好的預。
果不其然,王笑的后一句話就來了。
“你隨軍去一趟,若遇到孫知新、胡敬事、宗太沖、顧寧亭、李如靖這些人,親自勸一勸他們,他們若不肯降,就捉起來,但不必害了他們命。”
Advertisement
王珰登時就苦了臉。
但這次他卻是沒說什麼。
幾年前中原一戰,他流落河北,確實是過孫、胡等人的恩惠,彼此又是朋友。
唐節那個子他也知道,他若不去,沒準唐節平定張獻忠時,打著打著火氣上來,一刀……哦,一槊就把那兩個書生還有鐵豹子張嫂他們打死了。
“那……去就去吧。”王珰委委屈屈道,“我還能怎麼辦?”
王笑點點頭,拉了拉旁邊的繩子,不一會兒,進來了一個年輕將。
“末將洪承志,見過晉王。”
王笑于是向王珰道:“這是我邊的親衛,他會一路保護你。”
王珰轉頭看去,只見這洪承志極是年輕,看起來不過十八九歲,眼睛極亮,但穿盔甲卻還著一書卷氣。
他不由暗道:“這小子行不行啊,別到時還要我保護他……”
~~
待王珰與洪承志離開公房,王笑目送了他們的背影,又拿起案上的一封折子看起來。
那是左經綸的辭呈,當然不是現在就要批準的,而是要以天子的名義挽留幾次,來來回回的,等真批下來時大概西邊也平定了。
一則有個緩沖時間接,二則這是三朝老臣該有的面,王笑再重效率,也會給左經綸這個面。
而這天下之大,廟堂之高,總有舊人走,也總有新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100 章

至尊妖孽兵王
一代妖孽戰醫葉洛,受殺手之王臨終托女隱居都市。本想安穩過日子的他,卻不經意間被美女包圍,嬌俏護士,火爆女警,富家千金,冷傲總裁,當紅女星…一個個闖進他的生活,攪亂了他的平靜。葉洛嘆息:裝逼泡妞我早已厭倦,只想做個平凡人,你們何必逼我呢?
200.5萬字8 55723 -
完結1689 章

攝政大明
因為偶然的原因,趙俊臣穿越到了一個陌生的朝代,成為了一個惡名滿天下的貪官。在這里,昏君當政,遍目皆是奸臣,清流無用,百姓受苦。 趙俊臣沒有揭竿而起的魄力,亦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更無意于辭官隱退,成為平民百姓,受那世間動蕩之苦。 所以,他只能融于滿朝貪官之中,借貪官之勢,用貪官之力,成為這世上最大的貪官,自上而下,還乾坤之朗朗。 ...
565.1萬字8 17263 -
完結1054 章

調教大宋
慶曆六年,歌舞升平的趙宋王朝。迎來了一個瘋子.... 親眼見識了大宋的雍容華貴與溫情。 起初唐奕隻想享受這個時代,什麼靖康之恥、蒙古鐵騎都與他無關。反正再怎麼鬧騰曆史都有它自己的軌跡。千年之後中華還是中華! 亡不了! 但當那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出現在他麵前的時候,他的心變了...他想為那個老人做點什麼順便為這個時代做點什麼.... 於是怎麼把大宋這隻羊,變成呲著資本獠牙的狼!成了唐奕唯一
88萬字8 16976 -
完結1660 章
我要做皇帝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朕奮三世之餘烈,用天下之大義,乃執三尺劍,以做天下王。朝鮮衛氏王頭已懸漢北闕。南越趙氏納土內附。中央帝國,天朝上國,即將成型。但這還不夠!朕的眼睛裏,現在只有匈奴!帥師伐國,北擒單於問罪於朕前!
463.1萬字8 18097 -
完結4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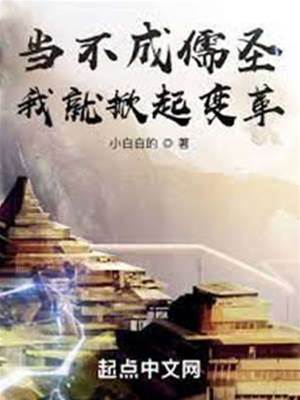
當不成儒圣我就掀起變革
作為一個演技高超的演員,林柯穿越到了大魏圣朝,成了禮部尚書之子。但他是娼籍賤庶!這個世界把人分為上三流,中流流,下九流……而娼籍屬于下九流,不能參加科舉。母親是何籍,子女就是何籍!什麼?三尊六道九流?三六九等?我等生來自由,誰敢高高在上!賤籍說書人是吧?我教你寫《贅婿兒》、《劍去》、《斗穿蒼穹》,看看那些個尊籍愛不愛看!賤籍娼是吧?我教你跳芭蕾舞、驚鴻舞、孔雀魚,看看那些個尊籍要不要買門票!賤籍行商是吧?你有沒有聽說過《論資本》、《論國富》、《管理學》、《營銷學》……還有賤籍盜,我和你說說劫富...
30.5萬字8.18 2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