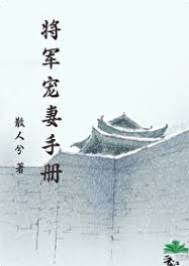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閨寧》 第207章 挾持
然而駿馬疾馳,塵土未曾落下,馬兒已不見蹤影。
濃濃夜幕下,馬蹄落地的「噠噠」聲響亦很快遠去。圖蘭拔腳要追,卻被冬至給攔了下來。冬至一臉凝重,擰著眉頭同沉聲道:「追不上的。」
那匹馬是燕淮的,正宗的西域馬,連自小吃的草料都是西域的草,生得高大健碩,跑起來腳下生風,乃是一等一的良駒。憑兩條人,那是本就不可能追得上的,便是眼下有普通的中原馬,也是難以企及。
圖蘭在漠北長大,焉能不知這些,但這會見謝姝寧不見了,心頭思緒了一團爛麻,哪還顧得上去想追的上追不上。
冬至一攔,便怒了,大力打開冬至的手臂,叱道:「小姐都被壞人給帶走了,你不追還攔我做什麼?」
原本說起西越語來就有些怪聲怪調,這會一著急說得快了,更是怪得厲害,聽得冬至忙不迭解釋:「你難道還能跑過馬去?再說了,方才那人你難道沒有認出來?」
他這般一提,圖蘭愣了愣,回憶著先前在胡家小院子里看到的樣子,心頭微驚。
——是國公世子燕淮。
在花園時,也在堆秀山上的景亭里,曾一點不落地瞧清楚過燕淮的模樣。
方才事態急,一時沒有想到而已。如今冬至一提醒,圖蘭更是慌了,磕磕絆絆地想要組織語言:「男的,他是男的,不可以同小姐一起……天黑了……」
冬至愁眉不展。
站在一旁的吉祥忽然冷冷嗤笑了聲。
圖蘭跟冬至一齊扭頭去看他,目如炬。
吉祥也不避開他們的視線,只將劍做拐拄在地上,歪著半個子面冷然地道:「你家小姐若是膽敢對世子不利,只怕謝家也該一道與世子陪葬!」
Advertisement
他說著恐嚇的話,心急如焚的圖蘭卻只覺得自己聽得一頭霧水,茫然地直了板凝視著吉祥上胳膊上的傷口,面無表地道:「是你家世子劫持了小姐,你怎麼這麼不要臉,還能說這樣的話?」
學的詞向來簡單實用,這會想也不想便將個「不要臉」三個字給丟了出去。
吉祥怒意難遏,拔劍就要殺了眼前的二人。
然而不等他們鬧開,已經盡數被火龍吞噬的農家小院後頭,忽然傳來了一陣馬匹驚的嘶鳴聲。
耽擱了這些時候,也不知雲詹師父逃走了沒,冬至心中大驚,飛快往那邊去。
圖蘭一跺腳,看了幾眼謝姝寧方才遠去的方向,牢牢記在心裡,亦跟了上去。
吉祥拖著傷的胳膊跟,站在距離燃燒中的火場幾步開外,幾乎能到火星撲濺在自己上的灼熱。
今兒個夜裡,悄悄潛如胡家的人,他殺了兩個。
胡家院子外,守在各角落的,還有三人,被冬至跟圖蘭乾淨利落地解決了。
被狼養大的圖蘭,在暗夜裡有著旁人無法比擬的天賦。
除卻這些人外,先前同燕淮麾下的天字五人相鬥,這伙子人里也不知究竟死了幾個。
吉祥暗自在心裡計算著,這一回來的人,至有十個。但他們沒有料到這裡還有旁人,也沒有料到圖蘭跟冬至的存在。事更正如燕淮先前所料,這幾人本沒有將他放在心上放在眼裡,悄悄潛胡家院的人,全都是為了防備吉祥。
結果一疏忽,這群人就開始步步踏錯。
刀劍影間,燕淮一出手便斬殺了一人。
吉祥頭一回知道,自家世子,竟對殺人一事,如此練,劍劍往要害刺去,目標明確,沒有一花樣。
京都的世家子弟,除了那些自詡書香世家,連劍都不一下的人外,旁的多多都會些拳腳刀劍功夫,這裡頭也有那麼幾個學的不錯的。但同燕淮一比較,本個個都只是花架子。
Advertisement
吉祥很吃驚,卻也莫名開始放心了許多。
他這才在解決了剩下的那一人後,擒住了偶然撞見的謝姝寧。
謝家八小姐,若活著離開這裡,保不齊口風不嚴就會將今夜的事泄出去。
他不能冒險,即便燕淮本沒有要取謝姝寧命的意思,但吉祥仍舊一意孤行了一回。然而,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看上去弱弱,風一吹就倒的人,竟還能從火場里逃生!
吉祥定定立在那,眉頭皺。
世子帶著人,去了何?
正想著,他忽然聽到一陣狼嚎聲,憶起之前似也聽到過,臉一白,戒備地四巡視。
向右側時,他瞧見圖蘭騎在一匹馬上朝著自己直衝過來,手上握著不知上哪兒奪來的劍,上頭鮮淋漓。在後,冬至架著馬車亦急急而來。
來者不善!
吉祥心裡冒出這麼幾個字,當即橫劍在前,愈發警戒起來。
圖蘭形高大,居高臨下地在馬背上看著他,似乎下一刻就會下馬兒抬腳踢死他一般。
但馬沒,圖蘭也沒說話。
說話的是冬至,他眼也不眨一下,直勾勾盯著吉祥道:「世子去了哪裡?」
吉祥冷聲道:「這話問錯了,該問你家小姐要去哪裡。」
方才謝姝寧竟還騙他,說名雲什麼鶴,簡直豈有此理!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人,指不定為了讓二公子襲爵,早就起了心思要害世子。詭異的念頭在腦海里一閃即過,但吉祥還是不自地握了劍柄。
「你們招惹來的壞人,你們要負責!」
圖蘭揚起劍,劍尖上一滴「啪嗒」落在了吉祥鼻上。
冬至鎮定些,但眼神似狼,狠狠看著他,繼續道:「人還沒有殺。」
方才他們趕往後頭,正巧遇上了個著黑的殺手,好在圖蘭反應靈敏又兇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上去「撕裂」了那人的嚨。
Advertisement
但他們誰也不知道,這附近究竟還有沒有藏在暗的黑手。
吉祥,也不知。
潑天的火下,他緩緩手去了鼻上的那滴:「我不知道世子去了何。」
若還有人未死,就說明,有可能已經有人追著世子去了。吉祥心焦起來,面上卻仍舊維持著泰然的模樣。
可巧這模樣惹怒了圖蘭,忽然俯,出比一般子大上許多的手掌,揪住吉祥後頸的裳就往馬背上拖。吉祥還未回過神,人就已經被丟到了圖蘭前,趴在了那。
簡直是恥辱!
他活了二十多年,何曾遇到過這樣的事,當下掙紮起來,卻被圖蘭一個大掌給拍得差點吐出來。
圖蘭死死制著重傷的吉祥,毫不留面。隨即調轉馬頭,口中肅然說道:「世子帶走了小姐,我們就帶走你。你什麼時候說出世子去了哪裡,我們才會放了你。」
吉祥眼冒金星,幾乎不過氣來,咬著牙說:「我當真不知世子去了何!」
圖蘭不信,丟了劍,揚鞭而行。
一馬一車行出小村,後忽然冒出來幾個黑的影。
吉祥正被顛得暈乎乎的,猛然瞧見,大驚失:「小心!」
圖蘭瞪圓了眼睛,頭也不回,拔下發上長簪往馬上一紮。黑馬長嘶一聲,跑了一陣風。
然而逃著命,圖蘭半道上還不忘記提醒他,記得說出世子去了哪裡。
吉祥被折騰得去了半條命,昏沉沉閉上了眼睛。
等到再次睜開眼,卻發現自己已經被捆住手腳塞進了馬車裡,旁坐著個閉目養神的年。
馬車外,冬至正在同雲詹先生說話。
雲歸鶴的車駕得不好,運氣也不好,他們才出了村,就被人給盯上了。馬車被毀,兩人倉皇而逃,直至了高高的草叢,那幾人忽然棄了他們調頭而去,這才幸免於難。
Advertisement
雲詹先生連聲說著萬幸,卻被冬至一句「小姐被國公世子帶走了」的話,給唬得老眼瞪大。
……
而同他們南轅北轍的燕淮跟謝姝寧,後自半刻鐘前,便已經如影隨形地被人盯上了。
謝姝寧渾僵,努力伏低了子,暗怕燕淮會不會擇個時機就將給拋下,獨自逃生。以所知的燕淮來說,這是極有可能的事。謝姝寧因此始終慘白著一張臉,又聞後馬蹄聲越來越近,心都快從嚨里跳了出來。
燕淮就坐在後,風一吹,他上的腥氣就不住往鼻子里鑽。
「坐穩了!」
忽然,後的人低了聲音在耳邊飛快說了一句。
旋即下的西域馬使出全力,邁開大步往前飛馳而去。
疾馳了一陣,道旁暗影重疊,視線越加昏暗。耳畔風聲大作,謝姝寧因只著了件髒兮兮的裡,冷得直哆嗦。
正慄著,燕淮突然一把將抱住,翻滾下了馬。也不知撞到了什麼,謝姝寧只聽得他悶哼了一聲,良久都沒有作。
馬越跑越遠,謝姝寧有心詢問,卻不敢在後有追敵的時候出聲說話。
好在只一瞬,燕淮便拉著站起來,開始往林中跑。
這個村子,只有前後兩條路可行,兩旁皆是山林,高高低低,又因在夏日,草木茂盛,極適合躲藏。
兩人踉踉蹌蹌地在高過一人的草叢間披荊斬棘,蹣跚而行。
山下不時有人策馬通過,皆追著那匹西域馬去了。
跑了不知多久,謝姝寧開始發抖,已經累到了極致,無力再走。腳步慢了下來,燕淮拖著又跑了一陣,驀地停了下來,回頭看著,緩緩鬆開了手。
謝姝寧苦笑,果然不能指他帶著自己這個無關的人逃命。
誰知下一刻,燕淮忽然將背了起來。
======
求票小劇場~
饅頭驚喜:「柿子大好人!」
柿子面無表:「作者君說了,木有網路又木有紅的日子廁所都被哭塌了,再湊不夠加更票,我就只能把你丟下跟一起去哭了。」
饅頭哀嚎:「只差3張了啊3張!」
猜你喜歡
-
完結475 章
廚女當家:山裡漢子,寵不休
一朝穿越成食不裹腹,家徒四壁的農家貧戶,還是一個沖喜小娘子。 陳辰仰天長嘆。 穿就穿吧,她一個現代女廚神,難道還怕餓死嗎? 投身在農門,鄉裡鄉親是非多,且看她如何手撕極品,發家致富,開創一個盛世錦繡人生。 唯一讓她操蛋的是,白天辛苦耕耘賺錢,晚上某隻妖孽美男還要嚷嚷著播種種包子。 去他的種包子,老孃不伺候。
87.3萬字7 49745 -
完結1071 章

權寵天下:本候要納夫!
忠遠侯府誕下雙生女,但侯府無子,為延續百年榮華,最後出生的穆千翊,成為侯府唯一的‘嫡子’。 一朝穿越,她本是殺手組織的金牌殺手,女扮男裝對她來說毫無壓力。 但她怎麼甘心乖乖當個侯爺? 野心這東西,她從未掩藏過。 然而,一不小心招惹了喜怒無常且潔癖嚴重的第一美男寧王怎麼辦? 他是顏傾天下的寧王,冷酷狠辣,運籌帷幄,隻因被她救過一命從此對她極度容忍。 第一次被穆千翊詢問,是否願意嫁給她,他怒火滔天! 第二次被穆千翊詢問,他隱忍未發。 第三次,他猶豫了:讓本王好好想想……
102萬字8 40383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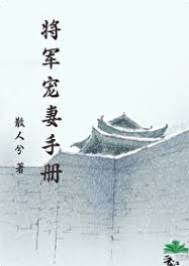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