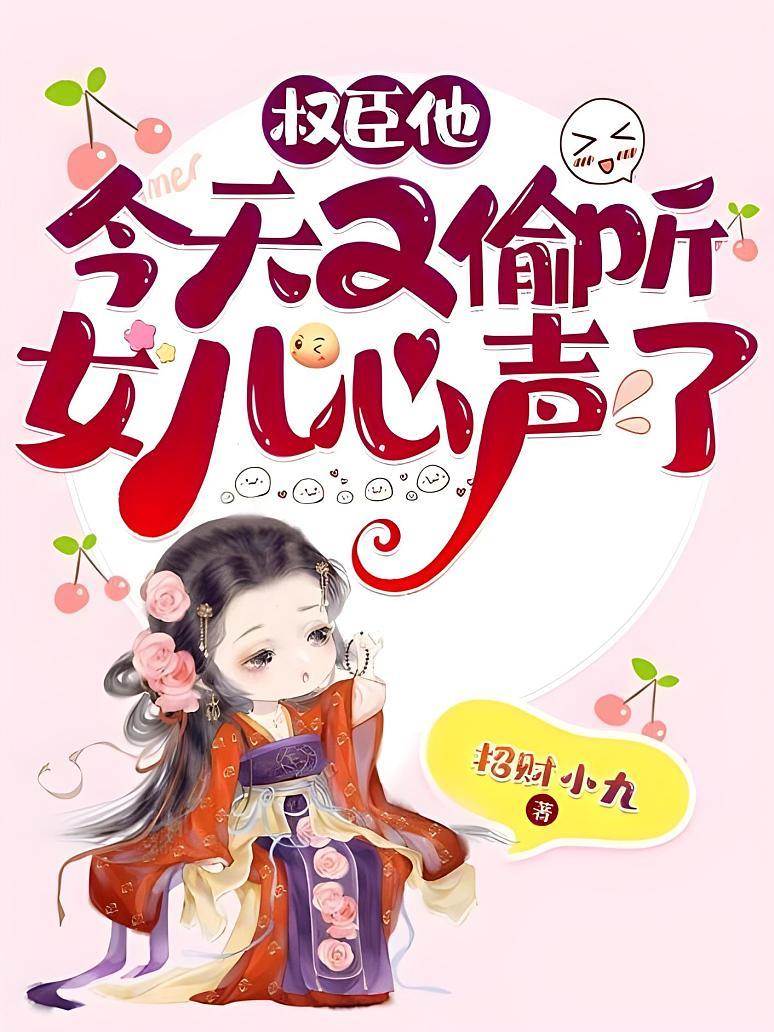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閨寧》 第252章 城府
話音悠閑,在他慣喝的明前茶因為熱水浸泡而漸漸舒展開的香氣里,盤旋於謝元茂的耳畔,揮之不去。
謝元茂看著端坐在對面,姿態愜意的三哥,不由得心中微冷,上乏力,只得以手撐桌,方才勉強未再失了方寸。桌上灑了茶,在潔如鏡的桌面上緩緩流淌。
手掌頓時便沾上了仍舊溫熱著的茶水,沿著掌心紋路直往袖口而來,轉瞬間袖子也了一截,模樣狼狽。
他語塞,不知如何應對謝三爺的提議。
謝三爺也不催促,只閑適地喝著茶,一副有竹的模樣坐在那,連看也並不看他一眼。
謝元茂的心便愈發冷了,他這樣子,分明就是吃定了自己會答應!方才說的那些個話,並不是詢問,而是知會。這樣想著,謝元茂的眉不皺了起來。
良久,他極力正起來,勉強用強的態度同謝三爺說道:「三哥休要說笑,長平侯府再落魄,也是侯府。兩家又是從小便將兒親事給訂下了,這會要將芷姐兒換人,林家人難道會應下來?」
略說了幾句,他也知道這件事不論怎麼看,都是謝三爺比較理虧,遂跟著道:「饒是京城各家的唾沫星子,也夠淹死人了!」
謝三爺聽了卻只是笑,圓胖的下笑得疊起,像是生了兩個。
他著謝元茂連連搖頭:「唾沫星子淹死人?六弟真真是多慮!這回芷姐兒宮,可不是我自個兒的主意,那是……皇上的意思!」話至尾聲,已低不可聞,但語氣卻是意外的堅定跟張揚。
即便來日林家心中不滿,恨不能立即從他上咬下一塊來,他們也奈何不得他。
甚至於,林家人連將這件事鬧大,怕是都沒有可能。
至多,也不過就是代替謝家六姑娘嫁長平侯府的謝姝寧,不討婆家歡心罷了。
Advertisement
而這些,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林家眼下這種境況,想要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也得看家中唯一的男丁林遠致是否有耀門楣的本事。依謝三爺看,林遠致可遠沒有這樣的能力。
故而林家給不了他助力,也給不了謝家助力。
謝家的姑娘嫁林家后,過的日子只要不難看到鬧到坊間,就都不能個事。
明眼人皆瞧得出來,嫁去林家,同棄子無異。
府上年紀尚算合適的,不過一個謝姝寧再一個二房謝四爺所出的五姑娘。可五姑娘的年紀比謝芷若還長,今年春上親事也已說定了,二房容氏是個難纏的,如果容氏在帝心也勉強還有一塊位置,謝三爺思來想去,便覺得謝姝寧最合適。
何況,是謝家主退了燕家的親事,后嫁了林家,真說出去,也是林家的臉面大。
謝三爺自覺十分滿意。
於是他殷殷勸說起謝元茂來:「老六,這件事於咱們家來說,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謝元茂只吃了些茶,滴酒未沾,人還清明得很,焉能就這麼傻傻地信了。見謝三爺當著他的面就開始胡說八道,不由心頭暗惱,下意識口而出:「三哥先前才說了句長平侯林家不過是門破落戶,這會倒就了百利而無一害?阿蠻雖然不如芷姐兒,那也是謝家大好的一個兒,怎地就只能去配了林家的人?」
「老六你先不要發脾氣!」謝三爺一臉的風輕雲淡,「林家雖不氣候,但到底也是侯府,家中沒有兄弟,阿蠻將來也就沒有妯娌,等到老太太一死,闔府盡掌在手,正正經經的侯夫人,哪不好?」
謝元茂一字字聽著,莫名覺得這些從謝三爺口中說出來話,帶著幾分耳。
似乎很久以前,他也曾在某從某人裡聽過差不多的話。
Advertisement
似乎也有人,在用這般拙劣的腔調反反覆復催眠對方。
他擱在桌上的手慢慢地收到了桌下,攥了自己噠噠的袖口。
是了,他記起來了。
多年前,他得了結燕家的機會,匆匆趕回府,面向宋氏時,說的那些話,可不正同今次謝三爺說的,一般無二?
難怪,難怪他說了那許多,也沒能宋氏答應下來,原來這些話聽起來竟是如此人發笑。
謝元茂掌心,也不知是被袖口沾著的茶水所浸還是沁出了汗來。
他苦笑:「林家不過爾爾,三哥想讓芷姐兒宮,索退了林家的親事又如何?」
謝三爺聞言皺眉,恨鐵不鋼地道:「糊塗,林家今日雖破,但來日方長,你怎知就沒有起來的那一日?結仇一事,能不做便不做。」
「難道換了人嫁過去,便不結仇?」謝元茂震驚,「三哥這打的是哪門子算盤!」
謝三爺「哈」地笑了聲,「你幾年不在場走,竟連這個也鬧不明白了?不在明面上鬧開,林家就只能吃他的啞虧!即便將來林家起來了,林遠致那小子是個人,也始終無用。謝家到底還是嫁了個兒去林家,兩家仍舊是姻親,該忍的,只能繼續忍著。」
他這樣的人,又豈能不步步都思量妥當?
謝三爺看向自家六弟的眼神,極為耐人尋味。
他分明,是算定了謝元茂無力辯駁。
謝元茂亦彷彿陡然間清醒,憤而拂袖起,「三哥打的一手好算盤!這事我不答應!」
好好的一個閨,憑什麼拿去於人做嫁,嫁去林家對三房眾人而言,分明沒有一好!
然而話已至此,謝三爺卻忽然冷笑起來:「榮辱與共,你可明白?」
「榮是三哥的,辱是我的,哪來的共?」謝元茂咬牙切齒地道。
Advertisement
謝三爺嗤笑,「你姓謝,這就是共。」
謝元茂重重搖頭:「三哥這事做的太不地道,休說我不答應,家中眾人想必也不會答應!」
「這件事,老爺子跟老太太都已經應下了。」謝三爺搬出了謝家的兩位長輩來,腰桿便更直了些。
謝元茂愕然:「不可能!」
謝三爺失笑:「為何不可能?若無把握,我豈能直接來尋你說話?再者,如果不是知道芷姐兒只要進了宮,將來必不會差,我又怎麼能斷送了同林家的親事,非要送宮不可?老六啊……」他長嘆了一聲,「皇上有意提拔謝家,若,謝家來日便能易地而居,從北城遷往南城,不過時日問題。」
皇城就在南城,南城歷來是王公侯爵所居之地,北城不過是尋常宦所居。
因而其言下之意,便是謝家極有可能,會從基上一了。
這麼一來,闔府上下,又有誰還會捨得反對謝三爺的提議。
謝元茂的目有些咄咄人:「從北遷南,若這般容易,京城地界早了套了。」他低了聲音,「皇上又沒糊塗!」
謝三爺斂目:「這話是皇上親口應承下的,你信不信都一樣,終歸事已定局。」
等到謝芷若先了宮,事落實后,便要求林家換了婚書上的人,林家只能照辦,否則還能鬧到皇上跟前去不?
謝三爺重重擱了茶盅,起要走。
剛邁開兩步,他猛地被謝元茂給拽住了。
謝三爺回頭低斥:「老六你這是做什麼?」
謝元茂鐵青著臉:「宋家不會答應的。」
「宋家?」謝三爺怔了怔,旋即黑了臉,「阿蠻姓的是宋還是謝?」
謝元茂極怕宋延昭,雖知隔得遠,但只要想起便仍是心有餘悸,因而愁眉不展恨聲道:「這事不妥!」
Advertisement
謝三爺無心同他繼續說下去,一把出手來:「母親那親近得了些進貢的大紅袍,品相味道皆是上佳,念著你喜歡,叮囑我同你說一聲,回去後去梅花塢走一趟。」
老太太已數年不理這種事,但這回,也忍不住還是親自出馬了。
謝元茂有種回到了當年他初初帶著宋氏母子幾人回到京城時的覺,心下冰冷一片,犯起噁心來。
兄長這是本就沒拿他當回事。
***
回到了府里,果真已有人長房的人在候著,他沒能回三房知會宋氏一聲,便被帶了過去。
長房老太太半頭華髮,正坐在炕上念經,見他來也沒停下,直至他坐立難安恨不得直接打斷了老太太的誦經聲時,才將手中佛珠往炕桌上一放,睜眼看向兒子,道:「老三都將事說了吧?」
謝元茂著滿頭的大汗:「說了,這事不合適。」
「我也知道不合適。」長房老太太咳了兩聲,「但是老六你忘了,翊哥兒才是三房的本,阿蠻說到底只是個姑娘。你幾位姐妹的親事,當年哪一個不是為了謝家打算的?到了阿蠻這一輩,也是一樣的。」
謝元茂一愣,突然語塞。
長房老太太繼續道:「哪怕敏姐兒好好的,年歲也太小了些,何況是個庶出的,不妥。林家雖不,到底是要嫁過去做侯夫人的,一個嫡字不得。阿蠻眼瞧著沒兩年也就及笄了,親事左右不過如此,能做個正經侯夫人,也不算太差。」
近些年,京里也是風雲突變,謝三爺的嫡長嫁進了李家,李家出了兩任皇后,本是風無限的才是。
誰知轉眼間,李家就快不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66 章

來人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啥? 身為王牌軍醫的我穿越了, 但是要馬上跟著王爺一起下葬? 還封棺兩次? 你們咋不上天呢! 司夜雲掀開棺材板,拳拳到肉乾翻反派們。 躺在棺材板裡的軒轅靖敲敲棺材蓋: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282.6萬字8.18 227621 -
連載1841 章

重生後我嫁了未婚夫的皇叔
前世,她是貴門嫡女,為了他鋪平道路成為太子,卻慘遭背叛,冠上謀逆之名,滿門無一倖免。一朝重生回十七歲,鬼手神醫,天生靈體,明明是罵名滿天下的醜女,卻一朝轉變,萬人驚。未婚夫後悔癡纏?她直接嫁給未婚夫權勢滔天的皇叔,讓他高攀不起!冇想到這聲名赫赫冷血鐵麵的皇叔竟然是個寵妻狂魔?“我夫人醫術卓絕。”“我夫人廚藝精湛。”“我夫人貌比天仙。”從皇城第一醜女到風靡天下的偶像,皇叔直接捧上天!
331.1萬字8 71759 -
完結332 章

首輔寵妻錄
侯府嫡女沈沅生得芙蓉面,凝脂肌,是揚州府的第一美人。她與康平伯陸諶定下婚約後,便做了個夢。 夢中她被夫君冷落,只因陸諶娶她的緣由是她同她庶妹容貌肖似,待失蹤的庶妹歸來後,沈沅很快便悽慘離世。 而陸諶的五叔——權傾朝野,鐵腕狠辣的當朝首輔,兼鎮國公陸之昀。每月卻會獨自來她墳前,靜默陪伴。 彼時沈沅已故多年。 卻沒成想,陸之昀一直未娶,最後親登侯府,娶了她的靈牌。 重生後,沈沅不願重蹈覆轍,便將目標瞄準了這位冷肅權臣。 韶園宴上,年過而立的男人成熟英俊,身着緋袍公服,佩革帶樑冠,氣度鎮重威嚴。 待他即從她身旁而過時,沈沅故意將手中軟帕落地,想借此靠近試探。 陸之昀不近女色,平生最厭惡脂粉味,衆人都在靜看沈沅的笑話。誰料,一貫冷心冷面的首輔竟幫沈沅拾起了帕子。 男人神情淡漠,只低聲道:“拿好。” 無人知曉,他惦念了這個美人整整兩世。
53.2萬字8.33 6779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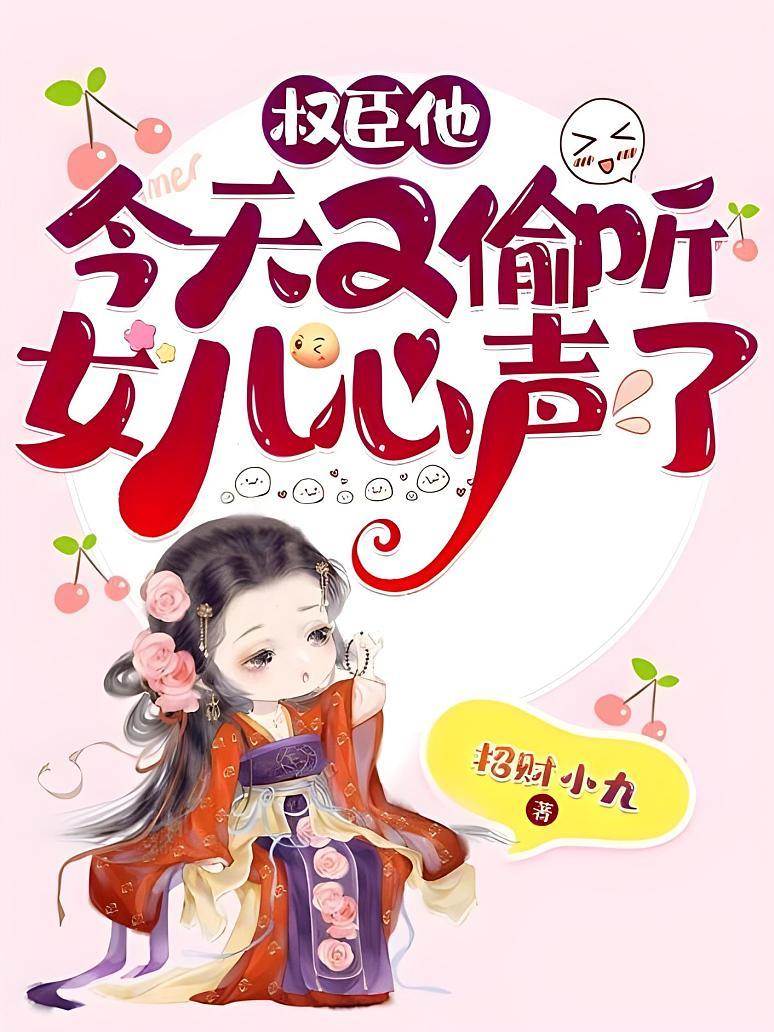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