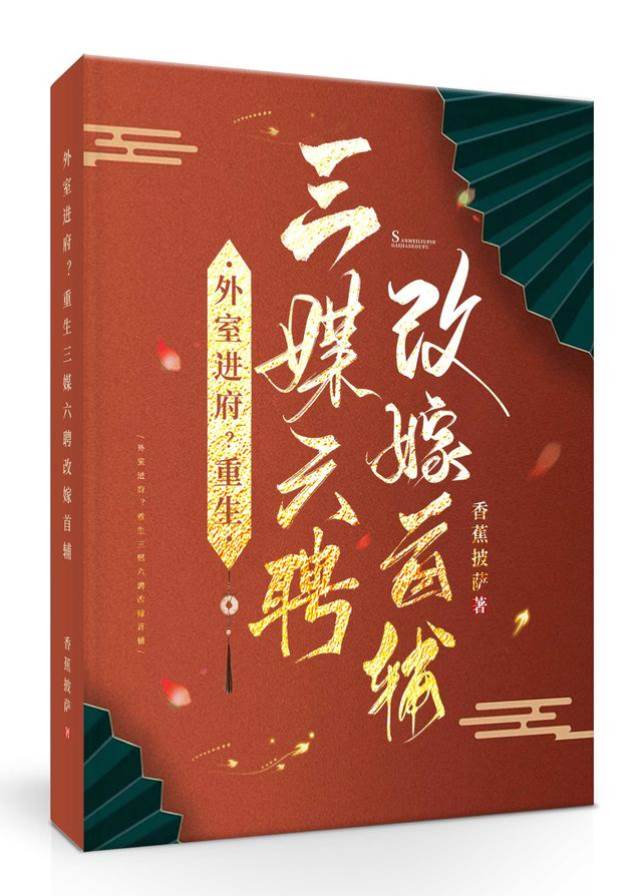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生於望族》 第321章 意外旨意
文怡很快便備好了禮與帖子,先派人送去滬國公府。國公府的兩位阮小姐大概是拿不準的意思,只是見帖子上的用辭都照著禮數來,想著丈夫柳東行畢竟也是軍中頗看好的新秀,便收了帖子。
約定的日期就是第二天。文怡只象平日出門做客時一般穿戴,只帶著一個丫頭一個婆子,坐著馬車便去了滬國公府。到了地方,又在外頭小花廳裡等了足有半個時辰,方纔見到了阮家二小姐。
阮二小姐本就比姐姐與文怡相,只是今日見了,態度也是淡淡的,雖然臉上掛著笑容,卻不過是礙著禮數罷了,哪裡有當初的親熱?
文怡自然能覺到對方的冷淡,覺得這似乎跟太子妃說的話有些不同——太子妃曾道,們不過是有些抱怨罷了,但這般客套的態度,哪時象是在對曾經是朋友的人說話?文怡一時有些退了,臉微微紅,只覺得自己好象在自取其辱,只恨不得趕告辭了事,畢竟阮二小姐的話裡似乎顯出那麼一送客的意味。
但文怡心裡掙扎過後,還是堅持下來了,想起自己才立下誓願兩日,若是遇到一點難,便打了退堂鼓,那要改變自己的決定不過就是個笑話,更何況,自己確實是有理虧之的,不是來結國公府的千金,而是爲自己的錯誤向朋友道歉,只要得償所願,即便得不到朋友的諒解,也總算是嘗試過了。於是便著頭皮,面帶微笑,以一種親切又不失禮數的語氣說著自己的來意,再回顧了一下從前與阮家姐妹來往時的好回憶,併爲自己在之前半年裡的怠慢與疏遠道歉。留了心,從頭到尾。都保持著朋友間平等對話的語氣,務必不出一半點兒的仰敬氣息。
Advertisement
阮二小姐阮孟萱一直不鹹不淡地微笑著傾聽的話,聽到後來,卻漸漸有些容,頭一次正面看著說話:“柳恭人這話也未免太謙了,其實也沒什麼。孩兒出了嫁,自然是不如先前在家時隨意的。我聽說柳將軍早就分家獨立了。家裡又沒個長輩持,你爲當家主母,自然是忙得不開。我們姐妹之間不過就是玩笑間抱怨兩句罷了,並沒有放在心上。柳恭人實在不必把這點小事當什麼正事看待的。”
文怡誠懇地道:“家裡事務雖忙,但也不是沒有空閒,是我自己子擰了,總是顧慮太多,纔會怠慢了你們。這原是我的錯,心裡也一直惦記著。覺得對不住你們,只是怕你們惱了,才遲遲不敢上門來賠不是。可如今,我就要離開京城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幾位,若再不來。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呢?你們不怪我,這是我的福氣。”
阮孟萱抿一笑:“你也太實誠了,隨便拿出個理由來嘛,比如家裡事兒多啦,親戚們麻煩啦,還有避嫌啦,什麼的。我也是明白的。柳大學士夫人的脾氣,我們也曾聽過的,還有顧侍郎家裡,前些日子,四請託人去向黃家提親,聽說差點兒就找上你了是不是?”
文怡一怔,萬萬沒想到對方消息如此靈通,深孃家族人丟臉了,臉一紅,乾笑道:“外頭人都知道了麼?這……這真是……畢竟是隔房的,長輩們行事,我們又不好攔著……”
阮孟萱笑得更歡了:“我就知道,你還是個明白人,只是運氣不好,沒遇上好親戚。行啦,多大點兒的事?別說你夫家如今的形了,姐姐與我,還有靈兒、玥兒兩個,平日裡與人往,何嘗沒有過許多顧慮?從小到大,也不是沒有一起玩得來的朋友因爲家裡的關係疏遠了的,大家心下明白,也沒什麼好抱怨的。誰想你卻是老老實實,只說是自己子擰,故意不理我們的。你就不怕這話說出來,我真惱了你?要知道,我們姐妹最討厭的,就是子擰的人了。就象你顧侍郎府從前的五小姐,你的堂姐,如今嫁給柳學士家大公子的那一位,如今在外頭走,越發擰了,我們都不願意與說話。”
Advertisement
文怡有些窘迫:“我自個兒知道是什麼緣故,若是把錯都推到別人上,豈不是更顯得擰了?那樣也太不實誠了。”有意略過了阮孟萱對文嫺的議論。
阮孟萱掩口低笑,哂道:“行啦,你今兒既來了,可見以後不會再擰了。從前那點小事就抹了吧。”歪歪頭,又笑了,“其實咱們之間也沒什麼可抱怨的,是不是?不過是時間長了見幾面罷了,居然還拿來當回事,在這裡說了半日。”又問文怡:“春熙訂了親事,你一定知道吧?可惜了,你這就要走了,沒法送出閣。”
文怡暗暗鬆了口氣,也笑道:“正是呢,爲此抱怨了我半日。不過我已經備好添妝的東西了,正打算臨走前再給呢。”
阮孟萱忽然湊近了低聲說話:“我聽說……這親結得極有意思,還有些秩事趣聞在裡頭,你家那位是親眼見的吧?我問春熙,不肯講,別人呢,都是男人,我又不好意思問。快給我說說吧,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有人說,小傅將軍被打得吐了,才娶得人歸的?”
文怡大汗:“這是哪兒來的傳言?”雖說傅仲寅上是沾了跡,但那不是吐的吧?
“那快給我說說!”阮孟萱一臉興致,“家裡的哥哥們都不知道打哪兒聽來的傳聞,把春熙說得象個夜叉似的,軍裡的人都說小傅將軍可憐。我就不信,雖說能打,可也不是不講理的呀?再說了,對小傅將軍可是一直推崇得很,心裡對這門親事未必就不願意。”
文怡無奈地嘆了口氣,爲了表姐妹的名聲,只得將自己所知道的形,略加刪減,去些許細節,通通告訴了阮孟萱。
Advertisement
阮孟萱聽得好笑:“原來如此!李家小弟那張臉,誰見了都不信他是好人。不過這般著上場,也難怪小傅將軍吃不消了。”頓了頓,眼珠子一轉,“不對……我聽說他在北疆的時候,曾連續追趕敵將六個時辰,一路連追帶打。都不見有毫疲,這不過是一兩個時辰的事。哪裡就累著了?況且春熙手如何,你我都清楚,便是有心考驗小傅將軍,也不會出手沒輕沒重,把人打出來呀?這……該不會是苦計吧?”
文怡心下佩服,眨了眨眼:“是什麼計,又有什麼要?橫豎是周瑜打黃蓋罷了。李大人和李太太還在旁邊看著呢,怎會讓小傅將軍真個傷?”
阮孟萱笑了:“原來如此,我就知道。若小傅將軍真個造了假,春熙會看不出來?果然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文怡離開滬國公府的時候,阮孟萱笑著親自送出了二門,就在上馬車時,阮大小姐那邊也派丫頭送了禮過來。併爲自己的怠慢向賠禮。阮孟萱笑著向文怡眨眨眼,小聲道:“大姐害臊呢,是快要出嫁的人了,天窩在屋裡繡的嫁妝!”
阮大小姐的丫頭在旁卻笑道:“二小姐,您只顧著說大小姐,怎的不說說自己?您不也快要出嫁麼?怎麼就不繡嫁妝?”
阮孟萱飛紅了臉:“死丫頭,看我撕了你的!”那丫頭一躲。笑著跑開了。聽到文怡的笑聲,又回頭來瞪後者。
文怡輕咳一聲,再次告別:“我要走了,多保重。”接著抿補充一句:“改日我再把添妝送過來啊!”然後便在阮孟萱的惱聲中笑著上車走了。
接下來的兩日,文怡又去了龍家與查家,倒比在滬國公府更順利些。龍靈是個不計較的人,加上阮家姐妹給遞了信,文怡纔開口,便笑著將事抹過去了。至於查玥,雖說子潑辣,還有些小心眼,但與文怡本就不算親近,倒也沒把的疏遠放在心上,反而更關心蔣瑤:“也不打聲招呼就走了,一走幾個月,聽說已經定了親,難道將來就不回京了麼?好歹要給我們來封信呀!”文怡答應會給蔣瑤捎信替抱怨,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Advertisement
文怡把心裡的這件事辦了,只覺得鬆了一口氣,連帶的信心也增強了許多,再次面對柳家與顧家長房的族人親戚時,也更應對自如了。原本在面對他們的時候,除了兩三位要好些的長輩與姐妹,對其他人就只是以應付爲主,務求禮數上不出錯,不人拿住把柄,若是對方找渣,才見招拆招,有時候難免要些氣。但如今事手腕有了長進,面對這些人時,開始主迎上去說笑,儘可能將話題維持在自己希的範圍,即便別人將話題引開,也會再度扯回來。
不得不說,這種辦法還算有用。於老夫人接連尋藉口了文怡過去,一次是爲蔣氏生病,一次是問及盧老夫人起程的日子,再有一次是問文慧的傷,三次都了兒柳顧氏回來,坐在自己邊,讓後者有機會與文怡多說些話,結果三次都被文怡扯開了話題。每當文怡看著柳顧氏在一旁滿面憋悶卻說不上話的模樣,心裡便暗自歡喜,回家告訴柳東行,柳東行也覺得十分解氣。但他有一點不明白:“這幾日二叔也時不時派人來我回去,我都拿公事推了,如今二嬸又是這般,他們究竟打什麼主意呢?”
wωw● ттkan● ¢O
文怡想了想,道:“不論他們要打什麼主意,我們只管收拾行李,等事料理完了一走,他們做什麼都再不與我們相干了。”
柳東行笑著點頭,又拿出一疊銀票來:“這裡是一千八百兩,小傅想買我們在京南的那座莊子,我見是他,也就便宜賣了。你收好吧,我們家若還有人在那裡,就回來,過兩日就接。”
文怡應了,一邊收好銀票,一邊笑道:“那莊子賣給他家,倒也是個好去,省得再留人看守了。”卻又想起冬葵是被打發到那裡去的,還有那馬有財,也在東邊的莊子裡尚未回來,忙傳令下去,讓人去接他們。
誰知道舒平卻從外頭跑回來,急急人傳信給柳東行,請他出去。柳東行不知何故,與文怡一起到了二門,只聽得舒平道:“大爺,二老爺那邊發話,說要在京裡開祠堂祭祖,爲太夫人、大老爺與大太太辦法事呢!”
“你說什麼?!”柳東行懷疑自己聽錯了,“你說……二叔要爲祖母、父親與母親辦法事?是什麼名義?!”
“是柳家大太夫人、嫡系大老爺與大太太的名義!”舒平嚥了咽口水,“小的生怕聽錯了,便找在學士府裡當差的親戚打聽過,聽得柳家的家生子們都在議論,說二老爺與二夫人似乎打算承認大爺這一脈的名分呢!”
柳東行全一震,有些茫然地看向文怡。文怡也十分不解:“我瞧二嬸的神,雖說象是想跟我說些什麼,但那語氣可一點兒都不客氣,怎麼才一會兒功夫……二叔變化也太大了吧?”
柳東行深吸一口氣,冷笑一聲:“這是好事。他願意主出面,我沒理由不應!”便吩咐舒平:“趕再派人去打探!再跟門房說,若是二叔那邊有信來,馬上告訴我!”
他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本以爲這件事要在回鄉祭祖後,才能如願以償,沒想到柳復會主提起——莫非二叔總算認清現實了?爲了拉攏他這個侄兒,連往日最看重的名份都不顧?
文怡卻總覺得有些不妥,柳二叔這一轉變,也未免太過突然了,至很清楚,二嬸在先前見面時,絕對還沒有這個意思,不然對方不會是那樣的態度。
就在夫妻倆都覺得不解之際,又來了一個更令他們意外的消息:聖上下旨,褒獎柳門容氏,加封正二品貞義夫人,褒獎其仁義貞淑,可爲天下婦人典範,云云。
柳東行接過聖旨,聽著傳旨的監恭喜的話語,再回頭看向文怡,只覺得如在夢中。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連載162 章

東宮美人
宋懷宴是東宮太子,品行如玉,郎艷獨絕,乃是世人口中宛若謫仙般的存在。南殊是東宮里最低下的宮女。她遮住身段,掩蓋容貌,卑微的猶如墻角下的殘雪,無人在意。誰也未曾想到,太子殿下的恩寵會落在她身上。冊封那日,南殊一襲素裙緩緩上前,滿屋子的人都帶著…
51.2萬字8 8875 -
完結919 章
娘子很剽悍
前世她不甘寂寞違抗父命丟下婚約與那人私奔,本以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幸福生活那知沒兩年天下大亂,為了一口吃的她被那人賣給了土匪。重生后為了能待在山窩窩里過這一生,她捋起袖子拳打勾引她男人的情敵,坐斗見不得她好的婆婆,可這個她打架他遞棍,她斗婆婆他端茶的男人是怎回事?這是不嫌事大啊!
85.9萬字8 2980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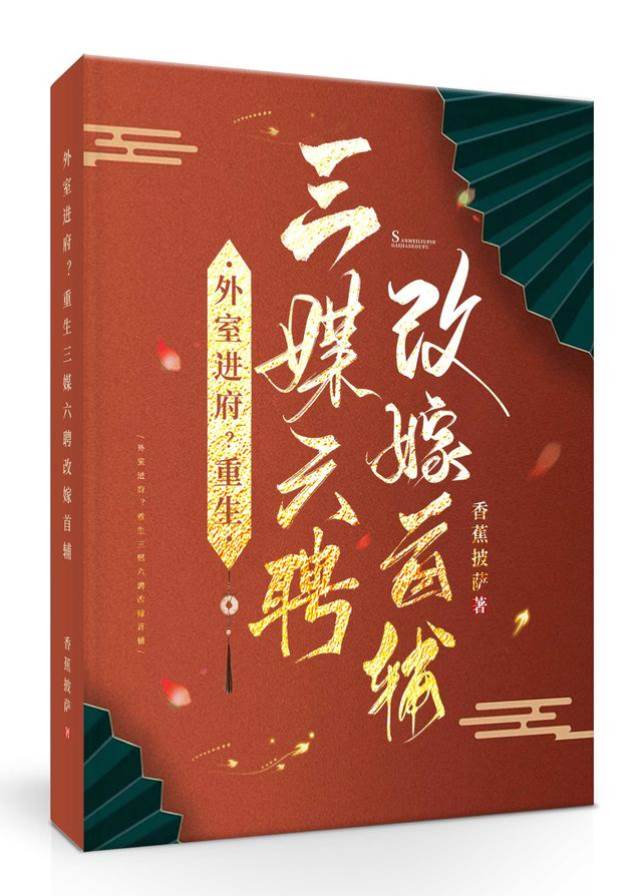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
完結239 章

寵妾滅妻奪嫁妝?廢你滿府嫁皇家
前世,謝錦雲管理後宅,悉心教養庶子庶女,保住侯府滿門榮華。最後卻落得一杯毒酒,和遺臭萬年的惡毒後母的名聲。死後,她那不近女色的夫君,風光迎娶新人。大婚之日,他更是一臉深情望着新人道:“嬌兒,我終於將孩子們真正的母親娶回來了,侯府只有你配當這個女主人。”謝錦雲看到這裏,一陣昏厥。再次醒來,重回前世。這一次,她徹底擺爛,不再教養狼心狗肺之人。逆子逆女們若敢惹她,她當場打斷他們的腿!狗男女還想吸血,風風光光一輩子?做夢!只是,她本打算做個惡婦,一輩子在侯府作威作福。沒想到,當朝太子莫名伸手,先讓她成爲了下堂婦,後又欽點她爲太子妃?她還沒恍過神呢,發現一直仇恨她的庶子庶女們,一個個直呼後悔,說她纔是親孃。昔日瞧不起她的夫看,更是跪在她面前,求她再給一次機會?
44.2萬字8.18 36260 -
完結185 章

小娘,你也不想王府絕後吧
西南王季燁出殯那天,失蹤三年的長子季寒舟回來了。爭名,奪利,掌權,一氣嗬成。人人都說,季寒舟是回來繼承西南王府的,隻有雲姝知道,他是回來複仇的。他是無間地獄回來的惡鬼,而雲姝就是那個背叛他,推他下地獄的人。她欠他命,欠他情,還欠他愛。靈堂裏,雲姝被逼至絕境,男人聲音帶著刻骨的仇恨與癲狂“雲姝,別來無恙。”“我回來了,回來繼承父王的一切,權勢,地位,財富……”“當然也包括你,我的小娘。”
27.5萬字8.33 87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