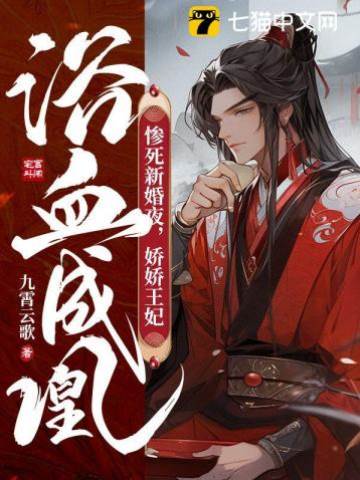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重生之美人計》 全文閱讀 - 219 瘋狂狩獵
元烈眸子裡閃過一冷的芒,抬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圖,我打獵的時候可不想別人打攪了我的興致,趁我沒有發怒,你該滾就快滾!”
“你說什麼?”圖不變了臉,在這片草原上還從來沒人敢這樣和他說話,他怒聲地道:“你這兔崽子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膽了!”隨即他策馬向前,丟了弓箭,揚起長鞭就要給元烈一鞭子,但是元烈的作卻明顯比他更快,他策馬上去,一腳踹開了圖下的烈馬,那馬長嘶一聲,突然仰天長嘶一聲,踢踏個不停,不斷噴著鼻息,開始變得暴躁不安。圖畢竟是馬上的勇士,他費了好大的功夫才將馬兒安下來,瞪著元烈厲聲地道:“你是哪裡跑出來的雜種!?”
雜種這兩個字明顯讓元烈到不悅,他的眼神驟然變得淩厲,騎著馬緩緩地了上去:“草原大君的兒子怎麼這樣不懂規矩,雜種也是你喊的嗎?睜開你的狗眼看看,你招惹的究竟是什麼人?”他話一說完,已經劈手給了圖一掌,圖沒有防備,整個人狼狽地從馬上滾了下來,不敢置信地倒在地上,愣愣地仰頭看著元烈。元烈在馬上居高臨下地看著他冷冷笑道:“回去向你父親說,是旭王元烈欺負了你,讓他去請皇帝責罰我!”
圖立刻就要跳起來,他可不管什麼旭王元烈還是什麼鬼的,這人的名字他聽都沒有聽過!他再也沒辦法忍耐,大聲命令自己的護衛道:“抓住他!抓住他!”
可就在此時,元烈旁的護衛已經出了馬鞍上的劍柄,數把長劍架在了圖的脖子上。圖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屈辱,他旁邊跟隨的護衛也是大驚失,誰不知道圖將是這片草原的繼承人,又有誰敢在他面前這樣無禮呢?便是越西的太子殿下,為了爭取草原大君的支持,也多次表示禮遇和優待。可眼前這個自稱旭王的男子,卻明顯不將草原上的人放在眼睛裡。
Advertisement
那些護衛驚慌地互相看著,其中一人立刻上來大聲地道:“你是越西的親王嗎?這位是我們草原大君的世子,你萬萬不可傷了他,否則你們皇帝也不會饒過你的!”
元烈卻突然大笑了一聲,他的長劍挑著風聲向著圖的頭頂斜斜地削下,旁邊的護衛驚呼道:“住手!”
圖驚恐地跌坐在地上,他的護衛甚至沒有來得及救他,在這個瞬間他的目變得越發的驚恐,只覺得頭上一涼,幾乎以為自己要被削掉腦袋,頓時屏住了呼吸,下意識地出手了,才發現心養了多年的辮子竟然被對方削了一半。他丟盡了臉面,額頭的青筋迅速了出來,下一刻就要然大怒。
元烈冰涼的劍鋒扁平著在他的頭頂上拍了拍,語氣淡淡地道:“記住,下次不要得罪你不該得罪的人!還有,那頭小狼……”
當圖到元烈眼中迸發出的殺意的時候,他意識到對方絕不是在跟他開玩笑,真是了殺心的。圖不是蠢人,他馬上住了怒氣,改換了語聲道:“是你的,那小狼是你的,送給你了!”
元烈笑了起來,目之中劃過一嘲諷,冷聲地道:“滾。”
圖立刻跳了起來,捂著頭飛快地跑了,他的護衛愣了一下,隨即騎著馬追上去道:“世子,世子,你的馬!”元烈站在原地,目幽冷地看了圖的背影一眼。旁邊的趙楠騎馬上來道:“殿下,這事該如何理。”
元烈淡淡一笑道:“把那小狼捉起來就行了,其它的,不必你管。”
趙楠目之中掠過一憂慮,這圖畢竟是草原大君的兒子,可元烈明顯沒有將對方放在眼裡。而且,主子命令等於一切,他只能無條件的遵從。當下,護衛們圍了一個圈子,將那頭小狼包圍了起來。
Advertisement
而此時的獵場之上,皇子們之間的爭奪倒在於其次,眾人的目漸漸落在了裴家和郭家人的上。郭澄原本打獵打得好好的,突然一騎烈馬飛奔了出來,擋在他的面前,郭澄揚起眉頭,對方正是裴家的二公子裴徽。裴徽笑容滿面地道:“郭公子,賽一場麼?”
郭澄冷冷地挑起了眉頭,似笑非笑道:“好,也不必浪費力氣,一場定輸贏吧!”
裴徽點頭,微笑如一位溫文的公子:“那我們就開始吧。”
此時,郭家兩個兄弟都聚攏過來,而裴家的另外三個人也策馬而立,追隨著裴徽。裴徽長嘯一聲,風馳電掣一般地騎著馬,追逐著一頭鹿,這一次,他和郭澄的目標便是比賽誰先中這頭鹿。幾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圍了一個圈子,那鹿踏著舞步一般地轉來轉去卻是轉不出去。每一回郭澄出的長箭都被裴徽半途攔截,而郭敦意圖近那鹿的舉也被裴搶在瞬間閃掠過。
郭導冷笑一聲,他再次舉起弓箭,猛地出了一肩,眼看那箭距離鹿不過是十米的距離,卻被裴出的一箭猛烈地一撞,頓時偏了方向,一下子斜刺了地上。
“三哥,你來!”郭敦大聲地喊道。
郭澄下那匹黑的馬以難以追擊的速度趕上了那頭鹿,已是搭弓箭,蓄勢待發!遠的人們看到郭澄已是勝利在的模樣,不由高聲喝起了彩,郭澄卻在此時覺得背心發寒,忽然覺得一陣犀利的風聲追逐而來,他猛地回頭、隨即一驚,短短的一瞬之間心念急轉,他整個人後仰在馬上,堪堪避過了這一箭。而這箭的人,不是裴徽又是誰呢?
郭家兄弟面一沉,這不是什麼狩獵,而是死戰,裴徽剛才明明就是想要郭澄的命。郭敦怒聲地道:“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麼!”
Advertisement
裴徽冷冷一笑道:“獵場之上,刀劍無,你們眼睛還是放亮一些,千萬不要擋在我的前頭,否則這一箭,可就饒不過你們了。”他說著這樣冷酷的話,臉上卻是帶著笑容。遠的人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只以為裴徽那一箭是向著鹿而去的。可只有郭澄才知道,剛才死亡離他是多麼得近。
“你真是狠毒!”郭敦大聲地喊道。
“狠毒不狠毒有什麼要,只要贏了不就行了麼。”裴獻策馬上來,笑容十分的冷。
郭敦滿面怒,即將暴走,卻被郭導拍了拍肩膀。郭導在一旁冷聲地道:“他們能如此,我們就不能嗎,這本來就不是什麼獵場,而是生死之爭。”兄弟兩人換了一個表。就在此時,他們看見裴徽的馬已經追上了鹿,眼看著就要出一箭,郭敦自策馬上前,攔住了裴,而郭導以一敵二,攔住了裴獻和裴白,唯獨剩下裴徽一騎,正向那鹿飛奔而去,郭澄冷笑一聲,騎著馬隨其後。此時,那頭鹿已經趁著他們爭奪的瞬間向草原深飛奔而去,裴徽冷笑一聲,執起長弓就要出去。誰知片刻之間,他的弓箭卻自己彈了起來,不知怎麼回事瞬間手中竟然只剩下了箭而不見了弓。他立刻勒了韁繩,馬兒高高地直立了起來,這才發現,他的弓竟然在瞬間被郭澄的長箭釘了地下,閃電一般的離了手掌。而他的手掌心之中,已經是鮮淋漓,若非他閃避得快,那一箭便是向他的腰腹之間!
“你好險!”裴徽厲聲地道。
他這一句卻讓郭澄笑了起來,郭澄微笑著道:“這也是向你們裴家學的。”
事實上,郭澄和裴徽的技都是半斤八兩,他們兩人都是由騎名家傳授,又都曾在戰場上曆練過,乃是當世不二出的騎高手。此時在這獵場之上自然是棋逢對手,難分高下,剛才郭澄被裴徽將了一軍,此刻自然要扳回一。
Advertisement
裴徽冷冷一笑,看了一眼自己的弓箭,狠狠的將它拋在地上,從一旁的馬之後,又出了一把長弓,他大笑著道:“鹿已經跑了,郭三公子去追吧。”
郭澄愣了一下,上下打量著裴徽,而裴徽含著笑,笑容恬淡,仿佛是一副審視的眼神。郭澄心道,不愧是裴徽,這樣被人辱也沒有當場失態。他冷淡地一笑道:“這場上若是換了別人,還不配做我的對手,你來吧。”說著,他已經隨手給了那馬兒一鞭,飛快地向前奔去。
裴獻裴白剛才都被郭導攔住,無論如何都沒辦法突圍,此刻又見到裴徽繼續向前追去,裴白狠狠地瞪了郭導一眼,調轉馬頭,飛奔著向前追去了。裴獻卻看了郭導一眼,似笑非笑地勒住馬韁繩道:“師弟,好久不見了。”郭導遙遙地看著自己兄長離去的方向,也不回頭去瞧裴獻,聲音裡淡淡的沒有:“師兄,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你,病都好了吧。”
裴獻一直都有眼疾,這事也是人盡皆知的,但郭導知道則是因為他們是同門師兄弟,都師從一位名師的教導。
裴獻淡淡一笑道:“總算還活著,怕是要讓師弟你失了。”
郭導笑容如常,卻沒有出生氣的表,事實上他和裴獻非但不是仇人,在他們小時候一起學藝的時候,還是很親的朋友。那時候裴獻不好,並不是學武的材料,所以總是被其他的師兄弟欺負,而郭導則是個頑劣,不聽教誨。兩個人竟然玩到了一起去,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有一天晚上,郭導又犯了錯,被**連夜趕下了山,他一個人在山間迷了路,在石頭裡,得快要死的時候,還以為再也見不到郭家的父母了。可是等他醒來的時候,卻瞧見了裴獻的臉,不由大為吃驚。裴獻竟然追著他一路從山上下來,找到郭導的時候,郭導只剩下半條命,整個人幹的已經快要死了。
裴獻扶著他從山上下來,可是卻到了狼群。裴獻當時不過十歲,武功微弱,也不好,被一只狼咬了一口,差點死於非命,本來他讓郭導放下他獨自逃生,可是郭導卻背著他,一路從山上走了下來。直到山上的**後悔了,又派了師兄弟將他們找了回來,他們兩人才勉強活了下來。從那時候,郭導便將裴獻當了最要好的朋友,因為裴獻不好,個又冷淡,所以在師兄弟之間向來很冷遇,於是郭導便將自己的匕首送給他,並且告訴所有的人,如果誰敢欺負他,就是自己的敵人。為了袒護裴獻,他和那些師兄弟們打了無數場架,好幾次都是重傷。正因為如此,這兩個年結下了非常深厚的友。
可是,當他們下了山才突然明白,原來裴家和郭家有那麼深刻的淵源,卻不是朋友,而是死敵。從那一天開始,兩個人就像是不約而同的,裝作對彼此都不認識。對於郭導來說,他並沒有忘記裴獻那一次的舍相救,而對於裴獻來說他也不可能忘記那些年郭導對他的維護。但那又如何呢,朋友歸朋友,死敵就是死敵,這是兩個家族間的仇恨。所以,他們只能是敵人,而不可能是兄弟,更不可能是朋友。
這一點,在裴獻再一次見到郭導的時候就已經確認了。裴獻冷淡地道:“我二哥是一定要殺了你妹妹的。”
郭導卻突然沉默了起來,良久,他的邊出一笑容,他慢慢地道:“我不會讓任何人傷害的。”
裴獻目冰冷地看了郭導一眼道:“若是連我也要殺呢。”郭導的笑容十分平靜,他了裴獻一眼道:“那我就只能連你一塊兒殺了。”裴獻只是微笑,從下山開始他就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誼早晚會有這一天的,裴獻冷笑一聲,策馬揚鞭道:“那就各憑本事吧。”
郭導注視著他離去的背影,良久沒有作,直到郭敦從背後拍了拍他的肩膀,大聲地道:“你愣著做什麼,還不快追!”
郭導微微一笑,遙遙地看了一眼李未央的方向,語氣卻是十分淡然:“你去吧,妹妹的邊沒有人保護,我不放心,我要回去了。”說著,他竟不再看向郭敦,而是策馬轉向場外跑去。郭敦看著他,不由覺得奇怪。
這邊郭家和裴家鬥得如火如荼,李未央是瞧在眼裡的。知道,郭裴兩家鬥了這麼多年,不管是在朝廷之中還是在獵場之上,都是勢均力敵,誰也不能將誰怎麼辦。但元烈上一次的行為已經徹底激怒了裴氏,猜想,對方不日將會有所作。只是,他們究竟將會怎麼做呢。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個走到李未央的面前,趾高氣揚地道:“你就是郭嘉麼?”
李未央抬起頭,了一眼,那仿佛站在之中,讓人覺得刺目。穿著豔紅的馬步,白的腰巾束在腰間,下面是寬大的擺,腳上還穿著一雙小鹿皮靴子。上很是幹練簡潔,下擺的子卻十分的寬大,方便於大步的起跳和騎馬,明顯是草原孩的裝扮。的像是被曬紅的玉,眼睛大大的,十分的清澈,眉宇之間帶著靈,與越西的小姐們不同的是,披散著黑的長發,發梢上結著小小的金鈴,走路之間,金鈴叮叮當當的輕響。
李未央沒有回答,只是目淡淡地掃過對方的眼睛,卻又看向不遠的獵場。這不由拍了拍自己的手掌道:“你沒有聽見我說的話嗎?”
李未央聞言,烏黑的眼眸微微一轉道:“聽見了,只不過我對那些沒有禮貌的人沒有興趣。”
李未央的上是煙羅的,在下自有一種淡淡的華,仿佛有一層淡淡的金霧蒙蒙地上來,看得人有一些炫目。這聞言,立刻跳了起來,面上氣得通紅道:“你說誰沒有禮貌!”
李未央微微一笑道:“在別人的名字之前,不是該自報家門麼?”
那叉著腰,面容惱怒道:“我是公主阿麗,你應該向我行禮。”
李未央角略微浮起一點冷淡的笑意,語氣十分的淡漠:“公主只是草原的公主,並不是我們越西的皇室。等你哪天嫁了越西,為了某個皇子妃,再提向你行禮的事也不遲。”
阿麗立刻暴躁起來,最討厭別人提起聯姻的事,而李未央明顯知道的痛楚,一一個準,怒氣沖沖地道:“你敢這樣對我說話,你以為你是誰!”
李未央微微一笑,慢慢地道:“那麼,你又以為自己是誰呢?”阿麗剛要斥責,卻聽見旁邊傳來一陣悅耳的聲音,仿佛帶著說不清的諷刺:“阿麗公主,我早就跟你說過,這郭家的小姐,可是誰都惹不起的。”
李未央向出聲的方向,那人腰肢纖細,姿容絕,不是裴寶兒又是誰呢。李未央的目慢慢變得嘲諷,道:“裴小姐這麼好的興致,也跑到這草原上來了,你是為了狩獵呢,還是為了和親呢,啊,莫非裴家想將你嫁到草原上做個王妃麼。”這話十分的刻薄,裴寶兒登時大怒道:“郭嘉你不要口不擇言,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是你可以隨便撒野的麼!”
李未央歎息一聲道:“我不惹人,偏偏有人來招惹我,阿麗公主,把你家的瘋狗牽回去吧。”
阿麗一愣,看了看李未央,又看了裴寶兒,有點分不清對方究竟在說什麼意思,心眼直,不過是了裴寶兒的挑唆,要看一看這靜王元英的心上人究竟長什麼模樣。
若李未央是像裴寶兒一樣的大人,阿麗公主還覺得沒什麼,但現在瞧見,這李未央容清秀,目冷淡,分明就是個冰窟窿。實在想不,這熱開朗的靖王元英,怎麼就會看上李未央呢,難道就像裴寶兒所說,僅僅是因為出郭氏麼。是啊,郭家是靜王的母族,他會從母族之中尋找王妃也是並不奇怪的,可是自從三年前阿裡公主見到靜王元英之後就對他一見鐘,打定主意非要嫁給他不可。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一個李未央,又怎麼會甘心呢。所以,揮著鞭子指向李未央道:“你起來,咱們比試一場,若你贏了,我就把靜王殿下讓給你,若你輸了,你就乖乖的離開他,再也不要肖想靜王妃的位置。”
李未央聞言便是一愣,隨即似笑非笑地看向阿麗道:“靜王妃,我嗎?阿麗公主是不是誤會什麼了,靜王不過是我的表兄而已。”
阿麗不耐煩地說:“我不管那麼多,你快點站起來!跟我比賽,不管是騎馬,還是打獵,爬樹,我都會贏你的,哪怕是你們越西子會的琴棋書畫,我也都會,絕不會輸給你!”
猜你喜歡
-
完結2063 章

亡後歸來
重重波瀾詭秘,步步陰謀毒計。她,獨一無二的狠辣亡後,發誓要這天下易主,江山改姓;他,腹黑妖孽的傾世宦官,揹負驚天秘密,陪卿覆手乾坤。她問:“玉璿璣,我要的天下你敢給嗎?”他回:“蘇緋色,你敢覬覦,本督就敢成全。”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縱觀天下,捨我其誰!
396.7萬字8 13509 -
完結503 章

重生之請妻入甕
聽聞鎮國將軍府,老將軍年老多病,小將軍頑疾纏身。作為一個不受待見的公主燕卿卿,兩眼發亮,風風火火的主動請求下嫁。本是抱著耗死老的,熬死小的,當個坐擁家財萬貫的富貴婆的遠大理想出嫁。不曾想,那傳聞中奄奄一息的裴殊小將軍化身閻王爺。百般***還…
77.7萬字8 29843 -
完結315 章

女扮男裝的男主她玩脫了
祁懿美穿成了最近看的一部權謀文中的……男主。 哦,還是女扮男裝的 眼看劇情要按權謀主線發展,為了讓自己這個權謀小白好好的茍到大結局,祁懿美果斷決定逃離主線,卻機緣巧合成了病美人六皇子的伴讀 從此她便和他綁定了,還被人們編成了CP,被滿京城
51.7萬字8.18 4709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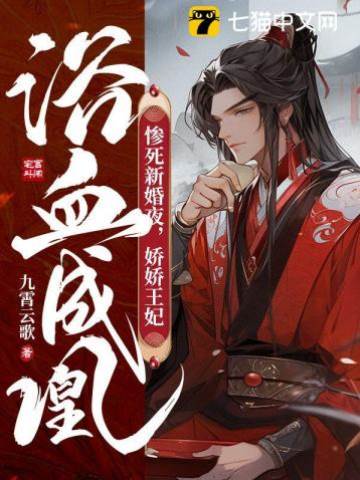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