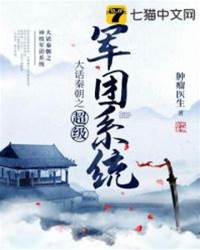《大漢帝國風雲錄》 第954章 亂世豪雄篇 長河落日
隨著朝廷收復的土地越來越多,朝廷的機構越來越龐大,各地士人也紛紛進了朝堂,朝堂上研習今文經學的大臣驟然增多。與此同時,朝堂上的權力爭奪越來越激烈,中興大業的推進速度越來越快,而朝廷里研習古文經學的大臣和研習「新經」的大臣在中興策略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於是,研習今、古文經學的大臣們為了制定和實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興策略,馬上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控制朝廷決策權的以研習「新經」為主的大臣們。
今、古經學兩派聯手對付「新經」一派,朝堂上的權力鬥爭隨即愈演愈烈。這兩年朝堂上紛爭不斷,也正是因為如此,而這次「明堂制度之爭」總算把這場爭鬥推到了高,雙方不爭個水落石出,誓不罷休。
爭論的結果不是勝就是負,沒有平手之說。
如果「五室明堂制」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新經」地位的穩固毋庸置疑。學上的穩固,影響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興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員將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新經」的地位將到嚴重打擊,雖然因為今、古文經學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新經」還能暫時維持學地位,但它的影響力會急速下降,剛剛建立的權威會然無存,而各地公、私學堂很可能會放棄「新經」,轉而繼續教授今、古文經學。久而久之,朝廷放棄「新經」為學是一種必然。
學上失去了權威,做為儒學基礎的禮制發生了變化,中興策略隨之發生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暫時對朝堂的影響不大,但隨著時間的延續,中興大業的不斷推進,這種變化會逐漸顯現,並最終控制中興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會逐漸失去決策權,並最終失去對朝政的控制。
Advertisement
=
李弘這次總算徹底明白了。
過去張溫、盧植、馬日磾等人在制定中興策略的時候,最擔心的就是學,當時李弘並不清楚它的重要。後來學的事出人意料的順利解決了,李弘當然也就無法進一步去深刻理解。現在,他理解了,但事已經變得非常複雜了,並不是自己支持哪一方就能輕鬆解決此事。
在這件事上,董卓曾經犯了很大的錯誤,最終導致他徹底敗北。董卓聽信了袁隗的話,倚仗手中的武力修改學,設立古文經博士,把古文經學也納了學,結果激怒了今文經學士人,引發了流慘案,繼而各地州郡聯軍討伐董卓,局勢再也不可控制。
學雖然關係到國祚命運,但它是儒士們的事,是學的事,和武人沒有直接關係,武人的介只會讓這場學之爭更加複雜,更加腥,甚至引發局勢的劇烈震。
=
崔琰希得到李弘的支持,但他的話說得非常婉轉,顯然他也擔心武人的介人會導致事一發不可收拾。
李弘聽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欣賞崔琰的謹慎,但現在問題不是武人能不能介的事,而是如何保證朝堂穩定,如何保證中興大業不會到此事的傷害。
李弘考慮再三后,鄭重問道:「那麼,我如何才能幫助你們?」
崔琰不假思索地說道:「大將軍,在此事沒有解決之前,萬萬不能用兵,無論如何都不能用兵。大將軍出外征伐,不僅僅是朝堂失去震懾的事,而是大軍的安全,社稷的安全。糧草輜重全部控制在朝廷手上,一旦朝廷以大軍的安全要挾大將軍,大將軍怎麼辦?一旦個別州郡,朝廷自顧不暇,大將軍又出兵在外,社稷的安全怎麼辦?」
Advertisement
李弘心神震,臉微變。
「我知道西疆的事非常急,但朝堂上的事更加急。事有輕重緩急,請大將軍務必三思。」
李弘微微點頭,又問了一句,「還有嗎?」
「如果大將軍願意,請你約見一次大司農李瑋大人和長公主府長史朱筱嵐大人。」崔琰說完之後,兩眼盯著李弘,眼神極為期待。
李瑋在朝堂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勢力龐大,直接影響中書監的決策,目前雖然他已表明了立場,但事關朝廷穩定,他極有可能頂不住各方力而放棄對崔琰的支持,當然了,如果有李弘的絕對支持,那又另當別論。筱嵐的作用更重要,目前能對長公主的決策產生影響的只有,如果長公主迫於形勢,早早拿出決斷,那麻煩就大了。
在崔琰、郗慮和趙松三人的期待中,李弘終於點了點頭,「我找個機會,到李大人府上去一趟。」
=
當天晚上,李弘書告鮮於輔、徐榮、麴義、張燕、呂布、玉石、良、楊、趙雲、文丑、樊籬、張白騎、張遼、何風等十幾位在京武將,詳細述說了自己的擔憂,告誡他們不要參予「明堂制度」的爭論。在朝堂上,只帶耳朵聽,不許說話,更不許發表任何言論。(按律,大臣們之間沒有特殊況不允許聚會,有什麼事只能以書信來往。)
大將軍約見崔琰三位大臣的事,顯然刺激了朝中的大臣們。朝堂上的爭論日趨激烈。
長公主煩躁不安,屢次派人催請太傅楊彪朝議事,但楊彪百般推辭,就是不去。長公主生氣了,手詔大將軍李弘,你親自去一趟看看。如果他不能走,就把他抬來。
楊彪苦連天,「大將軍,你何必為難我?我去了總要說兩句吧?我說什麼呢?」李弘笑道,「實在不行,你就裝聾作啞吧。」
Advertisement
楊彪駐著拐杖上朝了,他還真能裝聾作啞,人家說東他說西,胡攪蠻纏,最後長公主氣得一揮手,「你回家養病去吧,不要來了。」
=
十月下,局勢的發展有些失控,大臣們在朝議上本末倒置,該議的事不議,整天在明堂制度上爭論不休,接著開始有大臣開始抨擊「新經」了。
率先開始對「新經」發難的就是太僕孔融。孔融是兼學今、古文經學的大家,他引經據典,指出了「新經」很多不足之。接著宗正楊奇也開始了,楊奇是今文經學大家,他的話就難聽了,幾乎把「新經」罵得無完,最後就差沒有說鄭玄沽名釣譽了。
崔琰、郗慮、趙松然大怒,馬上出言反駁。
崔琰三人畢竟小一輩,激之下,言辭上對老一輩頗有些不敬,而且對今、古文經學的某些駁斥明顯措辭不當。這下激怒了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廷尉張邈、祿大夫鍾繇(攻克后,他從兗州返回了朝廷。)、司隸校尉陳宮等大臣,大家一擁而上,齊聲討伐。
崔琰三人抵擋不住,有些手忙腳了。大司農李瑋適時站了出來,接著大鴻臚袁耀、京兆尹趙戩,還有朱穆、田疇、田豫、余鵬、謝明等大臣紛紛出言相駁。
朝堂上混不堪。
=
長公主有些吃不消了,看出局勢發展正在逐漸失控制,隨即督請鄭玄、王剪等大師加快進京速度,並請大司馬大將軍李弘出面斡旋,儘可能先穩住朝堂局勢。
李弘最近因為西疆和益州的事,和一幫將軍們天天在大司馬府軍議,商量對策,並沒有參加朝議。接到長公主的手詔后,他非常吃驚,沒想到局勢發展這麼快,三派經學之間的矛盾轉眼就發了。
Advertisement
馬上就要到年底了,朝廷要做的事太多,如果把時間都耗費在這上面,朝政將被嚴重耽擱。
李弘馬上登門拜訪丞相蔡邕。蔡邕初先對李弘約見崔琰等三位大臣很是生氣,但後來看到北疆武人先是告假走了一批,然後留在朝堂上的人又三緘其口,一言不發,更搞笑的是武威將軍何風竟然在朝堂上睡著了,由此可見李弘還是非常敏銳地察覺到了其中的關鍵,及時退出了這場和北疆武人沒有太大關係的經學之爭,所以他對李弘的態度又大為改觀。
李弘勸說蔡邕,說各州刺史,各郡國太守、國相馬上就要進京上計(各地方向朝廷呈計書,其容為郡國一歲中的租賦、刑獄、選舉等等況),事務繁多,還是把「三雍」的事先放一放,暫時擱置爭議,沒有必要把事態擴大化。
蔡邕嘆了口氣,「我聽說,你又打算出征了?」
李弘笑笑,「是不是子龍告訴你的?他和文姬應該搬出去住,不應該再和你住在一起。」
「我就文姬一個兒,子龍一個婿,如果他們都搬出去了,誰來侍奉我啊?」蔡邕笑著了頜下的白須,「我老了,沒有多年活了,能天天看到他們,聽到孫子們的笑聲,我就很知足了。」
李弘笑著安道:「我看先生至可以活到百歲。」
「算了,你不要安我了。」蔡邕揮手笑道,「當年如果不是你救我,我早死在北寺獄了。這十幾年來,我看到文姬嫁給子龍幸福地活著,看到孫子們環繞膝前、天真可,我已沒什麼奢求了。」
「是嗎?」李弘一語雙關地問道,「先生還有一個最大的期沒有實現,是不是?」
「我看不到了,也許你還能看到。」蔡邕神漸漸嚴肅,「明堂制度的事,牽扯甚廣,估計你也從崔琰大人那裡聽說了前因後果,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說了。這件事我要謝你,大將軍能置於朝堂爭鬥之外,能清醒地看到爭鬥之後的東西,的確不容易。」
「我是朝中之人,就算我想獨善其,恐怕也跑不掉啊。」李弘面帶笑意,意味深長地說道。
「這是當然。」蔡邕說道,「但只要你能看到事的本原,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打算出征西疆。」
「不行。」蔡邕非常堅決地搖搖手,「出征是下下之策。朝堂上馬上就要雨腥風了,你不能離開長安,更不能出征。」
「我只有出征,才能暫時制住朝堂上的矛盾,才能避免這場雨腥風。」李弘著蔡邕蒼老而疲憊的臉龐,一字一句地說道,「年底一到,各州郡大吏雲集京都,事很有可能失控。」
「朝廷沒有財賦。」蔡邕白眉微皺,冷聲說道,「你想打西疆,但打西疆需要多錢?打下西疆后,回遷西疆百姓、安西疆羌族,又要多錢?佔據了西疆,我們要守住西疆,要派駐軍隊,要西遷人口到河湟、河西一帶屯田戍邊,這又要多錢?韓遂在西疆鬥了十幾年,為什麼最後還要冒著全軍覆沒的危險強行攻打關中?」
「子民,冷靜一點。我們打下西疆,佔據西疆,並不等於穩定了西疆,相反,是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要想拿下這個包袱,朝廷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所以打西疆不能急,我們先要做好背上西疆這個沉重包袱的準備,然後再去打西疆。」
李弘暗暗嘆了一口氣。他一直想試探蔡邕的態度,但現在看來,蔡邕心意已覺,朝堂上的這場雨腥風已經不可避免了。
「我能幫你什麼嗎?」李弘沉默很久后,恭敬地問道。
「穩住京都,穩住州郡,穩住軍隊。」蔡邕平靜地說道,「只要軍隊不,州郡不,京都不,就算朝廷了,也影響不了大局。」
=
接下來的幾天,李弘又分別拜訪太尉荀攸、史大夫劉和、太常許劭、宗正楊奇、廷尉張邈、太僕孔融,最後他走進了大司農李瑋的府上。
李瑋和筱嵐夫婦把李弘引進了書房。三人閑聊了一會兒家常。筱嵐說,大將軍回去要好好管一下你家的秀兒,都八歲了,再過四五年就要出嫁了,還象男孩子一樣「瘋」,無法無天。李弘知道秀兒一定又闖禍了,很是尷尬,「出了什麼事?信兒又被打了?」
「昨天右賢王劉冥的兒子劉潭來了,他們幾個孩子相約一起去北郊獵。你家秀兒說獵沒意思,要就人。」筱嵐還沒說完,李弘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李瑋連忙阻止筱嵐,但筱嵐心痛兒子,氣呼呼地數落了幾句。幾個孩子取下箭頭,分兩隊「作戰」。李信不小心中了秀兒,秀兒大怒,衝上去把李信一頓暴揍,把他打得鼻青臉腫地回家了。李信回家還不敢說。正好龐德的兒子龐會在,筱嵐三兩句就把事始末「詐」了出來,筱嵐溺兒子,氣得眼淚都出來了。
李弘連連賠禮,「這樣吧,我收信兒為徒,親自授他武技。下次再遇到這事,信兒最起碼不會吃虧。」
「什麼?」筱嵐急了,「還有下次?你回去警告秀兒,不準打我們家信兒。」
「好,好。」李弘和李瑋相視苦笑。到這種事,兩個男人只好任由筱嵐罵兩聲出口氣了。
這時筱嵐突然反應過來,「大將軍,你剛才說話可要算話,不許反悔。」
「我知道。過幾天,你讓信兒到我府上去住。我既然收他為徒,這孩子就給我了。」
「那不行。」筱嵐馬上搖手道,「不行,不行,你家秀兒會欺負他,絕對不行。」
李弘大笑,「你太溺信兒了。信兒看上去很文弱,其實他格很剛強,如果多加磨鍊,將來肯定能像他外公一樣,出則為將,則為卿。好,好,隨你。不過我如果出征,他可要跟著我,不能再留在家裡了。上次,你應該聽我的話,讓他到戰場上去看一看。」
「霸、趙統、龐會那幾個孩子一個比一個野,信兒跟他們在一起,每次都吃虧。」筱嵐一臉心痛地說道,「信兒如果去了,還不被他們幾個當馬騎?以我看,小天子給你這樣培養,遲早會像你一樣,將來不是頭豹子,也是頭老虎。」
李弘笑道:「當然是頭老虎了。」
=
三個人說笑了一陣,話題漸漸轉到朝政上。
「仲淵,朝堂上的事,越來越不對了。」李弘把拜訪蔡邕、荀攸等幾位大臣的事說了一遍,「我預有什麼事要發生。」
「當然有事要發生。」李瑋笑道,「如果不是我一直給崔琰幾位大人撐著,他們可能已經出事了。」
李弘稍稍沉了一下,轉頭向筱嵐。筱嵐從容一笑,「殿下的態度還是很堅決的,要不然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鄭玄大師儘快趕到長安,但殿下顯然高估了鄭玄大師的影響力。今日無論在朝堂上,還在是經學上,無人可比蔡邕大人的聲和權威。這場論辯,鄭玄大師極有可能敗北。」
「可有對策?」
「如果楊彪大人和許劭大人能助一臂之力,鄭玄大師或有取勝的機會。」
李弘想到楊彪的世故,苦笑搖頭。
「大將軍,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沒什麼可擔心的。」李瑋有竹地說道,「這場論辯的最終目的是打擊「新經」,為他們一下步修改學做準備,但今、古文經學的矛盾深固,反擊的機會比比皆是。現在對於我們來說,關鍵是如何控制局勢,如何以最小代價達到最大目的。」
猜你喜歡
-
連載617 章
大唐醫王
一個現代醫師回到貞觀年間,他能做些什麼?如果他正好還成爲了李淵的兒子,李世民的弟弟呢?李元嘉,大唐醫王。
117.4萬字8 29994 -
完結2629 章

從軍行
「近衛軍團何在,可敢隨我馳騁漠北疆場,馬踏燕戎王帳」 一個身披紅袍的將軍立馬橫刀,「願往」 身前的百戰之卒異口同聲的應答。 一個由小山村走出來的少年,從軍只為給家裡省點賦稅,只想攢錢娶青梅竹馬為妻,隨著軍功不斷,一步步陞官,大權在握之時卻山河破碎,城破國亡。 他登高一呼,起兵抗敵,他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王朝! 他要給自己心愛的女人一個天下!
559.3萬字8.18 54206 -
完結5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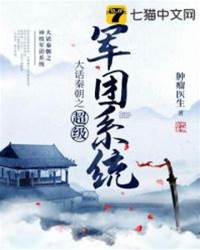
大話秦朝之神級軍團系統
主角蘇辰為了20萬的彩禮,被瘋博士坑,帶著神級軍團系統穿越到了秦末風雲變幻的年代。 始皇是他堂伯,公子扶蘇是他堂哥,他爹是長寧侯,他媽是襄武郡主,而他年紀輕輕就是大將軍蒙恬麾下的副將軍,他是泱泱大秦根正苗紅的「小侯爺。 開局:蘇辰就擁有了200年的功力。 徵召各種頂級兵種,打造秦末天下最強軍團,改寫公子扶蘇的命運,戰匈奴,平天下,征伐六國聯軍,書寫大秦新盛世。 一代神話,秦王蘇辰。
114.3萬字8 7366 -
完結2454 章

開局截胡五虎上將
劉備有五虎將?我直接截胡!劉備有臥龍鳳雛?我的智囊團讓臥龍鳳雛直冒汗!什麼!沒有系統?這,這,這。。。...
431.9萬字8.18 380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