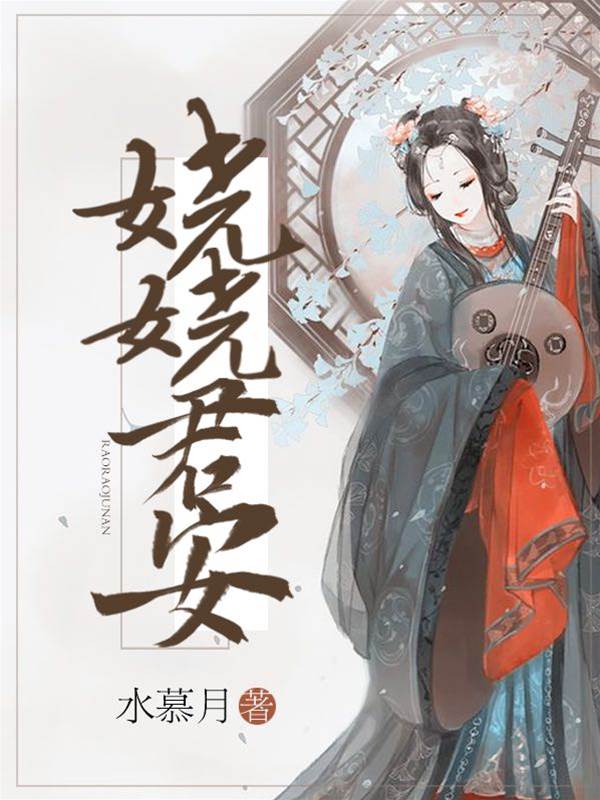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枷鎖》 第106章 第106章
“……從夏朝起,縱觀歷朝歷代,但凡亡國禍哪朝不是先起于禍?不信且看前數幾代明治年間,百姓食有余,家給人足,任誰見了不得道聲是盛世之相?可結果又如?僅劉貴妃一人足矣敗之!”
殿中的閣重臣言辭激烈,語氣萬分痛惜,隨即朝高階座方向抬手,高聲道:“臣自知忠言逆耳,但臣所言句句出自肺腑,字字赤膽忠!臣一片忠輔佐君王,并無半分私,為的是天下能海晏河清,求的是天下能盛世太平!臣對圣上、對朝廷、對天下百姓,竭誠盡節,天地日月無不可為證、為鑒!”
話語鏗鏘有,落地擲地有聲。
林苑將目重新投落在殿中,不輕不重的看那大義凜然的梗骨直臣。
“我看不見得。”聲音清越,依舊是不急不緩的語調,說話的期間面上含著淡笑,“王大人陳詞的確慷慨激昂,可是我卻未從這番激烈的言辭中,到任忠君、為國、民之。”
金鑾殿里有一瞬間的嘩然。
那閣重臣氣怒攻心,恨怒的咬牙切齒。
“娘娘……”
“你可敢聽我道明原委?”
林苑徑自打斷他的話,而后又環視殿中群臣,聲音緩卻清晰道:“諸位可愿聽我細說?”
那閣重臣忍著冷笑,抬抬手道:“臣愿聞其詳,請娘娘不吝賜。”并不覺得這位從來養于苑的娘娘能說出什麼來,想來也不過是要強詞奪理,要給按上個不忠的名聲來,自以為如此就可以折辱他罷。
可笑!這位娘娘怕是忘了,這金鑾殿上可不是那能供興風作浪的后宮,在這廟堂上匯集的可是謀臣武將人中龍,若說不出個確切來,再或是說的顛三倒四,或是淺之極,那可真是要令人貽笑大方了。
Advertisement
其他文武大臣面不顯,如思量不得而知。不過想來,與那位王大人有著同樣想法的人,應是不。
“那就先從忠君說起。”
林苑微偏過臉,隔著繡帷帽對旁人輕笑了笑,似是在安,而后方再次看向殿中,字字清晰道:“恕我見識淺薄,還未聽說過有一上來就將君主打為昏君,恨不得將其釘在恥辱柱上萬世不得翻的忠臣。”
那閣重臣面一變。
卻不開口,接著又道:“的確,你是了我這所謂妖妃的刺激,自覺有了妖妃就會有昏君,有了昏君,那國就會將亡。所以作為忠臣,你就要敢于站出來直言不諱,就算指著圣上的鼻子罵,當眾痛斥圣上的昏庸無道,那又有妨?你是忠臣嘛,行的是正義之舉,縱是被昏君所殺,那也是要流芳百世,青史留名的。”
“臣……”
“我話未說完。”林苑不容置疑的打斷他的話,神發淡:“可是王大人,我想知道的是,將我視作禍國妖妃,你憑的是什麼?空口白牙,上下兩片一,我好端端的一國儲君之母,未來皇后之尊,就要被你釘在妖妃的恥辱柱上,你憑什麼呢?”
“凡事,要將證據的。”
啟淡聲,居高臨下的看著那兀自不平的閣重臣,“就算大理寺斷案,那也要講究人證證俱全,反復確認證據沒有差錯,方能定案。更何況是你要定一國之母的罪,不講證據,如就能輕易下定論?”
“王大人,你說我是妖妃,那我虛求問,為妖妃的我,都做過哪些禍國殃民之?”
“我可有閑著無聊就撕巾帛摔瓷,窮奢極?可有慫恿圣上發明炮烙酷刑,點炊炭,燒銅管,活人?還是可有站在高高城墻上,笑看著圣上烽火戲諸侯?”
Advertisement
“可有讓圣上奢云艷雨?”
“可有讓圣上飲宴爾?”
“又可有讓圣上酒池林、奢糜腐化、荒無度!”
最后一音落下,微微坐直了子,正道:“我都沒有。”
語調并不高揚,卻落地有聲,字字有。
殿中的文武百或站或跪,或垂首沉思,或猶有不忿。
林苑又看向那閣重臣,“我既并未做這些禍國殃民之,王大人卻非要將一國之母按上妖妃之名,這番作為的確不像忠臣所為。況且……”
“縱我是妖妃,那圣上可就是夏桀商紂王之輩?”
這陡然轉過的話題讓本是冷鷙盯視王益的人,猛地轉頭看,高大的軀微微僵。
林苑沒有看,只語氣清厲的直沖殿中之人:“你憑空造罪名加諸我倒也罷了,如敢將昏君暴君這滔天惡名強按君王頭上,簡直是其心可誅!圣上自打繼位以來,赦天下,減賦稅,安天下,定民,躬勤政事,定,使得百姓安居樂業,連婦孺皆知當今賢德之名!你為臣子,不思家國百姓,不思如輔佐圣上開創建元盛世,滿心滿眼只盯著圣上的私德小不放!自以為忠君國,實則沽名釣譽,企圖踩著圣上就你的青史留名,說你其心可誅,是半點沒說錯!”
話音一落,偌大的宮殿闃寂了半瞬。
袞冕加的九五之尊,這一剎那好似周圍所有都離而去,滿目只余怒斥群臣,滿心將維護的模樣。
微抖的手攥住那座龍首。眼圈泛紅的直勾勾看著,頭滾,眸中急遽翻卷的緒不知是激,是震撼,還是不敢置信。
……竟會維護他。
Advertisement
那閣重臣俯大喊冤枉:“臣忠貫日,娘娘卻句句道臣是私,實天大之冤!臣并非妄言圣上昏庸,只是勸諫圣上,自古以來帶后妃上殿是昏君之舉,臣圣上以儆效尤,有不妥?如就了包藏禍心?”
“當然不妥。”林苑冷冷視:“帶后妃上殿就是昏君?誰規定的?你王益王大人嗎?”
那人氣急:“古之……”
“古之圣人規定的可是?你以誰為圣人?天道神仙?還是三皇五帝?”
林苑不假辭:“哦?看來都不是。妄我還當你所說圣人,是哪個能一眼看破天機,一言可定乾坤的神仙。那你所謂的圣人倒也只是個凡胎.罷了。這般的圣人世上多了去了,你將其定的規矩視為珠璣,旁人卻未必視作金科玉律。”
“所以王大人,在繼你將我打做妖妃之后,又將圣上打做了昏君,究竟是憑的什麼?”
那堂下之人膝行朝圣上方向拜了又拜,聲嘶力竭的分辯:“圣上,娘娘曲解臣的意思,臣也辯無可辯!只是自打天地初開那日起,便定了乾坤與,不可顛倒,那是了綱常!牝司晨,惟家之索,這是古之圣訓啊……”
“笑話。”林苑的聲音沁著涼意,“自打我殿來,在爾攻訐我之前,我可言過半個字?我一言不發的坐著,你們卻迫不及待的指我干涉國事,蠱圣上,禍國殃民。該喊冤枉的是我才是!”
“況我與圣上本就是夫妻,夫妻同進同出,該是莊談方是,應更利于國家穩固安寧,如算了綱常?怕是王大人孤陋寡聞,本朝還有地方是專以婦持門戶的。譬如那鄴下,便是如此。”
偏過臉看旁邊人笑道:“看來朝臣常年拘泥京中,見識大多有限,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若有機會,還是得讓人多去其他地方走走,開闊眼界。”
Advertisement
晉滁灼灼看,跳都停了幾許:“皇后所言極是。宣旨,降閣大臣王益為鄴下知州,擇日上任,不得有誤。”
鄴下多為鮮卑族聚集之地,民風彪悍,多不服朝廷管制。那王益一聽,不由眼前一黑,自覺圣上是擺明是送去死來著。
“鄴下民風多樣化,恰適合王大人開拓眼界。”林苑頷首后就再次轉向朝臣,收斂了面上神,淡聲道:“說完了王大人的不忠君,接下來,我再為諸位細數一番他的不為國,不民。”
“為國為民,并非是激昂陳詞,或是指天發誓,百姓就會贊你一句‘為國為民的好’。”
林苑不去看王益那張氣的通紫的臉,繼續道:“也并非是抓著君王的私德不放,不依不饒的給君王扣上大帽,君王認下罪過,你就是為國為民的肱骨忠臣了。家國天下,的確是百姓萬民的天下,可亦是晉家天下。圣上的私,只是不是危害社稷江山,不禍害百姓萬民,那又何必上綱上線,揪著不放?顯得另有居不提,也本末倒置了。”
“正大公無私為國為民者,當思的是國策,當做的是在政事上有所建樹。”
“思己可有攘安之才?思己可有想出利民政策?”
“朝廷政策法令上可有錯之?百姓安居樂業可有攔路之虎?”
“為開創建元盛世出過的?”
“百姓收多寡,寒與否,可能吃飽穿暖?又可有瓦片擋雨遮風?”
的聲音依舊平緩:“思民生,定國策,輔佐君王,此方為憂國憂民的忠臣所思所慮之。”
偌大的金鑾殿,闃寂無音。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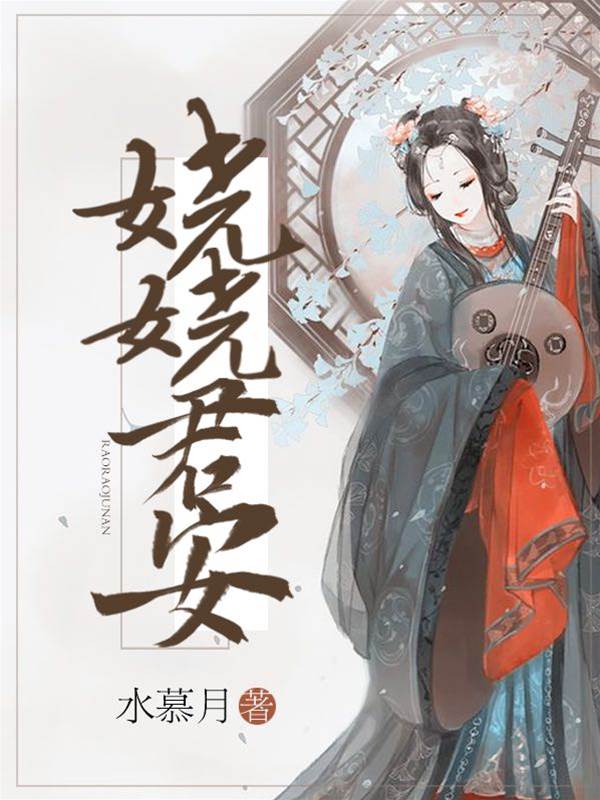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