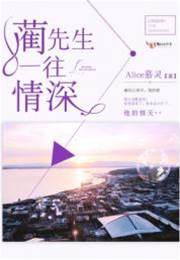《強寵霸愛:長官大人別亂來》 第75章 我願意為你做一輩子飯
周鴻了被砸的生疼的手臂,剛想發火,抬頭對上盛西慕那雙冰冷的墨眸,寒氣瞬間滅了怒火。他扶了下鼻梁上的眼睛,開口道,“不就是對付一個趙家嗎,還需要我親自手,你也真高抬了他趙一牧。”
“按我說的做。”盛西慕惜字如金,聲音一如既往的清冷。他顯然沒有耐心和周鴻浪費口舌。
周鴻無奈聳肩,“我查了一下,趙家現在正做政府的工程,大部分資金都在裏麵,你想截下這個月的工程款倒是不難,隻是,總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那麽大的工程,我就不信質量方麵會沒有一點兒紕。”盛西慕又道。
他的意思,周鴻自然明白。蛋裏麵挑骨頭,這事他在行。“好吧,我這就去辦。”他應了聲,然後起打算離開,同時,手抓住了桌上的酒瓶。“你胃不好,別喝了,為了一個人喝壞了子,不值得。”
“管我的事。”盛西慕清冷的回了句。
如果不是從小玩兒到大的,周鴻現在真想他。“盛西慕,你再這麽繼續喝下去,我隻能認為,你TMD真被尹夏言那妞拿下了。我們這種人,什麽都玩兒的起,就是玩兒不起。你好自為之吧。”
……
尹夏言已經不記得上一次看到海上日出是什麽時候。朝緩緩升起,金黃的點亮了湛藍的海水,好像托起新生的希一樣。夏言微瞇著眸,角約含著笑意。吞吐的氣息中,帶著海洋的鹹味兒。
“很,對嗎?”溫潤的男聲在旁響起。他們背靠背坐在的沙灘上,他溫熱的大掌牽著微涼的小手。
夏言側頭看向他,沒有開口,角卻笑意暖暖。不常笑,但笑起來的時候,眉眼彎彎,臉頰邊顯出淺淺梨渦,得醉人。趙一牧很喜歡看著笑,好似可以忘記世間一切的煩惱憂愁。
Advertisement
夏言站起來,展雙臂,懶懶的抻了個懶腰。“日出看完了,我要去補眠了。一牧哥,飯好了再我。”的語調也是懶洋洋的,帶著幾分撒的味道。
趙一牧無奈失笑後,又故意板起了臉。“做飯可是人的義務,夏言,你別想懶。”
“是嗎?”頑皮的一笑,撒向海邊別墅的方向跑去,“那就等我睡醒了再說,如果我一覺睡到明天早晨,就要委屈一牧哥肚子了。”
“尹夏言,你這個懶人,你別怕。”趙一牧大步去追,兩個人沿著海邊的沙灘追逐打鬧。孩清脆的笑聲如銀鈴般妙聽。
“尹夏言,你嫁給我好不好?我願意為你做一輩子飯。”趙一牧站在距離一丈遠的地方,雙手撐在腮邊,對著茫茫大海,大聲的呼喊。
夏言的笑容逐漸凝固在臉上,隔著不遠的距離,他深的凝著,夏言知道,他在等著的答案,可是,無法回答,更不能說服自己答應。所以,對他傻傻的笑著,裝作什麽都沒有聽見。
“一牧哥,你說什麽?”對他大聲喊道。
趙一牧是何其通的人,自然懂得這是委婉的拒絕。他走上前,再次牽住的小手,“我說,我們該回去了。你穿的這麽,海風涼,別染了風寒。”
兩人手牽著手,一前一後向不遠的別墅走去,卻各懷心事。
他高大筆的背影,在朝的餘暉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孤寂。當他說,要帶著逃離的時候,夏言有過掙紮猶豫,的離開,勢必會讓盛西慕將怒氣發泄在尹家人上。不想在牽連任何人。而趙一牧的一句話,卻徹底的打了。
他說:“夏言,如果盛西慕是一場噩夢,我就是那個將你從夢中喚醒的人。”
Advertisement
然後,他將帶到了郊外海邊的別墅。這棟別墅沒有登記在趙一牧名下,所以,外人想要找來,並不容易。他們的婚禮取消了,但趙一牧對夏言的又怎麽可能一筆勾銷。從那一天起,他就著手謀劃著一切,他們先在別墅中躲一段日子,等風聲過了,他就帶夏言去荷蘭,他在那裏買了一塊地,足可以保證他們下半生食無憂。
他說:“夏言,荷蘭有很漂亮的草原與風車,我們去那裏,做兩個快快樂樂的農民,好不好?”
夏言不說好,也不說不好,隻是眉眼彎彎,笑的很甜。
別墅的客廳鋪著的羊地毯,飄窗上,放著一把棕紅的小提琴。孩白皙的指尖輕輕的翻著琴譜,然後,將小提琴架在消瘦的肩頭,拉琴弦。溫婉的樂聲緩緩流淌而出,一首《之喜悅》充滿喜悅歡樂浪漫的調。
這一刻,難得的寧靜,夏言盡量去忘記那些不堪的過往,忘記盛西慕。可是,真的可以忘記嗎?那些不堪的記憶,就好像一把把利刃,在心口劃開一道道傷口,即使傷口愈合,還是會留下難堪的疤痕。
歡快的音調,不知不覺中,還是染上了淡淡哀愁,夏言墨青披散而下,窗外傾瀉而下,暈開了一室溫暖昏黃。
趙一牧安靜的坐在沙發上,目一直追隨著。眉心,逐漸的蹙起。
他起,來到夏言邊,一隻手從後環上腰肢,另一隻手按住了著的琴弦。
“一牧哥。”夏言抬眸,迎上他深沉的目。扭的在他懷中掙紮。
而他纏在腰間的手臂反而越收越,沒有毫放開的意思。溫潤的男聲在頭頂振響,“夏言,你知不知道你的曲子很憂傷。”
Advertisement
“有嗎?”夏言無奈的笑,將小提琴收琴盒中。還是嶄新的琴,拉奏的時候總有些生的覺。
“夏言,對不起,婚禮那天,不該讓你一個人離開。”趙一牧半擁著,下抵著額頭,低聲呢喃著,聲音中是難以掩飾的沉重與苦。他恨,恨極了無能為力的自己,恨極了有太多牽絆的自己。
“都已經過去了,還提它做什麽。”夏言淡聲回了句。
趙一牧痛苦的閉了雙眼,希一切真的可以過去。“夏言,我們結婚吧。”他的聲音有些微的哽咽。
夏言被他困在懷中的一僵,沉默了片刻,才仰頭迎上他的眼睛。“我了,去做些吃的吧……”
“夏言。”他用了些力氣的咬著的名字,這一次,他不允許再去逃避。“夏言,讓一切都過去,好不好?我們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沒有盛西慕,也沒有趙一豪,就隻有你和我,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夏言凝視著他,眸中璀璨一點一滴的逐漸泯滅,角微微上揚,牽起一抹嘲弄的弧度。“真的可以重新開始嗎!一牧哥,何必自欺欺人。”
“夏言……”趙一牧試圖解釋,而微涼的指尖卻按住了他片。夏言弱弱的搖頭,眸中暗含著點點星。
“和我重新開始,就意味著拋棄你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金錢地位,還有你的父母,一牧哥,你別忘了,他們隻剩下你一個兒子。”夏言的聲音很輕,卻字字句句切中要害。
趙一牧抓住肩膀的手掌突然收,他高大的止不住的抖著,但目卻依舊堅定。“我已經將他們安置妥當。”
夏言苦的一笑,反問道,“真的安置妥當了嗎?那這些天你為什麽要一直關機,甚至不開電視,也不上網。因為你怕,怕看到任何關於趙家的不利消息,你怕那些東西會搖你的決心。”
Advertisement
夏言的話,有些咄咄人,卻是不可改變的事實。趙一牧,到寧願為舍棄一切的地步。可是,無法回報他同等的,更不忍心,讓他背負所有的罪名。趙一豪死了,如果趙家二老再失去一牧,趙家的天就真的要塌下來。
“一牧哥,你說盛西慕是噩夢。其實你錯了,現在的一切,對我來說才是一場夢。一場寧靜而麗的夢,求求你,不要這麽早將我喚醒。”夏言將頭靠在他膛,冰冷的淚珠浸了他心口的衫。
從一開始,夏言就知道,他們是逃不掉的,即便可以不顧尹家的安危,趙一牧也無法擺他必須承擔的責任。他再,也不會為一個人的,他還是趙氏集團的總裁,是他父母的兒子。
趙一牧將擁得更,幾乎嵌自己的脈。如果,不是這麽聰明,如果能學會糊塗一點,他們也不會活的這樣辛苦。“夏言,隻要能和你在一起,哪怕一刻也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17 章

他不溫柔
五年前,陳家父母把陳洛如的姐姐陳漾包裝成名媛推銷給正在美國讀書的孟家太子爺孟見琛。婚禮前夕,陳漾查出有孕,孩子卻不是他的。為避免驚天丑聞,陳洛如被父母奪命連環call回國內為姐姐頂包。陳洛如:“我還要上大學呢,結什麼婚?”陳家父母:“孟見琛已經同意這門婚事了。”陳洛如:“他是魔鬼嗎?” 1、結婚四年,陳洛如和孟見琛猶如陌生人一般,鮮有會面。她和男性友人從倫敦燈紅酒綠的酒吧出來,看到身材頎長的男人站在勞斯萊斯幻影旁。孟見琛手執一柄長傘,左手無名指上套著一枚婚戒。雨珠順著傘檐滑落,他唇線緊抿,眸光深不可測。陳洛如聽見他緩緩開口道:“玩夠了嗎?孟太太。” 2、陳洛如第N次向孟見琛提出離婚,奈何這狗男人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爆。她氣得跑到奢侈品店瘋狂shopping——用他的卡。難能可貴地,孟見琛追了過來:“別鬧,回家。”陳洛如撒嬌道:“你就不會哄哄我?”孟見琛摟上她的腰,軟聲道:“乖,不氣了。跟我回家,嗯?”陳洛如翻臉比翻書還快:“姐夫,別這樣,姐姐還在家等你呢!”全店目光瞬間集中到孟見琛身上。 ****** 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茨威格《斷頭王后》 【作天作地嬌氣包小公舉X見招拆招高冷心機霸總】 閱讀指南: 1)先婚后愛甜寵文,男女主年齡差6歲。女主香港護照,結婚時18歲。 2)男主和姐姐沒有任何瓜葛,男主只愛女主一人。
31.7萬字8 29359 -
完結48 章

自此與你隔光明
夏清寧隻是想安安靜靜的陪在許墨琛的身邊,她真的沒有別的要求了,隻是能和許墨琛在一起就夠了,可是她卻被許墨琛所憎恨著 …
5萬字8 14277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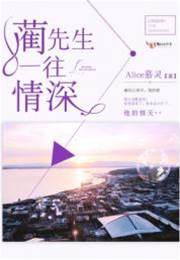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91312 -
完結1021 章

替嫁甜妻:大叔,你要寵壞我了!
初次見麵,她被當成他的“解藥”。 冇想到他對“解藥”上癮,親自上門提親來了。 蘇允諾嚇得瑟瑟發抖:“大叔,你要娶的人是我姐!” 君少卿一把將人摟進懷裡:“乖乖嫁我,命都給你!”
174.6萬字8.18 50762 -
完結489 章

晝夜妄想
他是京圈太子爺,又痞又瘋一身野骨無人能馴,她是寄人籬下小可憐,又乖又慫又清醒,有一天他對她說:“沈漾,幫我追到她,我滿足你一個願望,”可他卻不曾知道,她暗戀他整整七年了!她親眼見證,他為了她最好的閨蜜做盡了瘋狂事!直到那天,他說:“沈漾,她答應我求婚了,有什麼願望你盡管提!”她含淚祝福:“送我出國吧,越遠越好!”從此,她徹底消失在他的世界!後來,人人都以為太子爺會娶他心愛的未婚妻,卻遲遲不見有動靜!再後來,有人無意中撞見,曾經不可一世的太子爺,紅著眼把一小姑娘堵在巷子口,死死拽住小姑娘衣袖:“漾漾,求你跟我說句話...”
91.4萬字8.17 121759 -
完結291 章

有了讀心術后,薄情渣總跪求我回頭
一朝重生回二十三歲,倪楠體會到了什麼叫作自作孽不可活! 白天鞍前馬后伺候婆家人不說,晚上還得提防著自己的枕邊人會不會半夜抽瘋掐自己脖子。 好不容易熬到渣男老公的白月光回來了,倪楠本以為自己就此解放,誰知道對方壓根不走前世劇情,甚至連夜壓到她把歌唱。 第二天,倪楠揉著老腰,簡直欲哭無淚: 蒼天啊! 那些年走過的歪路終究是躲不過了!
56.5萬字5 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