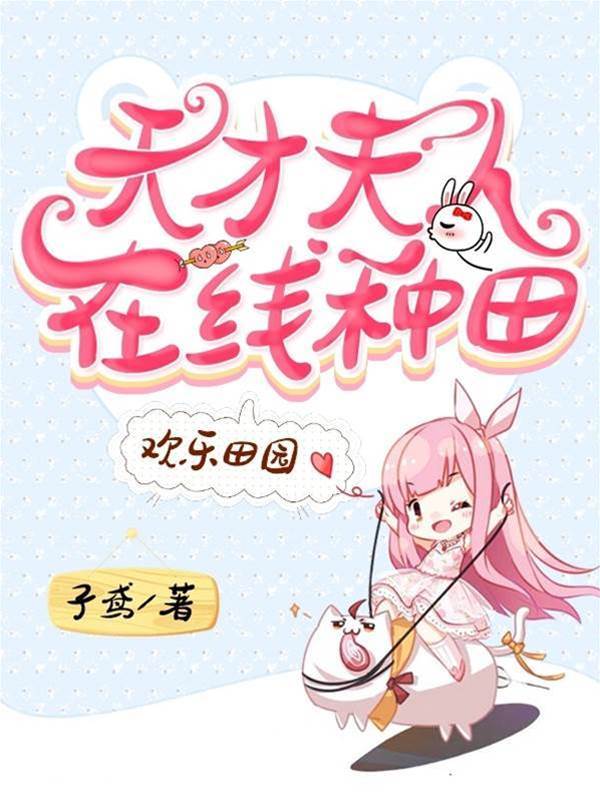《邊關小廚娘》 第80章 第 80 章(捉蟲)
熬了酸蘿卜老鴨湯, 姜言意借著去封府看辣椒的名頭,用食盒給封朔裝了一盅送去,鴨脖也特意用碟子裝了些拿過去。
出門時, 楚言歸喊了聲:“阿姐要去王府嗎?”
“我過去看看種的番椒,那院子也是王府租給咱們的,理當送個禮。”姜言意上這麼說著, 心中卻有些發虛。
楚言歸乖巧笑笑, 出兩個小酒窩:“這是應該的, 那阿姐早些回來, 我讓姚師傅等你一塊用飯。”
姜言意道:“我還得去番椒地打理一番,萬一回來晚了, 豈不是耽擱姚師傅和老先生他們回去, 飯好了你們就先吃。”
姜言意掀開竹簾出門,外邊大雪如絮, 竹簾輕輕搖晃,披著湖青織錦斗篷的影走遠了,楚言歸卻沒收回目。
楚忠來給炭盆子里添炭時, 他神有些鶩地道:“忠叔,我怕阿姐人欺負。”
楚忠年過三十,是跟在楚昌平邊的老人了, 見識的人世故也多,表爺自從喪母, 就一直不太穩定,表小姐在的時候他乖乖巧巧, 表小姐不在的時候,他就像一頭對誰都兇惡齜著牙的小狼崽子。
楚忠安他:“爺,小姐是個有本事的, 沒人能為難到,真要遇上什麼,三爺也不會袖手旁觀。”
楚言歸卻道:“阿姐再厲害再有本事,我也擔心。”
阿姐請來給他看傷的王府郎中,離開楚家那日的馬車,王府租給他們的院子……樁樁件件,都讓他不安,若是遼南王以這些做脅,欺負他阿姐,他阿姐只是死撐著不說怎麼辦?
楚家尚且只是在遼南王的庇護下才得以逃到這邊陲之地安,真要發生個什麼,遼南王府權勢滔天,他拿什麼去給他阿姐討回公道?
Advertisement
“喵!”
在炭盆子旁烤火的小胖橘突然厲一聲,一下子蹦出老遠,背部一團卷曲了起來,小胖橘努力扭過頭去被烤焦的那一團,聲像是嗚咽一般,細弱可憐。
楚言歸被貓聲拉回神智,掩下了心中的惶然,躬抱起小胖橘,“你又在炭盆子旁睡著了?”
胖橘在他懷里,揚起腦袋沖他了兩聲,像是委屈,又像是在責怪他沒把自己照顧好。
它就睡個覺的功夫,怎麼就被烤焦了一大團!
楚言歸小胖橘的腦袋:“下次別睡炭盆子旁了。”
小胖橘生氣甩了甩腦袋,不給。
楚言歸角彎起,再次把掌心罩在了胖橘腦袋上,胖橘整只貓臉都被他的手給蓋住了,只能不滿嚷幾聲。
門口的竹簾又一次被打起,幾個年輕公子哥有說有笑進店來,上都穿著服,顯然是府衙的人。
楚言歸抬起頭,看見最后面那文質彬彬的公子哥,倏地冷了臉。
“陸兄,回回邀你來這姜記古董羹你都百般推不肯來,怎麼著,這里的布置不比那些大酒樓差?”跟陸臨遠并肩的年輕公子邊說邊笑:“這店里的掌柜生得可一副好相貌,真跟那仕圖上走下來的人兒一般!你不曉得,盧員外家的小兒子為了看這掌柜,連著來吃了一個月的鍋子,也是個風流種了……”
“楊兄,慎言,兒家的名聲,萬不可這般玩笑。”陸臨遠攏著眉心道,他不管形還是容貌,在幾人中都是最出彩的,遠遠去,當真是蘭枝玉樹之姿。
陸臨遠是被幾位同僚拽過來,他百般推過,到底是沒推,他本擔心見到姜言意,但無意往柜臺一瞥,瞧見坐在那里的是楚言歸時,對上楚言歸滿是憎惡的眼神,他下意識別開了視線。
Advertisement
楚家舉家遷至西州的事,他早有耳聞,只是沒料到會在這里見楚言歸。
從前他一直都是厭惡姜言意姐弟的,這對姐弟愚蠢又傲慢,姜言意恬不知恥,跟蒼蠅一樣一直往他跟前湊,逮到機會就欺負言惜。楚言歸則是幫兇,他姐姐做的惡事里,都有一份他的功勞。
他對這對姐弟的厭惡,源于對姜言惜的喜歡。
如今或許是心境發生了變化,他們傷害姜言惜,應得的懲罰已經得到了,甚至遠遠超出了他們應的,他的厭惡也就此終止。說把們當陌生人看待,似乎又比對陌生人多了那麼一層東西在里邊,畢竟曾經有過太多牽扯。
陸臨遠這些日子想了許多,他退婚時尚且年氣盛,只一味地覺得這婚事是姜言意自己強求的,他為了姜言惜跟退婚,是姜言意自食惡果。后來楚昌平的那些話,終于撕掉了他那層理所當然的遮布——他若是從一開始就跟母親反抗到底,就不會有這樁婚事。
綜其原由,是他自己當時太懦弱,才促了這樁婚事,他并非全然無辜。
他們姐弟欠姜言惜的,一個被送去做營,一個被打斷了,算是都還清了。
但他悔婚欠姜言意的,還從未還過。
同僚們點了羊湯鍋,要了店里新買的梅花釀,從南邊的戰談到風月之事,觥籌錯,且言且笑,陸臨遠自始至終都不發一言,行酒令好幾次都行到他這里結束,幾杯薄酒下肚,他心緒更煩了些。
好不容易了,都是同僚,他費了些力氣才在府衙站穩腳跟,自然不能在酒桌上同他們惡,離開前便去柜臺提前結了飯錢。
楚言歸雖然憎惡陸臨遠,但想到阿姐店里的生意,不愿鬧太僵趕客,面無表說了結賬的銀子:“四兩七錢。”
Advertisement
陸臨遠給了五兩,緩聲道:“不必找了。”
言罷就披上斗篷離去。
楚言歸從屜里取出三錢就砸向了陸臨遠后背,冷笑道:“客,找您的錢,收好了!”
幾串銅板砸在陸臨遠披風上,又掉進了雪地里。
陸臨遠背對楚言歸站著沒作聲,他邊的小廝是到了西州后才買的,不知兩家的關系,被氣得不輕,怒道:“怎麼做事的,有你這麼找錢的麼?當心我告訴你們掌柜的去!”
陸臨遠道:“青松,走了。”
小廝瞪了楚言歸一眼,撿起落在地上的銅板,追上去陸臨遠,還能聽見他嘀咕:“大人,也就您脾好……”
楚言歸哂笑道:“你家大人脾自是好的,六禮都到了請期這一步才悔婚,從未想過被他悔婚的姑娘會為怎樣的笑柄。”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基本過了納征送聘這一步,就沒有悔婚的。大宣朝的風俗,子若是這時候被退親,都是公認德行不佳、不守婦道,結親的兩家人怕是得從此變仇家。
小廝心頭一個激靈,反應過來自家大人怕是跟這小郎君家中有什麼過節,沒敢再吱聲。
***
封府。
姜言意把湯拿過去時,還是燙的,給封朔盛了一小碗,催促他趁熱喝:“今日從面坊回來買了幾只鴨子,用酸蘿卜燉了湯,這湯清熱涼的,你嘗嘗。”
封朔沒去接手上的碗,反而一把攬住了腰往下一拉,姜言意被迫坐到了他上。
手上還端著碗,不由得驚呼一聲:“你作甚?”
封朔垂首嗅了嗅發間的清香,把下輕輕擱在肩膀:“抱你啊。”
只一句話,姜言意心就了下去。
Advertisement
自那日出城后,他們確實很長一段時間沒見了。
姜言意靠在他懷里,絮絮叨叨把自己近日的事說給他聽:“我盤下了一個面坊,以后打算賣面食。”
沒有說準備把方子給軍營的事,李廚子負責管理火頭營,沒有誰比他更清楚軍中適合什麼樣的伙食,比起蕎面餅子,方便面的制作本的確是高不。事到底不,等李廚子那邊答復就是了。
若是給封朔說了,便是軍中可能本就不用的方便面制造方子,封朔也會讓底下的人高價買走方子。
封朔抬了抬眼皮:“銀子夠嗎?”
姜言意道:“夠,面坊死了老東家,東家是個不的,欠了賭坊銀子,急著還錢,便折價轉賣與我了。”
側過臉去看他:“怎麼,你想借錢給我?”
封朔雙臂收攏了些,嚴嚴實實把人箍在自己懷里:“先借給你,趕在你還銀子前把你娶了,你就不用還了。”
姜言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你替我考慮得倒是周到。”
封朔似乎是想看的笑,他微微揚起頭,下無意間到姜言意脖頸。
姜言意輕呼一聲,整個人都瑟了一下,電般用手捂住了脖子。
下顎到的那一片細膩溫潤得人心驚,封朔頭了,眸暗了幾分,他啞聲問:“脖子怎麼了?”
姜言意看他一眼,似乎有點難以啟齒,“沒什麼。”
封朔不依不饒,眼底仿佛碎了星辰般,嗓音在這一刻低醇得人,“那你捂脖子作甚?”
被他這般追問,姜言意糾結了一下,還是說出了實話:“被你下上的胡茬扎到了,有點疼。”
封朔:“……”
曖.昧的氣氛瞬間無影無蹤。
他不聲抬起手手了自己下,今早沒有修面,短短的胡茬冒了出來,是有點扎手。
姜言意輕咳一聲,用湯匙拌了拌碗里的湯:“再不喝湯得涼了。”
封朔還是沒有手去接碗,只看了姜言意一眼。
姜言意痛恨自己竟懂了他那個眼神,想著好歹是自己看上的狗男人,寵一下就寵一下,舀起一勺湯喂給封朔,封朔張心滿意足喝下。
湯放了這一會兒,已經不燙了,口溫熱,不僅有鴨的鮮香,還有蘿卜的酸味,催生了不食。
他點頭:“湯不錯。”
隨即接過姜言意手中的碗,舀起一勺要喂給姜言意。
姜言意恥棚,皮疙瘩起了一:“你喝,你喝就行了,我在店里時就喝過了。”
封朔沒有放棄的意思,只得著頭皮喝了一口。
封朔看著一臉視死如歸的表,把湯碗放到一旁的書案上,單手按住姜言意后背,讓被迫趴在了自己懷里,另一只手刮了刮鼻頭:“你個不知好歹的,嫌棄什麼?這天底下除了母妃,還沒人喝過本王喂的湯。”
不知好歹的某人只能訕訕一笑:“我這是寵若驚。”
姜言意難得過來一次,封朔好不容易恢復了十的味覺,自是把老鴨湯和鴨脖都吃了個。
飯后他道:“我幫你找了個教書先生。”
姜言意想起自己先前跟他說起過要給姜言歸請夫子的事,沒想到他竟上了心,心下一暖,問道:“是哪位夫子?我明日就親自去府上拜訪。”
西州臨近關外,儒人仕子得可憐,有幾分真才學的,都被達貴人請去當西席了,剩下些半吊子的,姜言意又不敢用。
封朔道:“那天不是帶你去拜訪了麼?”
姜言意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封朔說的是梅林賣酒的老叟。
“那老東西雖然有幾年沒教過人了,但以前學識還不錯,好歹曾是三公之一,教你弟弟應是夠的。”
封朔語氣閑散,姜言意卻是驚得不知道說什麼。
位列三公,狀元郎想去當學生怕是人家都不愿收,哪怕楚言歸是自己弟弟,但他那點學識,姜言意心中還是有數。
原本只是想讓楚言歸讀書明理,心境開闊些,將來不走死胡同就是了,哪知道封朔暗請了這麼厲害的人。
遲疑道:“言歸以前讀書不上心,我怕他不得老先生的眼。”
這樣學富五車的老者教楚言歸,姜言意更多的是惶恐,怕楚言歸在讀書上挫更加自暴自棄,又怕浪費了老叟那樣的師資。
封朔道:“放心,那老東西挑剔著呢,是塊朽木他才不會給自己找麻煩。他已經去你店里看過人了,親口應了要教的,只不過前期得讓池青先帶帶,今后言歸跟池青就算同門師兄弟了,先也好。”
且不論楚言歸最終會學什麼樣子,單是有池青師弟這樣一個份在里面,將來他若是做幕僚,就沒人敢輕視他。
姜言意看著封朔:“所以那日帶我出城,本不是你一時興起,而是一早就準備好的?”
封朔看著泛紅的眼眶,大掌上臉頰:“哭什麼,我做這一切又不是沒所圖。”
他圖。
自始至終都是。
***
陸臨遠回到家中時,已經掌燈了。
那幾杯梅花釀初下肚不覺有什麼,在風雪中走這一陣,酒勁兒才慢慢上來,他白皙的面頰上染上坨紅。
紗窗映著燭火,可以瞧見里面有道倩影正忙碌著。
小廝見狀沒跟進去,知趣地去廚房窩著烤火了。
陸臨遠推門進去,姜言惜正在擺弄桌上的飯菜,見了他,立刻出笑,“陸哥哥,你回來了。”
屋外寒風肆,大雪枝,穿著一鵝黃的襖站在燈下,好似一朵開在寒夜的淡黃小花,弱卻又堅韌。
姜言惜的容貌初看并不人覺得驚艷,可一旦記住了的模樣,就再也忘不掉,尤其是那雙眼睛,好似山野間的小鹿,靈而澄澈。
上前接過陸臨遠解下的披風,掛到了墻上。
聞到陸臨遠上的酒氣,姜言惜眼神微黯,但面上還是掛著笑問:“陸哥哥今日怎回來得這般晚?飯菜我都熱了好幾次。”
喝酒吹了冷風,到了屋暖和起來,陸臨遠才覺著頭一陣陣的疼,他道:“對不住,言惜。今日推不得,跟幾個同僚小飲了幾杯。往后我若是沒回來,你就先吃,不必等我。”
姜言惜聽到他這話怔了一下,依然笑著,眼底卻有了些許凄苦:“我這一輩子,都在等陸哥哥,不是嗎?小時候等著長大了嫁你。宮后,等著有朝一日你帶我走……”
那滴淚終究是墜了下來,姜言惜抹了一把眼,繼續笑道:“說這些做什麼,我做了陸哥哥最的東坡,快吃。”
陸臨遠見這般,心痛之余,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姜言意來,到了西州之后,同樣是絕境,但姜言意從不等任何人來幫,甚至也不愿依靠旁人,似乎寧愿做一棵被人踩進泥里也還能再長出的野草,也不愿做攀附的藤蔓。
他看著姜言惜,嘆息道:“言惜,你不必為我這般。”
前世而不得的人如今就站在自己跟前,他該歡喜才是,可是看到似乎只為了自己而活,陸臨遠歡喜不起來。
這輩子他還有好多事要做,他若萬一有個好歹,姜言惜這樣該怎麼活下去?
姜言惜背對陸臨遠站著,握著筷子的一雙手得死,眼淚跟斷了線的珠子一樣直往下掉:“陸哥哥不喜歡的,我都改掉就是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223 章

田園嬌寵:神醫醜媳山裡漢
穿越到古代,她成了又黑又醜,全身肥肉,被妹妹和未婚夫背叛,最後隻能嫁到農家的鄉野村婦,潑辣無理,懶惰成性,臭名昭著。 冇事,她好歹來自二十一世紀。被背叛?她讓渣男後悔!名聲不好?她用事實堵住他們的嘴!妯娌不喜歡她?她送她們見鬼!長得醜?她可以慢慢變美…… 不過她隻想種種田,養養娃兒賺賺錢,哪裡想到,她那個山裡漢夫君竟然一步步青雲直上,成了權傾朝野的大人物…… (本文架空,請勿考據。本文架空,請勿考據。本文架空,請勿考據!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382.4萬字8 213064 -
完結991 章

學霸娘子在農家
飛機失事,一睜眼,她從一個醫科大學的學霸變成了古代小山村的胖丫頭,還嫁給了一個兇巴巴的獵戶。又兇又狠的獵戶是罪臣之後,家徒四壁,窮得叮噹響,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包子,吃了上頓冇下頓,暴富是不可能暴富的了。母親和妹妹把她當成掃把星,眼中釘,又醜又胖,怎麼還死皮賴臉的活著!阿福心態崩了啊,算了,養家大業她來,醫學博士是白當的嗎,一手醫術出神入化,救死扶傷,成了遠近聞名的神醫。眼看日子越來越好
121.4萬字8 78577 -
完結580 章

醫品福運農家女
外科醫生重生為農家小女,家有爹疼娘愛爺奶寵,哥哥們也競相寵她,哥哥們已經夠多,怎半道還撿來一個? 農家小女隻願歲月靜好,家人安康。奈何天不遂願,一場突如其來的冤情,打破了農家的歲月靜好。 流亡逃串中做回大夫,無雙的醫技讓京中權貴趨之若鶩……還有,半道撿來的哥哥咋回事?咋成了太子爺唯一的兒子呢?
141.4萬字8 60134 -
完結435 章

農門甜寵:我家夫人很威武
季婉柔書穿了,為了活命,百般示好男主,可男主似乎不領情,倒是男主的哥哥卻變得異常的和藹可親,心想著只要遠離男主,她就能過上混吃等死的生活,不成想,男主他哥竟然看上了她,這可咋整?
39.2萬字8 17531 -
完結3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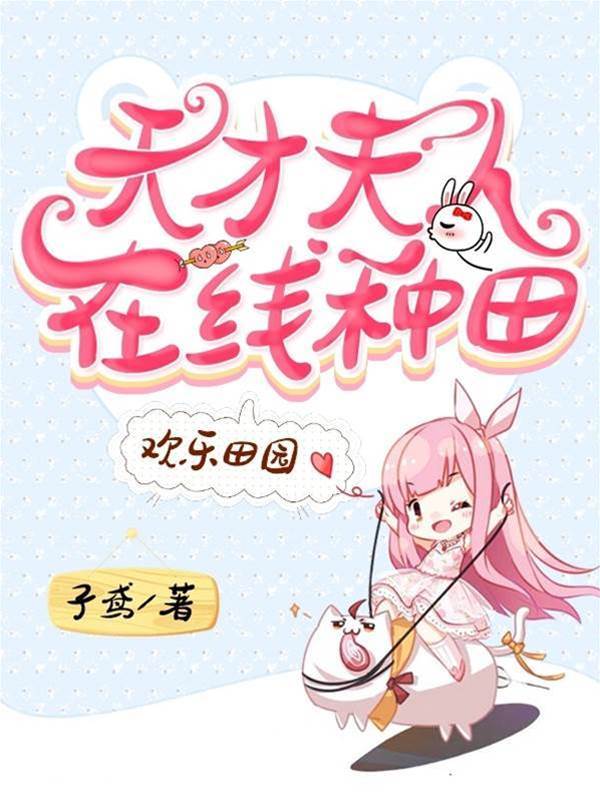
歡樂田園:天才夫人在線種田
研究出無數高科技產品的云若終于熬到退休了,只想從此在農村種田養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淡云流水了此一生。 可偏偏有人不長眼,要打擾她閑云野鶴的悠閑生活,逼她開啟打臉模式。 文盲?賠錢貨?網絡白癡?粗俗鄙陋的鄉巴佬?還想逼她嫁殘廢? 所謂家人對她的嫌棄猶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直到…… 世界頂級財團在線求合作,只要專利肯出手,價錢隨便開。 世界著名教授彈幕叫老師,只要肯回歸,他給當助手。 全球超級黑客直播哭訴求放過,以后再也不敢挑釁女王大人的威嚴。 十五歲全球最高學府圣威諾大學畢業,二十歲幾十項頂尖科技專利在手,二十一歲第十次蟬聯黑客大賽冠軍寶座,二十二歲成為最神秘股神,二十三歲自創公司全球市值第一…… 二十四歲,她只想退休……
62.5萬字8 15604 -
完結491 章

抄家流放后:全家一起去逃荒
(穿越空間種田團寵夫君嬌寵)蘇暮煙:「啥?」 夢到自己穿越逃荒了?還有空間和美夫君?這一下子就讓母胎單身的的蘇暮煙激動了起來! 蘇暮煙:「這活兒我熟啊」 憑藉著十多年的書蟲經驗,穿過去了指定是逃荒路上的富貴人家嘞! 不過這好像要是真穿去逃荒的話,那不得買買買! 屯屯屯啊?後來啊,蘇暮煙帶著弟弟妹妹和命不久矣的沈胤,成為了逃荒路上條件最富裕的人。 只不過這個高冷夫君,好像不太待見自己是怎麼回事?不過後來蘇暮煙表示這都不是事,現在有事的是自己要怎麼生一個足球隊出來嘞?「愁啊」
90.8萬字8.18 515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