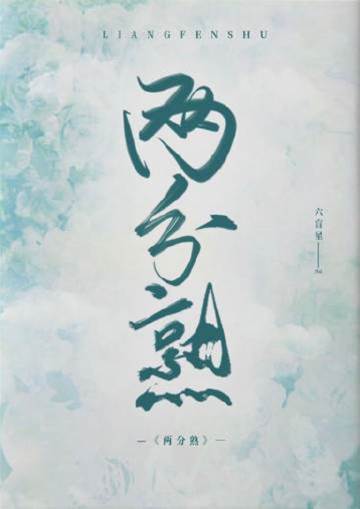《婚色幾許:陸先生入戲太深》 第122章 江偌年紀小,在家又被我慣出了脾氣
江舟蔓不開口,因為江偌說得每個字,都是剛才從裡冒出來的,那麼多隻耳朵都聽著,並且能心領神會其中涵義,若是要否認,敢做不敢當,反而被人瞧不起。
僵站在那裡,覺腳下有熊熊燃燒的火焰在將炙烤。
只聽江偌又問:「陸淮深,是這樣嗎?」
聲音很輕,在無人吭聲的客廳響起,仍是極為清晰。
曹文茉瞄了眼陸淮深看不出喜怒的表,拿不準他是怎麼想的,上次在陸家,他明顯是幫著江舟蔓在說話,他目前又已經開始理江氏份,應該是離婚分財產沒跑了。
這麼一想,相當於給自己吃了顆定心丸,也不管江舟蔓真跟陸淮深了事,對自己有什麼壞,只想著今天非要讓江偌吃不了兜著走才解恨。
壯著膽子接腔說:「當然沒錯!他和江小姐早就有結婚意向,本來連我們家老爺子都同意了這門婚事,你橫一腳,可不是害得人家而不得?」
陸葦雲真是不忍直視,曹文茉越來越像個白癡!
江偌朝輕笑:「看來三嬸也是迫不及待讓江偌嫁進江家了,所以今天才刻意把人帶來給大家混混眼緣。」
陸淮深面無表地看向曹文茉:「你把江舟蔓來的?」
曹文茉有點兒搞不清狀況。
這語氣,其實在座的都有點分不清了,他究竟是在怪曹文茉將江舟蔓卷進來呢,還是怪讓江偌不高興了呢?
還是季瀾芷最先反應過來,若是維護江舟蔓,可不會這麼連名帶姓的。
忽而抿著笑了下,暗自搖了搖頭,置事外一般緩緩將面前酒杯里的酒飲盡。
這個家,這些人,和江偌一樣,對此到厭倦。
這個家裡,沒有人願意剝開現象看本質,因為們只需要停留表面的鮮,不打破這延續多年的平衡。
Advertisement
曹文茉後知後覺說:「是我啊……」
笑了下,可依然沒人,空氣彷彿凝滯,將的笑襯托得突兀而稽。
看了眼各人,收起笑正道:「上次在家宴上,跟江小姐聊得不錯,請吃飯有什麼問題嗎?」
陸淮深問:「今天你做東?」
陸淮深的眼神讓曹文茉相當不安,可又彷彿被吸住一般,越心虛越恐懼,反而讓越加不敢躲避。
陸淮深一白襯衫黑西,髮型也不像時下流行的年輕男人會剪的樣式,永遠都是一頭乾淨利爽的短髮,不加修飾的額頭,加上劍眉深目,分明稜角,英氣剛中更帶著撲面而來的凌厲氣息。
面無表又寡言的時候,那眼神淡淡一瞥都讓人而生畏。
曹文茉用了很大力氣才在他的視線力中轉開臉去,理所應當地說:「你二嬸做東,可我帶個客人來有什麼關係?」
「你想帶個客人來沒關係,」陸淮深走近,居高臨下盯著曹文茉,「可你明知江偌在場,還故意找來我的前友,這就有關係了。」
在座的人為之大震。
曹文茉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看著陸淮深,嚨想要說話,目無意間掠過江舟蔓淚水瀰漫的雙眼,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也許之前還有人猜測陸淮深準備跟江偌離婚娶江舟蔓,但僅僅是『前友』三個字就足以說明一切。
三個字反轉局面,擺明態度。
陸葦雲嘆了口氣,勸陸淮深:「你三嬸說話做事都不巧妙,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人什麼樣,別跟計較了。」
季瀾芷不知何時已經挪了位置,跟陸星葉坐在一起,剛好江偌旁邊的位置就空了下來,陸淮深坐下,手抓住江偌在空調房裡待久後有些微涼的手。
Advertisement
江偌的手一直藏在桌下放在上,指甲的嵌進了手心,陸淮深的手過來的瞬間,將拳頭鬆開,順從地被他握住。
「別用計較這兩個字,顯得我們小氣,」陸淮深往椅子上一靠,看向江偌:「這事追究還是不追究?」
陸淮深手中源源不斷的暖意滲到江偌的手上,傳遞進骨子裡。
那作並不晦,所有人都看到了。
江舟蔓就站在江偌旁邊,看得更加清楚,還看著陸淮深的拇指毫無章法地,輕輕挲著江偌的手背。
他用『前友』三個字,踢走的臺階,用這個親昵作,漠視了的存在。
他甚至不多問一句前因後果,就選擇站在江偌後。
江偌現在心裡怎麼想的呢,是否像曾經那樣甜又竊喜?
你的昨天,我的今天。
你也不要太高興,你的今天,又是誰的明天呢?
曹文茉此時肺都要氣炸了,陸淮深他什麼意思?江偌要是說一句追究,他難道還要拿怎麼辦不?
而江偌並不多言,只垂著頭低聲說:「不用。」
陸淮深掀起眼皮盯著曹文茉,涼聲笑道:「三嬸,不看僧面看佛面,江偌年紀小,在家又被我慣出了脾氣,在外面尤其不得委屈,你以後有什麼火氣,沖我發。」
此話一出,江舟蔓一分一秒也待不下去,自嘲一笑:「看來是我這個壞人讓江偌委屈了,是我來錯了地方,打擾各位了。」
陸淮深始終還是給江舟蔓留了個面子,沒有為了維護江偌而說的任何不是。
可對於江舟蔓來說,徹底的無視,造的傷害更深刻徹底。
江舟蔓拎著包快步離去,一頭闖夜中,仗著有了黑暗的庇佑,眼淚便肆無忌憚。
外面起了大風,江舟蔓開門時只開了一小半,手鬆開,門啪的重重合上。
Advertisement
聲音在偌大的客廳里回。
二嬸見風使舵說:「三弟妹也真是的,太不懂事了,以後可要多注意了。」
牆倒眾人推,曹文茉肚子里的火正燒著呢,哪會自己吞下這口氣,立刻冷笑著揭穿:「你剛才添油加醋不是得勁的嗎?」
「胡說!」二嬸想要撇清關係。
陸淮深冷聲打斷:「以後這種飯局別找江偌了,工作忙,不像你們一天到晚閑得沒事,沒時間也沒工夫應付你們,有問題找我,想約也先找我。」
說完,跟姑姑陸葦雲招呼了一聲便拉著江偌一起離開了。
這時季瀾芷已經喝了不酒了,撐著腦袋那陣眩暈,人有些飄飄然,彷彿所有煩惱的事全都離遠去。
雙頰微紅,加深了腮紅的,又呵呵的笑著,襯得保養極好的一張臉愈加年輕起來。
出食指,朝桌上幾個人點了點,隨後自己笑著搖搖頭,「想看別人笑話的人,卻被別人看了笑話。你們的生活就是無趣,就是閑,才一天天尋思著怎麼給別人找麻煩。」
佩服江偌跟這些人撕破臉的勇氣,忍無可忍無需再忍,回想那場面仍然覺得意猶未盡。
江偌算不算是熬出頭了呢?至陸淮深心中的天平已經傾向。
而,要將心離,慢慢地、麻木地,度過這漫漫長的餘生。
這話像破風的箭矢,擊中了某些人的痛點,滿心的憤怒與不悅,見季瀾芷全然一副喝醉的模樣,醉人醉語,也不同計較,權當是最近日子不好過,喝醉發泄。
季瀾芷長嘆后說:「玩夠了嗎?玩夠我就走了哦。」
說完,俏地笑笑,拎起自己那隻同差不多的馬仕鉑金包,搖搖曳曳地走了,十足像個放飛自我聲犬馬的貴婦人。
Advertisement
開門那一刻,腳步依然虛浮,笑著笑著就哭出來了,癟著沖夜喃喃:「陸清時,你讓我下輩子都要像們一樣過了……」
是第三個從這個房子里走出來的傷心人。
……
江偌剛出來后就將手從陸淮深手心裡掙出來。
陸淮深沒設防,被掙開,他看向,江偌已經目不斜視往他停車的地方走去。
陸淮深停在原地幾秒,隨後隔著幾步的距離,跟在後,將車門解鎖,江偌拉開車門坐進去。
陸淮深上了車,關上車門的剎那,外界都被隔絕,車裡安安靜靜。
江偌靠著車座,目一瞬不瞬盯著窗外路邊的綠化,那樹冠茂盛遮天,裡面矮植叢生,一片黑暗。
開口說:「麻煩你送我回錦上南苑。」
陸淮深系安全帶的手頓住,盯著的側臉,白膩和廓,每次看都能讓他有不一樣的覺,比如現在的覺是鬱悶惱火。
客氣得跟他是計程車司機似的,下車會給車費那種。
陸淮深沒吭聲,那瞳仁黝黑,目沉得跟夜幾乎就要融為一,他抿著啟車子。
陸二叔家在的這一片區不悉,但是陸淮深開下高架,又拐進了一條三車道,江偌抬頭,看見了昏黃路燈下的指示牌,那是去城東的。
控制不住,開口就是寡淡的聲音:「陸淮深,可以送我回錦上南苑嗎?」
陸淮深冷嗤:「你要不再說個『請』字?」
江偌照做:「陸淮深,請你送我回錦上南苑。」
陸淮深咬牙,腮幫發,使勁掄了把方向盤,將車停靠在旁邊的公站臺前。
猜你喜歡
-
完結762 章

左少的深情秘妻
所有人都知道,許愿愛左占愛得死去活來。所有人都知道,左占不愛許愿,卻深愛另一個女人。直到幾年后,失蹤的許愿高調歸來。左占:許愿,我們還沒離婚,你是我的妻子。許愿笑得嬌媚:左先生,你是不是忘記,當年我們結婚領的是假證了?…
151.2萬字8.18 60403 -
完結183 章

強取豪奪:惹上狂野前夫
她本是豪門千金,卻因為愛上仇人的兒子,萬劫不復。他注定一代梟雄,竟放不下她糾纏不清。離婚之后,他設計讓她生下自己的骨肉,再威逼利用,讓她不許離開“安喬心,記住,不許離開!
50.1萬字8 3120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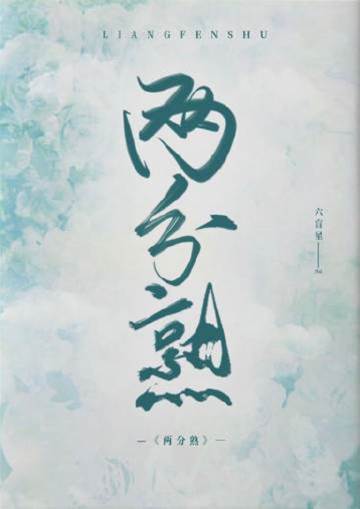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610 章

團寵小可愛:大叔,好好寵我
【馬甲+玄學+女強男強+團寵+娛樂圈】對女人過敏的大佬撿回來個女孩后將人寵翻天! “大叔,我喜歡這顆最大的全美方戒。” “全球鉆石礦脈都是你的。” “總裁,夫人把頂流女明星的下巴假體打斷了。” “她手疼不疼?還不多派幾個人幫她!” 墨冷淵:“我夫人是鄉下來的,誰都別欺負她。” 可眾人一層層扒小姑娘的馬甲,發現她是玄門大佬,拳皇,醫學泰斗,三金影后,…… 眾人瑟瑟發抖:這誰敢惹?
89.6萬字8.18 33866 -
完結211 章

夫人快復婚吧,總裁膝蓋跪爛了
五年愛戀,一年婚姻,她用盡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換不來他的另眼相看。后來她決定放過自己,選擇離婚。 回到豪門繼承家業。 白月光上門挑釁,她冷漠回擊。 將她和那個狗男人一起送上熱搜。 宋司珩這時才發現,那個只會在自己面前伏低做小的女人。 不僅是秦氏的大小姐,聞名世界的秦氏安保系統出自她手,世界頂級珠寶品牌的設計出自她手,第一個16歲世界賽車手冠軍居然也是她! “秦阮,你到底還隱藏了多少秘密。”男人將她比如墻角,對自己將她追回勢在必得。 她卻瀟灑將他推開,只留下一個瑰麗的背影。 “狗渣男,去死吧。”
39.2萬字8 1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