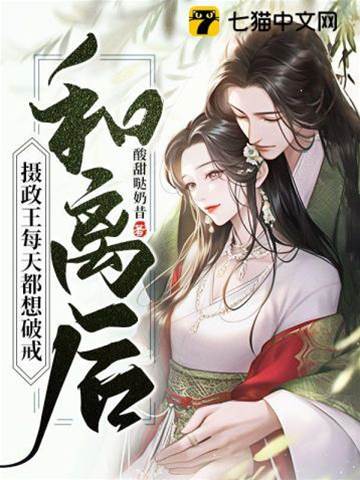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我見探花多嬌媚》 第二百二十七章敘敘話
顧長平此刻正走進錦衛的天牢里。
盛等在半路,遠遠見一道瘦削清冷的形,沖后的干兒子道:“都安排妥當了?”
干兒子陪笑道:“您老人家開的口,哪能不安排好。只是兒子不明白,您與顧祭酒素無往來,怎麼這會子倒盡心替他辦事了?”
盛微瞇起眼睛,冷笑道:“這也是你該問的?”
干兒子立刻給了自己一,“瞧瞧我這破,總是欠,氣著您老人家。”
盛懶得多言一句,大步迎上去。
干兒子沖他背影,撇撇,心道:干爹定是收了顧長平大把大把的銀子,才這麼殷勤。
真看不出來,顧祭酒還是個有有義之人。曹賊抄家后,他可是第一個來瞧曹賊的人。
“顧大人!”
“盛大人!”
顧長平抱了抱拳,遞過去早已備下的銀票,“拿著,天寒給兄弟們買點酒喝。”
盛從銀票中出面額最小的一張,塞進袖中,“一切都妥當,我親自陪大人走一趟。”
“如此,便有勞了!”
兩人并肩而行,順著臺階拾級而下,油燈暈暗,時不時傳來幾聲氣若游的聲。
牢房油燈昏暗。
顧長平站在鐵柵外,看著里面的人,低聲道:“盛大人,可否讓我進去陪先生一敘?”
盛立刻掏出鑰匙,打開牢房門,“顧大人,我在外頭等你!”
顧長平頷首,躬走進牢里。
“你來了!”
曹明康盤坐在惡臭的草席上,短短數日,已盡顯老態。
顧長平把食盒放下,學著曹明康的樣子盤而坐,也不嫌棄草席臟。
打開食盒,拿出一盤燒,一盤醬鴨,一盤素什錦,一碟花生,兩個酒盅,兩壺上好的竹葉青。
Advertisement
曹明康冷笑一聲,“子懷有心了!”
“應該的!”
顧長平給兩個酒盅倒滿酒,拿起一杯奉到曹明康面前,“先生,請!”
曹明康沒去接。
顧長平知道他在擔心什麼,把酒往里一送,飲盡了,低笑一聲,“先生,毒殺罪臣,我還沒那個膽!”
曹明康面一白,抖著道:“你到底想干什麼?”
顧長平又將酒盅倒滿,慢條斯理道:“不想干什麼,就想陪先生喝喝酒,敘敘話。”
曹明康只覺得心頭氣一陣翻涌。
他突然想到多年前,清瘦年跪在他面前,心事統統寫在臉上,如一彎干凈了的湖水。
曹明康與顧長平對視,他著他的眼神--
如今七八年風雨剛過,這張臉再不能看出一的喜怒。
也難怪,自己栽在了他手上。
曹明康沉默著將酒盅接過,一仰頭喝,顧長平再斟酒,他再仰頭……
三杯過后,他把杯子一扔,長嘆道:“我聰明了一輩子,不曾想竟被自己養的狗咬死,真是眼瞎。早知今日,當年我不該心留他。”
“先生其實可以換個角度想想!這不過是因果報應,又一個回罷了。”
曹明康眉心一跳,雙手死死的握拳頭。
牢中的時間仿佛停滯了。
良久,他咬牙道:“你……你……是如何知道的?”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先生,這世上沒有。”
顧長平口氣是既平也淡:“當年你踩著顧家人的尸骸上位,顧家上上下下數百口人,都是你青云路上的墊腳石,該還了!”
曹明康的子開始發抖。
那年他看出先帝空有一翻雄心報負,卻掣于顧家雙雄及宮中顧太后,便絞盡腦的想盡一切辦法要給先帝遞投名狀,為此不惜花巨銀買通了從小就侍候先帝的一個老太監。
Advertisement
有了老太監有意無意的牽引,先帝這才把目投向他。
先帝看中他,并非他有多聰明,而是他足夠卑微和渺小,不會引起顧家人的注意,才能以小搏大。
他沒有辜負先帝的希,從顧家最不統的顧六爺下手,以一已之力將顧家顛覆,從此平步青云。
只是他死活弄不明白的是,當年顧家的事,除了先帝外,只有數幾個人知道,這些人后來都被他滅了口,顧長平是如何知道這一切的?
“誰是當年的網之魚?”
“先生何必糾結這個,我說了,這世上本沒有。”
顧長平嘆了口氣,“不過有件事我倒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伴君如伴虎,先帝縱你滅了顧氏一門;也可縱我為了顧氏一案,而屠你曹府滿門。”
曹明康不可思議地睜大了眼睛,半晌后,他突然發出一陣大笑,笑出了濁淚。
本以為新帝弱無能,此事都應該是顧長平一人所為,卻不曾想,新帝和他早就穿了一條子。
不對!
笑聲孑然而止。
曹明康一把揪住顧長平的前襟,“誰,縱你為了顧氏一案,而屠我曹府滿門?”
顧長平笑了下:“是先帝。”
“先帝?先帝!”
曹明康喃喃自語。
慢慢的,揪著顧長平的手一點點松開,最后無力的垂落下去。他侍奉先帝幾十載,榮寵加,一呼百應,可謂真真的寵臣,
可再榮寵,同顧家一樣,也不過是臣。
臣,便是要用來祭殺的。
這樣才能換來新帝對大奏朝的說不一二。
果然是因果報應,又一個回。
曹明康原本恍惚的眼睛,漸漸清明,冷笑道:
Advertisement
“既然是回,那麼顧家曾經的下場,便是我如今的下場;我如今的下場,也是你將來的下場。咱們……誰也逃不掉,逃不掉!”
說完,曹明康死死的盯著顧長平,期盼在他眼中看到一他預想中的慌。
可惜沒有。
顧長平的眉目在昏暗的燭火中,像是籠起一層煙幕般的霧氣,他笑了笑,道:
“命運這東西,怪得很。看不見,不著,等你察覺到它的時候,都在臨死之前。我的下場是好也好,是壞也罷,都不是先生應該心的事。先生該心的,是你的家人。”
顧長平頓了頓,道:“為先生的學生,回頭我會上書一封給天子,求他看在先生為大秦勞一生的份上,對曹府的家眷網開一面,免了死罪。”
猜你喜歡
-
完結986 章

農門有喜無良夫君俏媳婦
東臨九公主天人之姿,才華驚艷,年僅十歲,盛名遠揚,東臨帝後視若珠寶,甚有傳位之意。東臨太子深感危機,趁著其十歲壽辰,逼宮造反弒君奪位。帝女臨危受命,帶先帝遺詔跟玉璽獨身逃亡,不料昏迷後被人販子以二兩價格賣給洛家當童養媳。聽聞她那位不曾謀麵的夫君,長得是兇神惡煞,可止小孩夜啼。本想卷鋪蓋逃路,誰知半路殺出個冷閻王說是她的相公,天天將她困在身旁,美其名曰,培養夫妻感情。很久以後,村中童謠這樣唱月雲兮哭唧唧,洛郎纔是小公舉。小農妻不可欺,夫婦二人永結心。
173.1萬字8.18 37020 -
完結237 章
重生后王妃咸魚了
沈妝兒前世得嫁當朝七皇子朱謙,朱謙英華內斂,氣度威赫,為京城姑娘的夢中郎君,沈妝兒一顆心撲在他身上,整日戰戰兢兢討好,小心翼翼伺候。不成想,朱謙忍辱負重娶出身小門小戶的她,只為避開鋒芒,韜光養晦,待一朝登基,便處心積慮將心愛的青梅竹馬接入皇宮為貴妃。沈妝兒熬得油盡燈枯死去。一朝睜眼,重生回來,她恰恰將朱謙的心尖尖青梅竹馬給“推”下看臺,朱謙一怒之下,禁了她的足。沈妝
37.5萬字8 18649 -
完結239 章
念卿卿(重生)
【男主篇】 梁知舟一生沉浮,越過屍山血海,最後大仇得報成了一手遮天的國公爺。 人人敬着他,人人又畏懼他,搜羅大批美人送入國公府,卻無一人被留下。 都說他冷心冷情不知情愛,卻沒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漫長的夜裏,是如何肖想自己弟弟的夫人,如癡如狂,無法自拔。 他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便是沒能阻止她成親,哪怕拼死將她救出,得到的只是一具屍骨。 所幸他重生了,這次那怕冒着大不韙,他也要將她搶回來。 沒有人比我愛你 在你不知道的歲月裏,我已經愛了你很多年 —— 【女主篇】 虞念清出身樂平候府,生得冰肌玉骨,容貌傾城,不僅家中和順,還有樁令人豔羨的好親事,京中無人不羨之妒之。 可無人知,她夜夜所夢,與現實恰恰相反。夢中,她那才學雙絕的未婚夫勾引她人,而素來對她慈愛有加的祖母卻爲了家族利益強逼她出嫁,再後來,母親兄長接連出事,一夜之間她引以爲傲的一切都成了鏡花水月。 夢醒後,爲了化險爲夷,虞念清將目光對準了前未婚夫的兄長—— 那個善弄權術,性子自私陰鷙的、喜怒不定的天子近臣,梁知舟。 虞念清膽顫心驚走過去,望着面前如鬆如竹的的男人,猶豫很長時間才下定決心問:“你能不能幫我?” 男人俯身捏起她的下頜,俊臉隱匿在陰影裏,看向她目光沉沉,“我從不做虧本的買賣,你可想好?” —— 【小劇場】 虞念清記錄日常的生活的小冊子被發現,上面這樣寫着: “梁知舟很危險,但是他願意幫我” “晚上做夢夢見了一個和梁知舟很像的人,他一直親我” “梁知舟變了樣子,我很怕他” “原來那幾次夢中親我的人都是他” “我想起我們的上輩子了” “他是壞人”(被劃掉) “他很愛我” “我想我也是”
39.5萬字8 2844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80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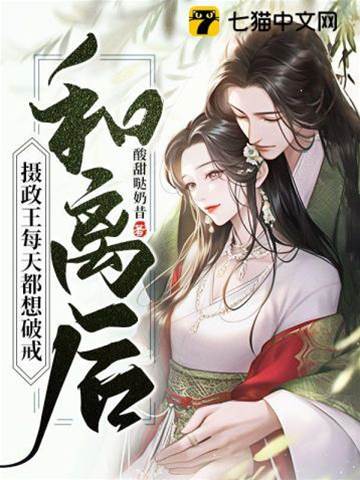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