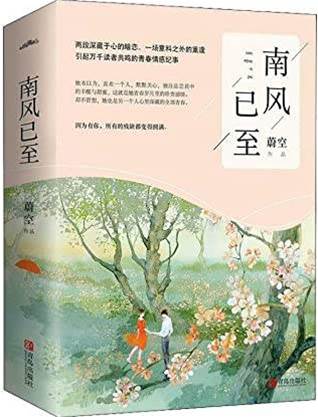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完美隱婚》 第128章 至於婚禮,蕭家可以不給
這一頓飯,吃的還算融洽。
蘇老爺子和靳恆遠頗有話題,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事;蘇老太太則和靳恆遠提到了他母親靳媛的近況。
蘇錦不說話,低著頭,聽了之後這才知道:和那個還沒見過面的婆婆是認得的,曾幾次在慈善義拍上見過面,還一起吃過飯。
「當年蘇家遇上經濟窘境時,靳士曾出手幫過一把。至今我還記在心上。」蘇老太太委婉的表示了一下激之。
靳恆遠微微一笑,接話道:
「我母親脾氣比較直爽,不是死板之人,懂得變通之道,若非是人,想過幾天簡單的相夫教子的小日子,的作為,在商場上,應該比蕭家人來得的更大。」
這句話,明顯敬著母親,心也是向著母親的——在蕭家,只有他父親蕭至東是經商的。
是的,聊天的時候,靳恆遠提到了他母親的豪爽,提到了他外祖父外祖母的寬厚,就是閉口不談蕭家任何人。
這是為什麼呢?
蘇錦不得而知,只覺得裡頭的原因,怕是極其複雜的。
飯後,蘇老爺子聽了一個電話,就帶著蘇老太太離開了。
這當中,這對老夫妻,也是絕口未提蘇暮白的事。
可見,他們此來,不是來拆姻緣的,而是來表關心的。
臨走,靳恆遠一恭敬,給了一個承諾:
「爺爺,出孝之後,我一定請上長輩登門拜候。」
蘇老爺子頗為欣:
「好,我一定在家敬候!」
車子駛離,靳恆遠、蘇錦、蘇暮笙在路邊揮手目送。
「我……去商城買點東西。姐夫,你帶姐去好好談談吧!」
蘇暮笙識趣的走開,很快在人來人往的步行街上沒不見。
城市是這麼的繁華。
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忙碌。
悲傷離合,喜怒哀樂。
Advertisement
每個人都在忙碌中寫著屬於自己的宿命似的人生故事。
有人幸,有人不幸。
機緣無不在。
有人峰迴路轉,人生再現一片彩。
有人樂極生悲,生命只剩一抷白灰。
有人平平淡淡,至死庸庸碌碌。
有人生於富貴,游刃於名利之間,一生風無限……
世有萬萬人,萬萬人的境遭皆不會相同。
這就是生活。
有點發燙。
靳恆遠環視了一圈人流、車流綿綿不息的街道之後,轉頭看靜立邊的蘇錦。
以後,就是他生活的中心。
他凝睇著。
雖畫了妝,可臉上的紅腫還是看得分明的,爺爺大約是老眼昏黃了,所以才沒有留心到。
真要看到了,恐怕又是另一番擔憂。
此刻,的臉無比平靜,可心底呢?
可像臉這樣毫無波瀾?
「我……」
「我……」
兩人不約而同開了口。
靳恆遠笑容溫溫的:
「太太先說。」
這句話燙到了蘇錦的心。
「我想一個人走走。」
低聲說: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吧!我想一個人冷靜的想一想。」
「你確定?懷著一肚子的疑問,不和我說說話,你就能自個兒想清楚?」
靳恆遠挑眉反問,語氣沒有半點不快。
「是,我確定。
「我想獨自梳理一下自己的緒,更需要時間驚。
「靳恆遠,你帶給我的這些讓我意想不到的真相,不是我一下子說消化就能消化,說接就可全盤接收的,你知道嗎?」
抬頭,目輕盈,帶著請求之:
「想當初,我和你相親時,我要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婚姻,一份簡單的生活。
「可你已經把它複雜化了。
「而那份複雜,已經超出了我本來對於未來的預算。
「現在,我得重新考慮一切已經定型的況。
Advertisement
「冷靜的思考,有助於我迅速從現在這個狀況走出來。」
目接時,沒閃躲:
「有些事,我的確需要和你通,但不是現在。
「最大的杴,不在你,在我心裡。
「心結不是你可以解開的。
「它需要我自己想想通。」
說到這裡,又深深吸了一口氣:
「其實,想,也沒用,還得有足夠的勇氣去接以後可能面臨的一切。
「那才是最難的。」
靳恆遠聽明白了:指的是蕭家的態度。
「需要多久?」
「不會很久。」
輕輕說:
「到時我會聯繫你。然後,我們再好好談談。用比較理智的心態說說話。我現在的緒,其實還是很不穩定的。也許現在,我們談著談著就能談崩。」
垂下了頭。
他雙手袋,定定看:
「好。那我等你電話。你走吧!我看著你走。」
「再見。」
蘇錦抓著包,投了茫茫人海。
靳恆遠看著,眼中是滿滿的包容。
從來是一個缺乏安全的孩子。
小的時候如此,長大后,還如此。
他記得還是小書的時候,曾說過那麼一句話:
「二斤哥哥,人上怎麼就沒殼呢?就像田螺。要是有殼,被人欺負了,我可以躲在裡頭。就不用怕挨打,也不用擔心被罰著淋雨生病了……」
長大后的,因為在上了嚴重的傷,真的為自己造了一個保護殼。一應到可能會危及未來安寧的事要發生,就會進行自我保護。
在害怕到傷害。
因為有前車之鑒。
更因為,在的世界,與來說,誰也靠不住。
所以,已習慣了凡事靠自己,哪怕遇上可能是自己力不能及的事,也要冒險靠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
要是實在解決不了,就只能忍氣吞聲。
Advertisement
可的驕傲不允許常常去忍氣吞聲,怎麼辦呢?
只能防患於未然。
在可能發生傷害前,進行自我保護。
其實,活在世上的人,誰又沒過氣,過委屈呢?
只是有些人強勢,會有後來的揚眉吐氣;有些人弱勢,日子常過的戰戰兢兢,過的窩囊;有些人很努力的做著本份的工作,但求無過:不張揚,也不低聲下氣,努力經營生活的同時,把自己嚴嚴的保護著。
是第三種。
求著平淡,求著安穩,求著不傷害。
所以,才會抗拒。
這丫頭啊,真是太讓他心疼了。
蘇錦漫無目的在街上逛了一圈,只買了一束鮮花——養母最的白鬱金香。
一輛計程車,將帶去了育才小區。
開門進房,蘇錦很驚訝。
「暮笙,你怎麼回來了?」
那個從來不知道要整理的蘇暮笙,竟在養母的像前著檯面,正目深深的睇著照片上的人兒,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聽得,回頭也驚怪的了起來:
「姐?你也來了?不對,你怎麼一個人啊?」
他往外頭張著:
「姐夫沒跟過來嗎?」
「沒有!」
蘇錦去找玻璃花瓶,裝水,把花了進去,送到養母像前。
「談的怎麼樣?」
蘇暮笙像跟屁蟲一樣,追著問。
「沒談!」
「為?」
蘇暮笙眨眼,滿面不解。
蘇錦靜靜看著像:
「我需要……想一想。」
給養母上了一柱香,去擰了一瓶水,一邊喝一邊往房裡走。
「想什麼啊?」
蘇暮笙繼續追著。
這景,就像小時候一樣,這孩子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追著,打破沙鍋問到底。
養母看了,常常發笑。
現在,依舊在笑,只是掛在牆上了。
蘇錦沒答,進了自己的房,先是把房間整理了一下,暮笙懂事的幫忙,然後,從床底下拉出整整齊齊一大包。
Advertisement
「這是什麼?」
暮笙的注意力轉移掉了,看著蘇錦仔仔細細的把捆在上面的繩解開,展開外頭那一層牛皮紙,全是畫——的畫。
最上面的那張,被裱了起來,裡頭是一對年輕男。
嫻靜如水的子,笑臉若芙蓉,清雅之極,那是畫筆下的姑姑;英俊不凡的男子,笑得明亮,溫潤如東升之旭日,那是畫筆下的蕭至誠……
事隔多年,他們的音容笑貌宛似還在耳邊在眼前,可他們,到底已經不在了。
「姐姐,你別難了。姑姑和至誠叔叔都過世那麼多年了……你要這麼想,害死姑姑的不是蕭家,是那個該死的傅世淳。全是那混蛋,毀了姑姑,第一次婚姻報銷在他手上不說,還毀了姑姑另找幸福……」
蘇錦坐在地上,著那張畫兒,似水流年,好像又在眼前重演了一遍似的,經過了那麼多年,記憶不是模糊了,而是越發清楚了。
輕嘆,自裡幽幽飄出來:
「是啊,全是傅世淳害的。
「那場錯誤的婚姻,姑姑早不想要了。
「一直想離,離不了。
「我進蘇家的第二年年底,姑姑就在那心思了。
「那時,傅世淳早在外頭養人了。只是保工作做的相當好,本讓人查不到養的是誰?
「既然都有了其他人,就該把姑姑放了。
「可他為了錢,為了姑姑陪嫁的那些份,拖著死命的不肯離婚。
「姑姑和他談離婚,他就要全部的份,你知道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嗎?
「要是讓步了,就等於把半個蘇家全給了傅世淳。
「姑姑哪能把蘇家的份給了那敗家子。只能忍了。
猜你喜歡
-
連載757 章

婚期365天(慕淺霍靳西)
(此書已斷更,請觀看本站另一本同名書籍)——————————————————————————————————————————————————————————————————————————————————————————————————————————————————————————————————慕淺十歲那年被帶到了霍家,她是孤苦無依的霍家養女,所以隻能小心翼翼的藏著自己的心思。從她愛上霍靳西的那一刻起,她的情緒,她的心跳,就再也沒有為任何一個男人跳動過。
133.4萬字8 2244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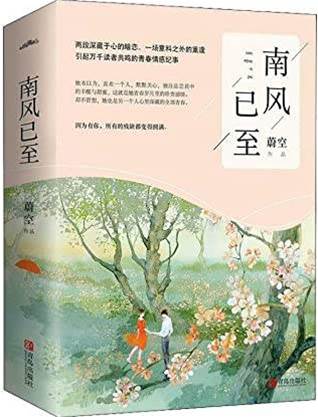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78 章

為情所婚
故事的開始,她闖入他的生活,從此天翻地覆。 故事的最后,他給了她準許,攜手共度一生。 一句話簡介:那個本不會遇見的人,卻在相遇之后愛之如生命。
20.9萬字8 19102 -
完結1547 章

墨少難惹:嬌妻帶球跑
他是商業帝王,清冷孤傲,擁有人神共憤妖孽臉,卻不近女色! 她是綠世界女王,冰冷高貴,卻…… “喬小姐,聽聞你有三禁?” 喬薇氣場全開,“禁孕,禁婚,禁墨少!” 轉瞬,她被丟在床上…… 某少居高臨下俯視著她,“禁婚?禁墨少?” 喬薇秒慫,想起昨夜翻雲覆雨,“墨少,你不近女色的~” “乖,叫老公!”某女白眼,拔腿就跑~ 某少憤怒反撲,“惹了我,還想帶球跑?”
272.3萬字8 60252 -
完結850 章

閃婚當晚,禁欲老公露出了真面目
【重生打臉+馬甲+懷孕+神秘老公+忠犬男主粘人寵妻+1v1雙潔+萌寶】懷孕被害死,重生后她誓要把寶寶平安生下來,沒想到卻意外救了個“神秘男人”。“救我,我給你一
87.7萬字8.18 36674 -
完結201 章

我欲將心養明月
高中暑假,秦既明抱着籃球,一眼看到國槐樹下的林月盈。 那時對方不過一小不點,哭成小花貓,扒開糖衣,低頭含化了一半的糖,瞧着呆傻得可憐。 爺爺說,這是以前屬下的孫女,以後就放在身邊養着。 秦既明不感興趣地應一聲。 十幾年後。 窗簾微掩,半明半寐。 秦既明半闔着眼,沉聲斥責她胡鬧。 林月盈說:“你少拿上位者姿態來教訓我,我最討厭你事事都高高在上。” “你說得很好,”秦既明半躺在沙發上,擡眼,同用力拽他領帶的林月盈對視,冷靜,“現在你能不能先從高高在上的人腿上下去?”
31.6萬字8 2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