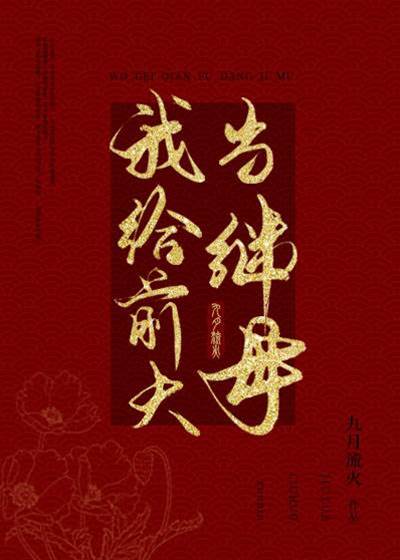《位極人臣后我回家了》 第46章 第46章
小怪的力顯然比好得多, 背著這個累贅,也走的毫不費勁。常意不知道他背著自己走了多久,總之應該比之前走的路長的多。
里看不見日月, 也沒有一,常意沒辦法判斷時間,只能安靜地趴在它背上, 看著它走了很久很久。
它背著停在了一地方, 常意跳下來,或許是被背久了, 的也恢復了力氣,走起路來也不費勁了。
這地方和剛剛的不同,方方正正的, 顯然是人工修建過的。常意在這個小房間里繞了一圈, 了里面的東西, 大多是些銅之類的, 還有些服,它應該就是在這里翻到的服。
和看到小怪上的服時猜想的一樣, 這些東西都是陪葬品。
他們現在于墓中,或許是山崩發了什麼機關, 又或者是這墓引發了山崩,都有可能,而意外又倒霉地掉進了里面。
常意嘆了口氣, 搞清楚在哪對的境沒有太大的幫助。
如果不是天然形的山, 很難在其中找到水源和食, 而且墓作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如果沒能找到出口,這里面的空氣也不夠撐多天的。
那麼出口呢?
既然他們現在在這個放陪葬品的耳室里, 肯定有其他地方是相連的。
問題就在這。
常意抿,咬牙看向了這間屋子里本來的門。那里已經被沖下來的石塊堵死了,不僅死死地堵住了這個口,甚至傾瀉出來的坡度都占據了小半個房間。
顯而易見,這個墓已經因為之前的山崩坍塌了,剩下完好的空間,只有他們現在所的這個耳室,和剛剛走過的那個閉空間。
常意深呼吸一口氣,確認沒有其他出口了,找個地方坐了下來。
Advertisement
徹底放棄了。
主墓室都塌了,這墓里已經全部走過一遍了,沒有任何出口,想出去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自己打個上去——沒有工,要有這個本事憑空打個,也不至于掉到這里面來。
指外面的人找到也很渺茫,這樣的墓一般都不淺,他們救援的人頂多清理地面的碎石,不會無端往下挖幾尺,平白浪費人力力。
得接一個人死在地下的事實——哦,不是一個人,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小怪。
也不知道怎麼他,干脆就順其自然地他小怪,它好像也能聽得懂。
它看著常意靠著墻坐下不了,也磨磨蹭蹭地走到邊,挨著坐下。
它像只被馴養的寵一樣,地著,眼神一點也不加掩飾地看著。
如果是其他人,常意絕對不會讓他靠近自己,但它的一舉一都太本能了,常意看著它,只能聯想到直白的類,被一直野親近,有點奇怪,但沒有被輕薄的怒氣。
它也沒有別的作,只是輕輕地靠著,好像在上屬于人的溫度。
小怪的形比常意高得多,跟它的型比起來,能從常意上汲取的溫度有限。它了,似乎想再靠近一點,但不知道是不是被剛剛的匕首刺過一次,并沒有繼續。
常意一直注視著它,見狀頓了頓。
沉默了一會,腦子里有點空,在這里,只有一個人類,面前的小怪,不會說話,也不會思考。
沒必要想太多,畢竟可能馬上就要和它死在一塊了。
常意慢慢地出手,拉住了他的手腕,說道:“你很冷嗎?”
它用另一只手蓋住的手背,在一片漆黑中,看見它的眼睛深邃地注視著他,淡灰的瞳孔一道豎線,說不清楚那是什麼覺,從和它相的皮上覺到了它的興和混沌。
Advertisement
它的手很燙,不像冷的樣子。它捧起的那只手,輕輕放到了自己的臉上,常意冰涼的手著它的皮,它閉上了眼睛。
有點像以前看別人養過的,在懷里撒的小狗。
沒養過什麼寵,春娘不會讓養的,淮侯也不會送,寵是很貴的。
常意回手,從上出一塊油紙包著的東西。
不用它表現出來,常意也知道它不知道怎麼打開,把油紙拆開,出里面一塊雪白蓬松的糖。
“這是銀糖。”常意知道他聽不懂,但不說些什麼,在這安靜的空間里未免顯得太空寂了:“你背了我那麼久,吃一點東西吧。”
雖然這點糖只是杯水車薪,但好歹還有點甜味。
有關扶等人在,穿著羅,自然不會帶什麼干糧餅子在上,這糖是上唯一能吃的東西。
這是前幾天特意讓關扶買的糖,本來是想上山的時候帶給那個厭的年的——他當時吃的時候,表是見的雀躍。
常意記很好,所以又買了那塊糖,只不過他吃不到了。
它就著常意的手咬了一口銀糖,眼睛亮晶晶的。
“你也喜歡吃糖?”
在沒有生路的境地下,常意意外放下了滿腦子的思慮,放松下來,懶散地說道:“我本來是想來山上找人的,也不知道山崩了,他有沒有活下來。”
小怪聽不懂,但作為一個傾聽者來說,這樣更好。
“他沒嘗過甜。”常意有一搭沒一搭地說道:“我以前也沒嘗過,所以我想讓他嘗嘗......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活在這世上的,有哪個人不苦呢?”
想拉那個年一把,實際上只是想拉自己一把。
想活,想建功立業,活得比之前更好;他也想活,想知道真相,想堂堂正正地活著。說到底,他們都只是在人間努力掙扎的普通人罷了。
Advertisement
可惜都不走運,都得葬在這山上了。
小怪默不作聲地臥在間,手里捧著半塊糖不彈了。
怎麼不吃了?
......沒有靜。
常意再一看,他已經靠在上睡著了。
......睡得這麼快,不會是豬妖吧。常意很佩服他在這種地方都能睡著,也可能它本就不清楚現在的境。
常意了它的頭發,烏黑的頭發沒有束起,但是意外地不是很臟。心里浮起點淡淡的疑,它不會說話,但卻知道用服蔽,也會清理自己的。
清理不奇怪,也會,但不會有恥心,也不會去尋找服蔽——這是人才會有的習慣,或者說被人影響后的習慣。
它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是人,為什麼會變這樣?
常意下意識地去想,但突然反應過來,它是什麼東西,已經沒必要去細究了。
看著它閉著眼,閉,角下微抿,鼻梁高,不的時候,和正常人似乎沒什麼區別。
算了......不是一個人死在這里面,也是一種不幸中的萬幸了。
它上像是有把火,靠在上暖烘烘的,常意一個人安靜地坐了一會,居然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
再次睜開眼,常意明顯覺到了自己這的反擊,嗓子疼得好似被人用刀進管里捅了幾刀,眼睛幾乎腫得睜不開了。
反正沒有,睜不睜開都一樣,常意干脆閉著雙眼。上的反噬意料之中,本來就不是什麼健康的,在地下不知道多久沒進食水了,又走了很久的路,幾重力下幾乎面臨崩潰。
輕輕張了張,角干裂到粘粘在了一起,發現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反倒嗓子好像被撕開了一點,更疼了。
Advertisement
需要水。
但這里面不可能有水源。
所以放棄了掙扎,想盡量節省一點力氣,然后慢慢等待死亡。
雖然早就預料到了結果,但果然......真正面對的的時候,還是有點不甘心啊。
有什麼溫熱的東西在了的手上,先是試探地了一下的溫度,又包裹住的手,指尖探的指,牢牢箍在一起。
常意反應過來,那是它的手。
它的手比大許多,握著,好像在給傳遞溫度。
常意雖然睜不開眼睛,但也能覺到它在看。
它大概在疑自己怎麼了吧?
常意張了張,但是說不出話,也不知道說什麼。
仿佛全的骨頭都被盡了一般,得沒有一點力氣。意識越來越模糊了,已經不到面前的小怪在干什麼了。
唯一的,只剩下兩人握著的雙手,它死死地攥著,好像在用疼痛提醒,還活著。
常意苦笑著想,沒用了,放手吧,別拽著了,萬一真死了,他似乎也分辨不出來。
不過它的確實比好,同樣在里待了這麼久,沒吃沒喝——甚至還要比更久一點,但看它這麼大勁,一點事兒也沒有,只是披了件服也沒著涼。
覺到小怪牽著的手,已經很久沒了,漸漸的,它的力氣也松下來,放開了的手。
有指節蹭過了的,常意的已經裂開了,連那若有若無的過都疼得心里一,好在它沒有繼續到,而是進了的,指節微曲撬開了的。
口腔被他人手指侵略的覺并不好,常意牙齒磕在它手上,想用咬合它退出去,被它撐住。
雖然已經沒什麼力氣了,但咬合力足以在它手指上留下疤痕,它卻像不到痛一樣,一直拿指節撐著微張的。
有些惱怒,但沒有一點力氣反抗,罵也罵不出聲。下一秒,便覺到一道撕裂的聲音。
溫熱的、潤的皮湊近了的邊。
微微粘稠的順著的邊到口腔里,充斥著閑腥的鐵銹味,流干涸的管,緩解了一點的疼痛。
它是傻子嗎?!
常意反應過來它在給自己喂什麼,劇烈掙扎起來——但這點沒力氣的撲騰,還不如岸上瀕死的魚。
哪怕被撕咬、被用舌尖抵住,它自始至終都不曾移開撐著的手,將一點一點喂進里。
猜你喜歡
-
完結208 章
重生之農家釀酒女
現代調酒師簡雙喪生火海又活了,成了悽苦農家女簡又又一枚. 一間破屋,家徒四壁,一窮二白,這不怕. 種田養殖一把抓,釀酒廚藝頂呱呱,自力更生賺銀兩 培養哥哥成狀元,威名赫赫震四方. 曾經的嫂嫂一哭二鬧三上吊,撒潑後悔要復和,陷害栽贓毀名聲,讓你仕途盡毀;霸氣新嫂嫂一叉腰——打. 酒莊酒樓遍天下,不知從哪個犄角旮旯裡冒出來的七大姑八大姨齊上陣,奇葩親戚數不清,老虎不發威,當她是軟柿子? 大燕丞相,陷害忠良,無惡不作,冷血無情,殺人如麻,人見人繞之,鬼見鬼繞道;只是這賴在她家白吃白喝無恥腹黑動不動就拿花她銀子威脅她的小氣男人,是怎麼個意思? ************** 某相風騷一撩頭髮,小眉一挑:"又又,該去京城發展發展了." 某女頭也不擡:"再議!" 再接再厲:"該認祖歸宗了." 某女剜他一眼:"跟你有半毛錢關係?" 某相面色一狠,抽出一疊銀票甩的嘩嘩響:"再囉嗦爺把你的家當都燒了." 某女一蹦三丈高:"靠,容璟之你個王八蛋,敢動我銀子我把你家祖墳都挖了." 某相一臉賤笑:"恩恩恩,歡迎來挖,我家祖墳在京城…"
66.4萬字8 73556 -
完結1729 章

一品嫡女
她是丞相長女,為助夫君登上皇位,容貌盡毀,忍辱負重。豈料,渣男早已與心機庶妹暗中茍合,藉口將她打入冷宮,再聯手庶妹逼她剖腹取子,逼她唯一的弟弟淪落成乞丐,殺她全家,將她做成人彘,囚禁於牲口棚,與豬狗同眠,受盡人世間最慘痛的折磨。 一朝重生,她脫胎換骨,浴血歸來,仇恨加身!頂著一張美艷的「冷血臉」,奪重權,鬥姨娘,殺庶妹,杖奴婢,遇神殺神,遇鬼殺鬼,渣男隔三差五登門拜訪,變著花樣提親,她隻給他一個字:「滾!」 她說,這一世,不動心,不動情,不愛,不恨,隻願如此過一生。可惜,最終她還是逃不過前世欠下的情債。 他說:江山,本王要;你,本王也要,皇權之中若少了你,哪怕生靈塗染,江山盡毀,背負一世罵名,被日夜詛咒,我也要奪回你。 他說:我的骨子裡,我的血肉裡,我的經脈裡,都隻有三個字——連似月,你要走,我陪你赴湯蹈火;你要留,我陪你細水長流。
313.8萬字8.18 57275 -
完結2098 章
醫笑傾城
天才醫學博士穿越成楚王棄妃,剛來就遇上重癥傷者,她秉持醫德去救治,卻差點被打下冤獄。太上皇病危,她設法救治,被那可恨的毒王誤會斥責,莫非真的是好人難做?這男人整日給她使絆子就算了,最不可忍的是他竟還要娶側妃來噁心她!毒王冷冽道:「你何德何能讓本王恨你?本王只是憎惡你,見你一眼都覺得噁心。」元卿凌笑容可掬地道:「我又何嘗不嫌棄王爺呢?只是大家都是斯文人,不想撕破臉罷了。」毒王嗤笑道:「你別以為懷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會認你這個王妃,喝下這碗葯,本王與你一刀兩斷,別妨礙本王娶褚家二小姐。」元卿凌眉眼彎彎繼續道:「王爺真愛說笑,您有您娶,我有我帶著孩子再嫁,誰都不妨礙誰,到時候擺下滿月酒,還請王爺過來喝杯水酒。」
694.5萬字8.33 9267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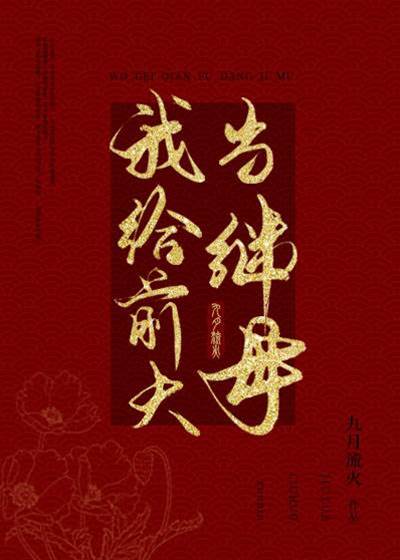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40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