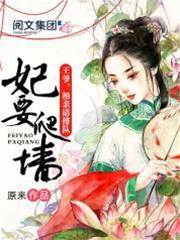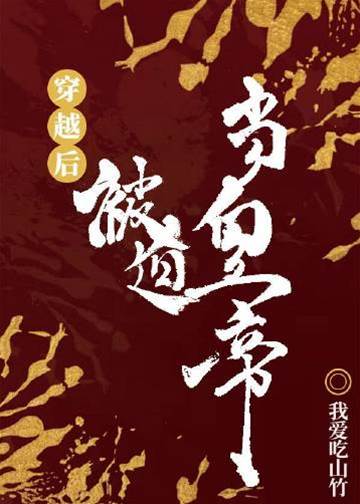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160章 第 160 章
每天傍晚皇宮落鑰前, 起居舍人會把今日皇上的起居注送國史館中,上頭記錄著帝王從早上起床到夜里睡下這期間的每一件事。
人無完人嘛,誰也不住一天十二個時辰不錯眼地觀察, 起居注上有時也會悄悄缺一節、一頁。
守門的金吾衛站了一天崗, 眼地等著宿衛來換防,正是一天中最松懈的時候。老遠瞧見個紫老公公, 蹣跚著腳步,帶著四個小太監緩步行來。
小衛兵打起神,忙把大門推開:“明公公, 又來送起居注啦?”
明公公面皮兒微寒,眼風也不往兩邊掃,像往常一樣趾高氣昂地進去了。
其實頂著張人|皮|面, 真的不太敢眉弄眼——盡管年頭兒說放心戴,質量妥妥的,可這面薄如蟬翼, 叁鷹怕自己笑一笑,面當著人繃兩半兒。
盛朝的國史館落在了外廷西頭的武英殿,主殿占地一畝半,還有東西配殿兩座, 穿廊嵌套了一重又一重,莊重又深沉。
叁鷹當著金吾衛的面兒鞋換,這是防塵用的,又掐細嗓子說:“你們在外頭候著罷。”
扮作小太監的幾個影衛應聲站定, 各個長了雙能一百八十度轉圈的眼, 暗中觀察著金吾衛每一個樁點,出了事兒,也好及時呼哨傳信。
皇宮史館分兩座, 一座是挨著東宮及文華殿的東史館,一座就是這武英殿——文華殿多為書,存放的是皇帝廷旨、閣宗卷、員貶擢、各地奏折檔、軍機檔等等。
太子看書,看的自然也不是閑書,他多數時候都在文華殿呆著。
武英殿則更晦一些,這里頭有地地道道的皇家大事記:開國的祖皇帝、奪嫡篡位的庶皇子、進爵為異姓王的封疆大吏、作的佞臣、宮闈之禍中某妃嬪蹊蹺謎的死因……
Advertisement
除了皇家和宗室之外,還存放著歷朝文武大員的生平事跡。王朝二百多年,沒資格配太廟的王侯與名臣海了去了,家資料全在這里放著。
百年盛世,盛朝還從沒有過一句話聽得不順耳就搞滿門抄斬的皇帝,于是史表忠心的最好辦法,就是直言不諱、下筆如刀,將君臣一言一行詳實地記錄下來,為一雙雙近真實的眼睛,留下史料,供后人評說。
一排排的書架有丈來高,稀疏地分格陳列著傳記。
叁鷹腳步聲輕悄,在殿繞了個圈,沒想好放哪兒去。
風里雨里蹚過多回了,外頭的換防聲響起,宿衛就在廊下走,叁鷹也不慌,他揣著匣子這邊翻翻,那邊瞅瞅,覺得放哪兒都不合適。
門邊的書架太顯眼,保不齊被哪個眼尖的看著;放殿深吧,通風不好的地兒容易,太監檢查得勤快。
塞進歷代皇后里吧,好像不太合適;塞進夭折皇子那一堆里吧,又怕殿下不高興;塞進臣錄里吧,有點對不住姑娘。
他這麼琢磨著。
忽然,殿深傳來幽幽一聲。
“別翻啦。”
叁鷹嚇得三魂六魄沒了一半:“誰!”
他一激,下意識地繃肩腰,繃了一把蓄勢待發的弓,往殿深去。
叁鷹心思電轉:進門時整個大殿都是黑的,沒一點亮,也沒聽著氣息,能騙過他耳朵的只能是習武之人!
東南角上的暗,慢悠悠亮起了一盞燈,太子穿著一常服,笑得有幾分促狹。
叁鷹三魂六魄又排好了隊,立刻塌腰彎一座拱橋,掐老太監的腔調:“殿下怎麼在這兒?老奴給殿下請安。”
太子:“別裝了,我聽出是你了,二弟你來做什麼?”
Advertisement
叁鷹只好又直起腰來,干笑著把事兒說了。
他窺著太子殿下的神,沒從這位主子爺臉上瞧見丁點的驚訝,仿佛他開了個頭,太子就已經了然于了。
叁鷹猜得確實不錯。
工部影像院半夜停,大清早天剛明,又倉促地催著魯班匠開工;騰出軍驛三百人手,全留著待命,明兒一早就要把還沒配好畫帶的放映機送往各地去。
這麼大的靜,太子靠三分消息、三分觀察、再加四分猜測,就把事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拿來我瞧瞧。”
叁鷹忖了很短的一瞬,沒敢耽擱,應了聲“好嘞”,端著扁匣呈上前了。
太子大致翻了翻,他們寫得太碎,贅述也多,全謄抄了蚊蠅小字。他一眼掃過最前頭幾行,不值當細看,往后頭一翻,同樣看到了那三張畫。
做大哥的笑得靠在書架上,笑完了,太子悠悠道:“放進歷代王妃生平紀事中罷。”
叁鷹一迷瞪:“……會不會太逾矩了?”
太子似笑非笑瞧著他。
叁鷹不知怎麼,立馬領會到了太子的意思。
等太子登上大寶,殿下妥妥晉爵一字王,二姑娘……就算當不了王妃,姓后頭怎麼也得帶上“側妃”倆字了,這不板上釘釘的事兒麼。
“還是殿下說得對,您火眼金睛,奴才一萬個不如您!”
叁鷹找見歷代王妃那一排架子,樂淘淘地放進去,沒敢摞最后邊,往前邊的王妃傳記冊中拉了條,把扁匣藏進去了。
越想越覺得這地方好:國史館雖說前廷后宮幾位主子都能進,可誰閑的沒事兒去翻歷代王妃的生平去?
文華、武英殿里的國史都是傳抄本,就是手抄的,這兩座殿里的書足有幾萬冊,從來不雕版刻印——怕匠人無德,雕版流民間,再由坊間的刁民篡改、戲說正史,所以從來都是由司禮監和翰林院筆錄的,十年才清點翻新一回。
Advertisement
下一回清點的時候,沒準老皇帝都駕鶴去西天玩了,放這地方真是妙啊。
他折回,一個腦袋叩地上:“奴才告退,主子爺也早點歇息,您還要看多久啊,奴才給您多點兩盞燈吧?”
“不必,我也要回了。”太子揮袖,示意他自去。
叁鷹便躬告退。
東南角上的那盞燈又黯了,太子黑辨位,走回書架前,把翻了一晚的那本史籍放回去了——書脊上寫著《永徽二十四年紀事》。
那一年,是祖爺爺在位的最后一年。
年老的皇帝政務清閑,四十不以后沒什麼大功大過,那一年同樣沒做什麼打的事,前半本史冊就寫得乏善可陳。
直到時年八月,皇爺爺帶著嬪妃去承德避了避暑,遇上了四皇叔造反,二弟親手斬了四皇叔,京城中抄了幾戶人家,午門前浸石磚,罪名為謀逆。
這麼大的事,竟然只記了寥寥一頁,仿佛藏了個見不得的。
……
天幕黑沉,而與此同時,工部造放映機的魯班匠人收了尾。
所用的影屏越來越大,最后甚至拉了面三丈長的白布,支開放院子里,他們在測試最遠觀看距離。
一排排機挨個放到源前試播,幕布上每一段畫全流轉順暢,沒有卡帶和缺幀。
“奇啦!”魯師父了一聲:“我這昏花老眼站在二十步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又是正反兩面都能看的,演一場能坐下三五百人。等到了各府城,一天起碼能千八百人看上。”
徐先生不吝稱贊,一疊聲了好幾聲好:“當真是不世出的奇,諸位勞苦功高,回頭我必在太子面前給諸位請功!”
“多謝先生。”
匠人們寒暄著,一群工部小吏奔走其中,細致地在每臺放映機底座蓋上了方方正正的紅泥。
Advertisement
平平無奇的小篆字,卻是天下絕無人敢仿的印章——那是文帝的年號,將來會作為帝王的功績載史冊,好圣明君主青史留名。
至于發明人和造作者,能在史書上蹭個一隅,留下個鄙薄的賤諱,那就是祖墳上冒青煙了。
翰林觀禮的隊伍有十余人,都抓最后一晚上學習這萬景屏風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項,一邊記錄著這一奇的外形尺寸等等細節,再編《天工造》中整理文。
誰也沒注意到他們后邊還混了個影衛,仗著個子高,探著腦袋瞅人家翰林學士寫的錦繡詞兒,這邊抄一句、那邊倆詞的。
可惜天太黑,這群文化人寫得佶屈聱牙的,恨不得用遍字典上所有生僻字,好多字的筆順都看不清。
影衛黑著臉放棄了,扎了個馬步寫了個簡版本。
——時有異人唐氏,造放映機……好看至極,妙至極……
——初版三十臺萬景屏,于天寶七年九月十七夜,由十幾位翰林學士各領專差、武略將軍隨行護送,走軍驛送往各省。
國史館大門合攏、工部九月大事紀筆的那一刻。
相隔三里地的西市上,唐荼荼冷不丁地咬著了舌頭,疼得嘶了一聲。
忽有所地向東邊。幾道鐘聲,自街口的報時樓頂上送出,嗡——嗡——嗡,拖著長長的余音連響了五聲。
唐荼荼住筷聽了片刻,這分明是每天都聽得到的戌時鐘,卻好像跟平常有哪里不一樣了。
鐘聲穿力強,敲得一下子耳清目明,纏在上多日的、那種冷不丁恍惚一下,甚至左腳絆右腳的滯不見了。
這鐘聲似五長釘,釘印堂和四肢,將牢牢實實地楔在這個時代。
唐荼荼只疼了很短的一瞬,之后,大片沉甸甸的踏實涌來,像浮萍從此有了,深深扎進泥土里,諸事塵埃落定。
“荼荼怎麼啦,這魚不好吃?還是魚鱗沒刮干凈吶?”華姥爺問。
“沒事。”唐荼荼笑起來:“忽然頭不暈眼不花了,姥爺這兒的飯真好吃。”
“那可不!”華姥爺笑得合不攏,吩咐廚娘再給加倆菜。
“姥爺這兒的廚子是你娘花了大價請回來的,一個月十幾兩銀子供著——你娘沒個長,說風就是雨的,瞧人家酒樓年年賺大錢,也打算開個酒樓玩兒,那不是胡鬧嘛!”
老人家話,說著說著就跑偏了,又笑瞇瞇收回話來,給荼荼舀了碗老鴨湯。
“乖孫多補補,補補就不生病了喔。”
猜你喜歡
-
完結368 章

醫妃難撩:王爺,休書請接好!
前世,沐清凝慘死,本以為她的一生就如此慘烈收場了,可誰想到,一閉眸,她卻重生到了十二歲。那時父親未曾出事,流雲珠尚在手中,還有負了她的四王爺還在權鬥中聲名鵲起。沐清凝大喜,為了復仇,她製造偶遇,以無雙的醫術養成五皇子沈允陌,本想跟沈允陌聯手鬥渣男,可誰想四年後,他搖身一變成了大名鼎鼎的夜血侯。是夜,沈允陌勾起沐清凝的下巴:「皇嫂,你如此勾引本座,意欲何為?」
66.3萬字8 34373 -
完結1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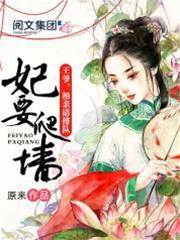
妃要爬墻:王爺,相親請排隊
不舉的七皇叔大婚了,新娘子卻是個產婦!新王妃喜堂產子,七皇叔雙喜臨門,卻從此戴上鉆石級綠帽。當冰山王爺杠上第一紈绔——“都用不著你奮斗本妃就給你生個便宜兒子傳承衣缽哪里不好了?”“傳承之事大過天,這種事本王還是必須親力親為的。”某妃撇嘴:“為?就你那小泥鰍,為個屁!”“是否能為,王妃嘗試一下便知。”感受著小泥鰍瞬間變鋼鐵,某女凌亂,眼睛一閉,咆哮道“你以為戴上個鋼筋套里面就不是豆腐渣了?”可素……為什麼萌萌噠兒子長得越來越像這條小泥鰍了?難道是……近墨者黑?
243.3萬字8 82466 -
完結69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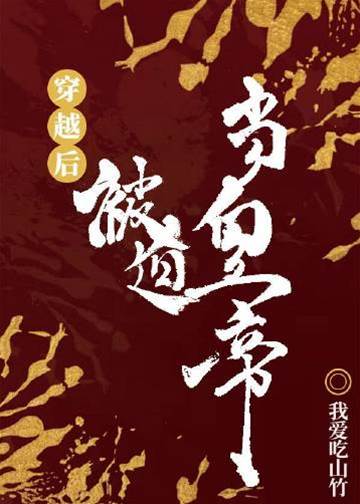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1013 章

娘子在上:將軍,雙世寵!
前世的她胸大、顏高,生活富足,家人牛逼,明明有一手好牌確被她打成了爛牌,晚年凄慘孤苦,最后自殺在那人面前時她方醒悟,她對得起自己,確對不起身邊所有的人。 重生后的她發下宏愿要和那個頂著女主頭銜的人成姐妹,和那個才高八斗注定發達得男人成兄妹...
152.8萬字8 209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