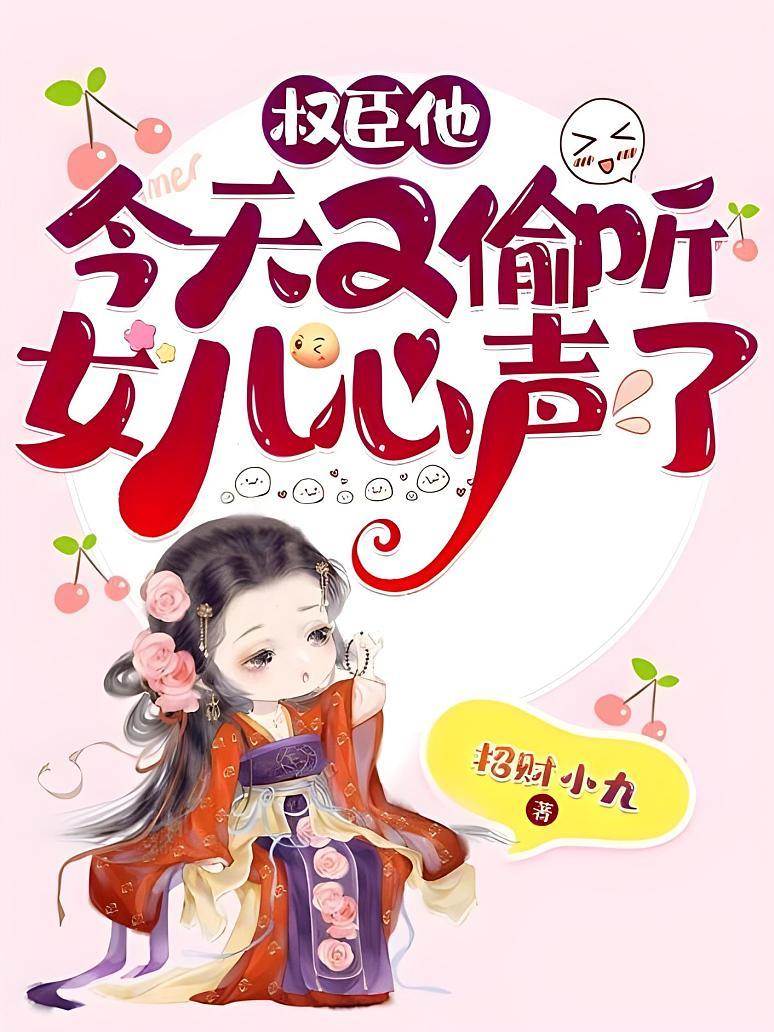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182章 第 182 章
十月廿七那天早上, 飄了點雪。
唐荼荼邁出房門時腳下一,這才看見地上覆了一層雪籽,薄泠泠的, 一碾就化。
這下棉襖也不夠用, 唐夫人從打好的包袱里翻出披風,一人一件裹上。
唐義山要去老宅跟爺爺住一陣子, 華瓊私底下與他囑咐,住得不適應就去那兒。只是國子監地界偏東, 離華瓊住的西市遠,老宅的爺叔伯又盛相邀, 小輩辭不得,就先回老宅住了。
全家只留下他一人, 雖然仆役書全留齊了, 邊不缺伺候的, 家里頭還是放不下心, 一家人各有各的擔憂。
唐老爺扶著兒子肩膀,諄諄教誨:“我兒切記好好讀書,業于勤, 荒于嬉,爹爹雖離你遠了, 你自己卻不可貪玩耽誤學業,等過年的時候, 再清閑。”
“孩兒謹記。”
唐夫人的悄悄話得背著老爺說:“你伯伯嬸娘那幾房人的脾氣……義山你自己也有數, 要是誰給你臉看了,別慣著他們,去你娘那兒住。”
“孩兒省得。”
珠珠淚眼婆娑:“哥,你跟我們一起走吧!”
當哥哥的不容易, 哄完爹娘,還得哄這小丫頭:“再哭要皸臉了,我每月給你們寫信,特特多給你寫一封,好不好?”
“好!說定了!”
他像模像樣地哄完珠珠,又笑著看向荼荼:“妹妹有什麼要囑托的?”
唐荼荼想了想:“好像沒有。哥哥很厲害,我知道的——既然爹要你發,那我就勸你多玩吧,學習要勞逸結合,別天天讀死書,多朋友,多出去走走,多看時政新聞。”
“需要幫忙的時候就跟娘說,別一人死扛。”
唐老爺背著手嘀咕:“不像話,不像話,荼荼這是心跟我作對呢。”
Advertisement
全家人都笑。
唐荼荼最后看了一眼這宅子。
住了九個月的宅子,尚不足夠讓唐家人生出不舍,誰對這宅子的留也沒深。
是“生”在這兒,長在這兒的,在這宅子里養好了神,才敢爬出去看看世界。
管家伯把大門落了鎖,隔斷了里邊的一草一木。
一行六輛馬車,十來匹馬,陣仗大。一路穿巷而過,走過各家門前,看門的家丁都探出頭,拱手笑祝了句“一路順風”。
路過容府時,大門開著一條小,里邊似有人影。
馬車轱轆轉了一圈就過去了,唐荼荼只看見半綢。
杜仲帶著仆役和藥,幾人沉默地在街門口等著,人人背了個小包袱。他拿出一封太醫署簽發的撥調信,請唐老爺過目。
他是太醫署考過試、掛了名、有行醫資質的大夫,有了這封撥調信,這就算是出外差,家里長輩托付過來了。
唐老爺雖沒見過他,一聽來由,自個兒補上了因果,連聲說:“好好好!小杜只管跟上,等到了縣衙,自會委派你事務。”
唐荼荼沖他揮揮手。
杜仲靜靜片刻,又垂眸去看地,與幾個仆役步行著跟在了后頭。
他們是要到城外租車的,城門外有客旅行,做馬匹、馬車租賃,有時也接托鏢生意,在直隸幾地來回行走。
每日進出京城的百姓絡繹不絕,天津還算是近途,雇個車夫,跟隨大部隊上路,一路的花用不算貴。
唐老爺一掃前陣子的郁氣,神氣揚揚的,隔著車窗都能聽著他的嗓門。
“快瞧,禮開城門了!”
唐荼荼從側窗探出頭,東方日出,晃得直瞇眼。
挑今兒出門并不是湊巧,是唐老爺的主意,說是要帶們看看大軍出征是什麼樣。唐家和去往北境的運糧兵并不一道兒,恰恰都是東城門出門,順路看看這陣仗。
Advertisement
一路差清道,兵部與禮部員送行。運糧兵早早在城外候著,極目去,全是捆扎實的糧車。
唐荼荼遠遠著傳旨站上城樓,于大軍前宣讀圣旨,城門上幾面龍虎幡獵獵鼓風,氣氛莊嚴肅穆。
三軍列方陣,運糧兵的棉外全套著薄甲,三萬人,站了好長,從城門下一直延續到遠方的深林中去。
被大軍截在城門外的百姓愣愣看著,半月前還因為“朝廷新征民伍”的事兒罵罵咧咧,這會兒全不吭聲了,揪扯出新的擔憂來。
這些活生生的兵,這些之軀,好多都是年、青年面孔,跟各家的兒郎沒什麼兩樣。
——三萬人站開就不到頭了,蒙古二十萬騎軍境,不會有事吧……
——運糧兵尚且披了甲胄,要上戰場打仗的兵得死多哇……
連最嘰嘰喳喳說小話的珠珠都噤口不言語了。看見姐姐抬起右臂,合攏五指,收肩,朝著那頭敬了個禮。
珠珠也有樣學樣,跟著立正敬了一個軍禮。
“好孩子。”唐荼荼腦袋,小丫頭扭著頭躲了。
等到清點軍糧與整隊之時,大軍最中心的那簇人便朝著駐亭走來。
最當中的二殿下一明鎧,護齊全,只出一張俊的臉,三軍目皆隨他行。
龍鱗一般的銀甲葉編綴排,三疊護肩更襯得他肩寬背闊,口虎頭紋赫赫威風,打磨亮得像一面鏡子,朝底下反出明燦燦的,是為“明鎧”。
還沒上戰場,這一大將風范就很懾人了。
四城門外都有駐亭,尋常的路亭和茶寮供百姓歇腳用,駐亭卻連著驛館,是員和軍驛兵歇腳用的豪華大亭,八角重檐,一個亭子占地百來平,很是威風。
Advertisement
唐荼荼遠遠和他對上視線,心思一,若無其事地往亭邊走。
一群小吏慌忙行禮:“請殿下安!”
晏昰:“不必多禮,諸位自去忙。”
送行的禮部典儀是個面孔,來唐家吃過酒的,與唐老爺寒暄著,唐老爺也不好先走一步,讓大軍看著自己隊伍的屁,那不統。他帶著夫人和以前的同僚說著話。
唐荼荼著廊柱站,還目視前方,人前假裝跟二殿下不認識。
兩人很有共識地沒扎堆站一塊兒,中間隔了兩個人的空當,外人眼里看不出親昵。
晏昰瞧了瞧這大棉襖,厚得不像話,還沒到數九寒冬呢,從頭到腳裹得就張臉了,到了冬天怎麼活。
他微微開合:“前夜只顧喝酒了,忘了與你說正事。”
唐荼荼:“哎,您說。”
晏昰被這個“您”梗得稍作停頓。
“江凜我沒帶上走,他年紀尚輕,對兵政事務不,還得再磨礪幾年。他這邊還有點事要收個尾,大約比你晚到半月,等去了天津,你督促他好好習武。”
此時是下半月,蕭臨風出來的日子,那年原籍就是天津,來京城考了個鄉試一直沒回去,被隊長拖拉著。
唐荼荼本想給隊長留封信,又怕蕭臨風從中作梗,專門改的留言,索把信托付給影衛,等下月初一再給隊長。
晏昰:“我手邊人,調度不開,只把叁鷹和芙蘭留給你,天津另有幾十探子。我給你的那枚私印絕不能丟,四品以下所有軍全可憑我私印調度,要是有應付不了的急事,你只管用。”
“出門在外別惹事生非,真惹了事兒,讓叁鷹傳信給我。”
唐荼荼想笑,又得憋著,哼了聲:“知道啦。”
Advertisement
遠三萬大軍,近的員和隨侍也有百二十,還有更遠道兩側被兵線戒嚴了的百姓,唯他是視線中心。那些視線眾星拱月圍著他,也隔出鮮明的界限來。
在這些人眼皮子底下,唐荼荼沒法自在,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失儀的。
他忽問:“怎不敢看我?”
這話親近得過了分,一下子把唐荼荼那些顧忌攪碎了一半。
扭過頭,打量他這一鎧甲,外殼锃亮。
唐荼荼視線往上挪。
他眉宇間是渾然天的英氣,別人眉尾細淡,他反而往濃黑的長,雙眉飛揚鬢,骨廓如削。
年桀驁之氣還沒褪干凈,子的擔子已經催著他做沉穩老的將軍,兩樣截然不同的氣質,全匯聚在一雙眼里,被上的明鎧襯得恍若神明。
好像他天生就該是這樣,好像他天生就該穿鎧甲。
唐荼荼沒敢手去鎧甲的質地,又忍不住問:“沉不沉?”
晏昰笑了聲:“手。”
他抬起一條胳膊,架到唐荼荼手臂上,立馬把手臂得墜下去一截。
唐荼荼:“好家伙!這一得三四十斤吧,打仗時候真這麼穿,能抬起胳膊來嗎?”
三四十斤算什麼,重甲還要再重十斤,巨盾兵全是力士,單手可舉七八十斤。尤其自個兒還一怪力。
晏昰覺得被小瞧了,抵著牙磨了磨:“怎麼說,我也是男人。”
唐荼荼咬著忍笑:“知道啦。”
不多時,傳令兵來報:“殿下!一切準備妥當,該是的時辰了。”
各營重新整隊,方陣換行軍陣,三萬人是推著糧車換個方向,都是鏗鏘的鐵甲鳴音。
驛亭里的員侍從,全長脖子看大軍。
趁著周圍沒人看這里,唐荼荼忙解下繡袋遞給他,飛快說。
“這里邊是遠鏡,昨晚上才送到我家里。時間太,只趕制出來兩把,放大倍率大概是十倍。今早有點霧,我照了照,基本能看清四里地外的太和殿殿頂,再遠還沒顧上測。”
“這是很厲害的東西,能站在幾里之外觀察敵,殿下好好用。”
唐荼荼有點憾:“可惜只能放大張角,鏡片度不夠,線太暗的小件就瞧不著了——使用說明我裝里頭了,等我改良好圖紙,之后的遠鏡會一批一批做出來,我托付了云嵐姑娘寄去邊關。”
琉璃廠是蕭家投了錢的,算是出資,云嵐居士腦袋里邊再擰,總歸還是個心懷家國大義的好尼姑,不會在這種事兒上拉后。
晏昰:“知道了,我上車再看。”
做放映機時,晏昰就聽說過兩回,大致聽懂了原理,沒抱太大期。
這會兒一聽,“四里地外能看見太和殿殿頂”,憑影衛的目力,每人都能看見,不足為奇。
可這是親手做出來的。
晏昰只當是禮收下,灑告別:“走了,你們也早點上路罷。”
唐荼荼辭別的話全涌到邊,還沒尋著個出口,后一群禮已經涌上去了,團團圍住了他。
兵部付虎符,又雙手呈上一桿紅纓槍,晏昰長|槍大展,甩了個槍花,紅纓高舉向天。
“拔營——!”
城樓上兩排號角朝著天吹,勢如長虹,大有震天撼地的氣魄,咚咚的鼓聲為和音,那是行軍鼓。
送行的員齊聲道:“臣等靜候殿下凱旋!”
呼出去的呵氣冒著白煙,吸進來的氣卻是冷的,凍得肺管子都疼。唐荼荼捂住鼻子暖了暖,才后知后覺——是有點難過。
不著頭的大軍阻隔了視線,只看著一片軍旗,紅的黃的黑的,繡著龍、繡著四神與各種異的,獵獵鼓風。
那條路一無際,風呼嘯過松林,聲如波濤。
再遠以后,鼓聲、號角聲全聽不著了。
唐荼荼忽然覺得有點懊惱,沒多叮囑幾句。
那是戰場啊,戰馬會失蹄,火炮會炸膛,一個回回炮能投下百斤巨石,炸得人仰車翻,后頭的神醫救不迭,命就留那兒了……
——呸呸呸,唐荼荼你個烏。
唐荼荼在自己上打了三下,珠珠看傻子似的看著。
“姐,快上車呀!咱們要走啦!”
唐荼荼應了聲,坐上車,捧著手爐不放了。
華瓊送的四馬車很寬敞,足夠荼荼、珠珠,連上幾個丫鬟全坐上去。
唐老爺意氣風發,剛看完大軍,滿心豪壯志,跟家丁要了匹馬,踩著上馬石上去了,姿倒也灑。
“走嘍!隨老爺我赴任去!”
……
晏昰把遠鏡罩在眼上,跟著說明書,作生疏地旋轉對焦。
視野跳躍幾下,立即從模糊轉為清晰。
二里地之外的外城墻一躍到了眼前,箭樓上站哨的兵懶,塌著腰沒站直,正紅的旌旗被大風刮得舞,撲打在那哨兵上,甚至能看清哨兵甲胄的,看清旌旗被風吹皺的褶子。
晏昰驚得一個后仰,后背撞在馬車壁上。
此等奇!什麼來著,遠鏡!
這名兒毫不響亮,哪里配得上此等奇!該千里眼才對。
晏昰拿在手中翻來覆去地看,想拆開木筒看看里頭構造,這一細瞧,他眸一。
木筒側面有字,是刀尖刻上去的兩個字,橫平豎直。
——平安。
是倉促刻的,沒有筆,橫短了,豎長了,可還是好看得不得了。
他挲著幾條刻痕,心里那棵細弱的芽輕悄悄破土,探出頭,放肆地汲取養分,催芽拔節,一節一節撞著腔,要從他心口沖出來。
晏昰推開車窗,朝后去。
軍隊快,唐府那一行人遠得快要看不清了。
他喝道:“廿一!你下馬。”
廿一不明所以地讓了馬,看著殿下飛上馬,狠狠一揚鞭,朝著城門的方向沖去了。
耳邊風聲驟起,在他心上豁開一道口子,把年人建功立業的野心,還有一團愚魯遲鈍的意,一腦地鑿進他心里去。
寒風如刀割臉,和著霹靂的馬蹄聲,涌起無邊的暢快來。
后的影衛嗷嗚喊著:“殿下干嘛去?都拔營了怎麼還走回頭路啊?回頭路不吉利!”
沒聽著主子應聲,幾名影衛紛紛駕馬追了上去,揚起一大片煙塵黃土。
一片馬蹄聲朝著這邊飛踏而來,唐荼荼有所地掀起簾子。
只見北方一騎絕塵,一路劈開重重兵甲,千里走單騎一般朝著沖來。
到了近前,他驀地提韁勒馬,在唐家全家人驚愕的目中,打馬近了的車窗,俯頭低聲問。
“你死前,年齡幾許?”
唐荼荼啞了,腦袋里無數念頭瘋狂轉。
珠珠:“讓我聽聽!姐!唔唔……”
小丫頭一個勁兒地往這邊,唐荼荼怕珠珠聽著一字半字,拼命摁著珠珠的臉往遠離的方向推。
晏昰低笑一聲,笑聲從中溢出,結連滾,換個說法又問了一遍。
“你上輩子死前,活了多大?”
唐荼荼心噗通噗通跳起來。
晏昰:“回話。”
他離得太近了,幾乎是頭抵著頭的耳語。那是鐵甲的味道。
唐府眾人見鬼似的瞪直眼,啥也聽不著,只看見二殿下和自家二小姐“耳鬢廝磨”,唐老爺的眼珠子快從眼眶掉出來了。
唐荼荼嗓子發干,頭發,指尖戰栗,整脊梁骨都別扭地這節往左,那節往右。
坐也不是,傾湊過去也不是,后仰也不是,手全不知道往哪兒放。
結結回:“二、二十六。”
眼睛眨都不敢眨。
晏昰“哈”了聲,像是有點失,又像認了命。
他抓著馬鞭直起,重新笑得華綻綻,上鎧甲似披了天。
“知道了。到了天津好好念書,等我凱旋——珍重。”
余音很輕地打了個旋,撞耳中,唐荼荼還沒穩住心跳,二殿下狠狠鞭馬,追著大軍去了。
摁著鼓噪的口,順了順呼吸,也沒把心臟一拍快過一拍的跳摁下去。
“姐!姐!”珠珠喚著,驚奇中著歡喜,歡喜中帶著八卦,眼睛快要瞪出來了。
“是不是他?!我見過他!那晚上就是他!我記得這個臉……唔唔!”
八個家丁驚悚地互相著,騎著馬的唐老爺抖抖索索坐不住了,唐夫人那輛車車窗前了好幾個嬤嬤的腦袋。
車夫喚著:“快往那邊坐坐,車要翻了!”
各種混。
唐荼荼忽然懶得顧忌那些繁文縟節,半個子躍出車窗,朝著遠去的一人一馬揮了揮手,喊聲裹進風里。
“殿下珍重!全須全尾地回來啊!”
馬上人背著,高高揮了揮手。
作者有話要說:噠噠!!!第一卷完!!!
講一下下卷安排(有一丟丟劇)。
.
.
.
.
.
天津卷按篇幅大致分為四部分,不跳時間,會一點點寫過去。
第1部分是雙線,鄉村醫改的初步嘗試,還有邊關戰況,這部分兩人不在一起,基本是“書”流,中間只見一次面。時間線大概是一個月(現實一個月),但我對醫改不,如果寫得不順手,會酌這部分。
只想看戲的老板們可以跳,11月再見啦~
第2部分是建設最縣城,駕下天津,這部分倆人是朝夕相的。
3、4部分是清剿海患以及水軍整改,戰火中的萌芽,小大大大甜,打仗會很慘烈。
本卷主角團是荼荼、二殿下、唐家、江隊長和蕭臨風、杜仲,還有第四位大神隊友。
明天休息一天,我整理一下廢稿和大綱,然后發車!
國慶節快樂!
猜你喜歡
-
完結1566 章

來人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啥? 身為王牌軍醫的我穿越了, 但是要馬上跟著王爺一起下葬? 還封棺兩次? 你們咋不上天呢! 司夜雲掀開棺材板,拳拳到肉乾翻反派們。 躺在棺材板裡的軒轅靖敲敲棺材蓋: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282.6萬字8.18 227621 -
連載1841 章

重生後我嫁了未婚夫的皇叔
前世,她是貴門嫡女,為了他鋪平道路成為太子,卻慘遭背叛,冠上謀逆之名,滿門無一倖免。一朝重生回十七歲,鬼手神醫,天生靈體,明明是罵名滿天下的醜女,卻一朝轉變,萬人驚。未婚夫後悔癡纏?她直接嫁給未婚夫權勢滔天的皇叔,讓他高攀不起!冇想到這聲名赫赫冷血鐵麵的皇叔竟然是個寵妻狂魔?“我夫人醫術卓絕。”“我夫人廚藝精湛。”“我夫人貌比天仙。”從皇城第一醜女到風靡天下的偶像,皇叔直接捧上天!
331.1萬字8 71759 -
完結332 章

首輔寵妻錄
侯府嫡女沈沅生得芙蓉面,凝脂肌,是揚州府的第一美人。她與康平伯陸諶定下婚約後,便做了個夢。 夢中她被夫君冷落,只因陸諶娶她的緣由是她同她庶妹容貌肖似,待失蹤的庶妹歸來後,沈沅很快便悽慘離世。 而陸諶的五叔——權傾朝野,鐵腕狠辣的當朝首輔,兼鎮國公陸之昀。每月卻會獨自來她墳前,靜默陪伴。 彼時沈沅已故多年。 卻沒成想,陸之昀一直未娶,最後親登侯府,娶了她的靈牌。 重生後,沈沅不願重蹈覆轍,便將目標瞄準了這位冷肅權臣。 韶園宴上,年過而立的男人成熟英俊,身着緋袍公服,佩革帶樑冠,氣度鎮重威嚴。 待他即從她身旁而過時,沈沅故意將手中軟帕落地,想借此靠近試探。 陸之昀不近女色,平生最厭惡脂粉味,衆人都在靜看沈沅的笑話。誰料,一貫冷心冷面的首輔竟幫沈沅拾起了帕子。 男人神情淡漠,只低聲道:“拿好。” 無人知曉,他惦念了這個美人整整兩世。
53.2萬字8.33 6779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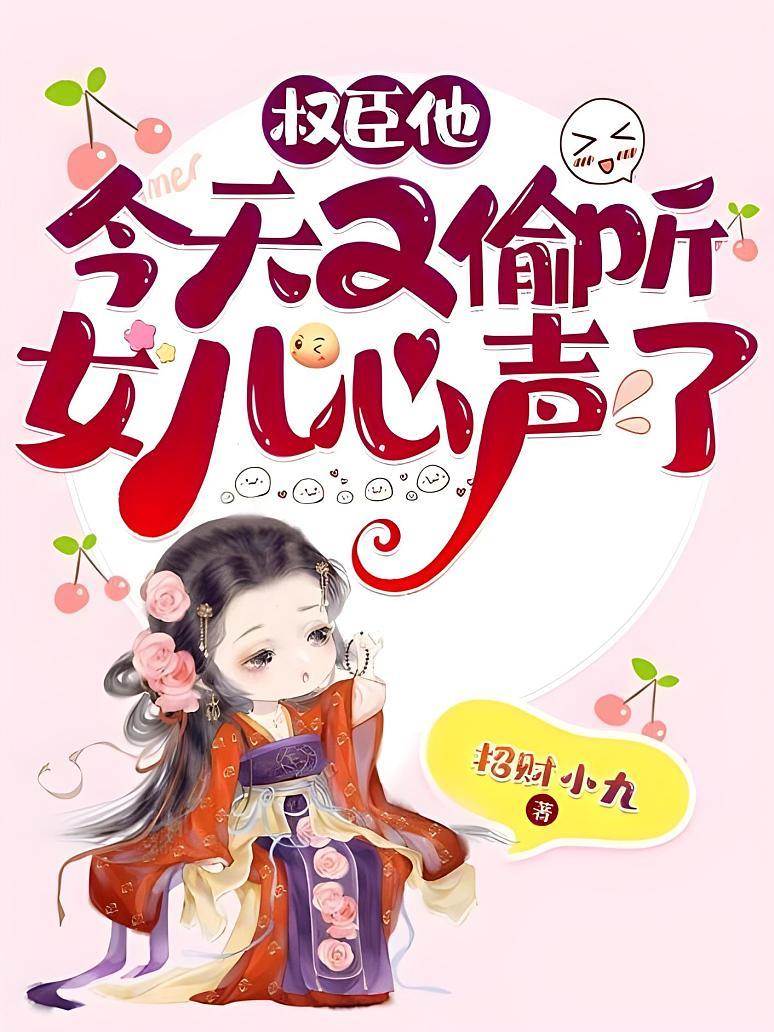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