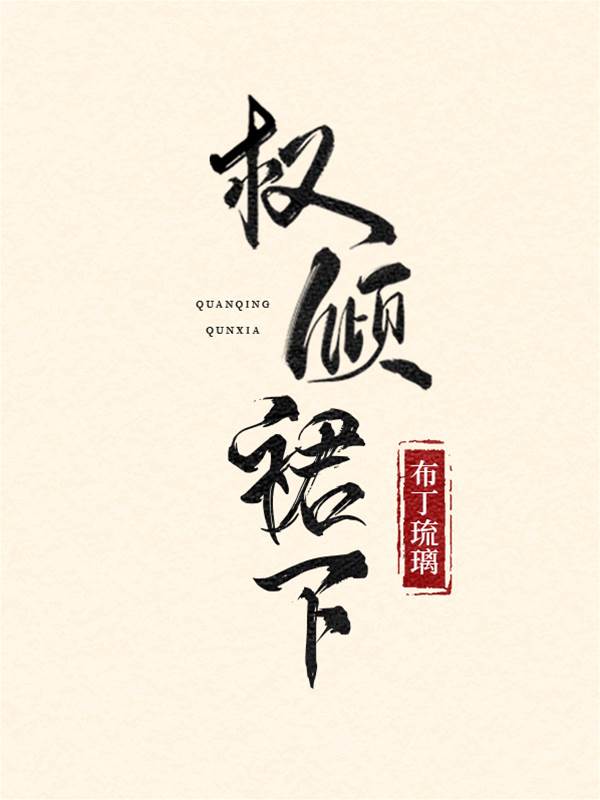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188章 第 188 章
信走的是暗驛, 影衛專門的言報之路,隨天津的書一起。
這些“書”多數是送往宮里的折子,各地的驛、軍驛都是地方出資籌建, 地方管轄的,政治影響很大——吏治清明的地方,驛站運營得好;員上下沆瀣一氣的地方,驛淪為虛設,遞上去的折子總是要經幾道手。
膽小的庸敢截折子,膽大的貪惡吏,敢把折子改得面目全非,重新呈上去。
其后,折子進閣是一重關, 進前又是一重關。
盛朝廣開言路,允許小吏越級上奏天聽,可天下每月的折子何止千百,一重重的員替皇上“分憂”, 清簡折子, 能呈到皇上眼跟前的,每天撐死了也就十封。
剩下的,全在暗底下爛著。
該上去的奏事折沒遞上去,不該上去的請安折遞上去了……背后有無數雙控政局的手,致使言路凋敝衰微,阻斷了清直呈天聽的路。
影衛從南到北搭建了一張巨大的信息網,當然, 他們做的也不是什麼地道事兒,他們會在書傳遞過程中攔截抄錄,篩檢出一切關鍵信件, 整理好送到主子面前。
殿下一份,太子一份,事兒大的還會給老國公遞一份,請老國公幫著審度,背后又有無數幕僚文士一齊分析,是為“足不出戶,知天下事”。
若放到后世,晏昰毫無疑問是個信息狂,天下事在不在掌中另說,他每天無數信息打眼前過,大事小事全得知。
叁鷹寫好信,才剛送到靜海縣的樁點,那扮作掌柜的探子賊兮兮笑著,雙手端來一只木盒。
“新鮮的,一刻鐘前剛到。”
是只紫檀木盒子,沒上鎖,盒子扁平狹長,還涼冰冰得凍手,盒面上覆了層細白的霜。
Advertisement
瞧叁鷹一臉的狐疑,探子笑著說:“我可沒敢打開。這東西外頭裹了個冰盒送來的,天冷,冰還沒化干凈呢,不知裝的是什麼時鮮。”
叁鷹晃了晃,隔著盒子聽了聽靜,覺里邊的東西輕飄飄的。
他莫名其妙地端著這木盒回去了,給芙蘭。
唐家落腳的那宅子掌大,幾個院里全住滿了人,他二人不好往進混。好在這兩天趙夫人時時吩咐丫鬟過去送東西,芙蘭扮作丫鬟更容易混進去。
澡堂出事的第四天上午,唐荼荼才拖著一疲憊回家。
在縣衙后院住著,事事不便,腳腕上的傷也才剛結痂,好幾天沒洗澡了。
進門就要熱水,備好干凈裳,唐荼荼舒舒服服泡在大浴桶里,每一個孔都舒坦了。
這一進的屋,除了個屏風隔斷什麼都沒有,簡陋得一眼能到頭的屋子里,不知何時多了抹亮。
桌上放了只彩瓷瓶,有一只小白花豎在里邊,有點蔫吧了,耷拉著腦袋,花枝倒還。
房間小,唐荼荼站起來一手就能夠著,拿在手里仔細瞧。花是淡淡的白綠,分了三層花瓣,每層都是五朵,層層疊疊攏著淡黃的蕊。
就這一朵白花,說它好看是抬舉它,唐荼荼湊近聞了聞,也不怎麼香。
“芳草,這什麼花兒呀?都蔫吧了,怎麼還不扔啊?”
外邊給守門的芙蘭頭一哽,著鼻子裝芳草的聲音。
“小姐,那是從五百里之外快馬加鞭送回來的綠萼梅,還有一封信,在花瓶底下呢,您不看看嗎?”
唐荼荼心思分了岔,沒注意到這聲音的蹊蹺,手在臟服上蹭了蹭,過那封信。
信封上一個字沒寫,拆開里邊,寥寥三行字。
Advertisement
——山中有一溫泉谷,路過時見三棵野梅樹逆時生長,初初破蕊,倒也別致。
——已平安到上馬關,勿念。
嘖。
唐荼荼心想:雅致人啊,大老遠地送一梅花,多浪費人力力。帶點特產,帶點風干牦牛也好呀。
卻怎麼也收不住角的笑,笑得想在浴桶里跑圈,想潑水玩。
拿起來又逐字看了一遍,這回臉上一燒,還以氣音“呸”了一聲:誰念你了!安安心心打你的仗。
外邊珠珠喊,一聲“姐——”剛開頭,房門就被推開了,唐荼荼手忙腳地把信塞進臟服里。
手一,花瓶罐子噗通掉地下,碎了四片。
唐荼荼:“……”
珠珠趕沖上來:“哎呀這麼好看的瓶子,姐你干嘛摔了它呀?”
唐荼荼反過來嚷:“你干嘛沖這麼急啊!你……”
氣死個人。
看見珠珠,忽的想起了前兩天在吉祥酒樓吃飯時,有個雅間名,那個詞什麼來著?
“什麼寄梅花?什麼意思來著?”
“驛寄梅花,驛站的驛。”珠珠脆聲說:“劉宋朝有一個詩人,他住在江南,他的朋友是鮮卑人,住在長安。國家在打仗嘛,兩人的友全靠書信來往。”
“有一回詩人走在路上,遇見了一個送信的驛使,要往北方去,就說,‘哎呀,你幫我帶一封信給我的好朋友吧’。但是驛使不耐煩等他,詩人只好從路邊折了一枝梅花,匆匆寫了幾句詩。”
“前兩句我忘了,后邊兩句是——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歌頌了兩人偉大的友。”
唐荼荼角的笑一秒拉平。
“哦。”
房頂上的芙蘭聽著里邊姐妹倆胡謅八扯,心拔涼拔涼的。
*
Advertisement
而此時的邊關。
“殿下!殿下!收著千里眼啦!”
一個大漢猛地掀開帳簾,兩旁侍衛還沒來得及提槍攔下他,葛二將軍靠著一蠻力,撞開兩人沖進營帳了。
晏昰披坐起,攏了個松散的髻。昨夜突擊哨衛營,查夜里宿衛夠不夠警惕,他睡下時天快要亮了。
“殿下,這是太子親自指了小將護送過來的,好大兩箱子,不知道帶過來多把千里眼。”
這蠻漢捧著一個大箱,以與自己不符的、非常小心翼翼的力氣,把箱子放到桌上開開。
里邊是一排簇新的遠鏡,面上涂了漆油,锃亮亮的。
晏昰看著他,在這套相似的眉眼中有些許恍神。
這是赤城守城將葛規表,葛循良一母同胞的弟弟,原本都是赤城人氏。
葛家上頭的祖宗是學問人,給兒子取名也取得雅致,恭謹循良、行應規表,要他們做善人,行善事,做人做事謹守尺度,別出格。
老祖宗對子孫的期冀全藏在名字里了。可惜兄弟倆都奔著歪路長,個頂個的五大三,腰圓臂鼓,得盯著,罵著,他們定期修理儀容,不然一臉大胡子油得能結綹,起了戰事時活像兩頭野熊。
但軍中將領各有天,智勇雙全的不見,智如諸葛七竅玲瓏心,勇如關公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那是野史,聽個熱鬧也就罷了。
為帥者,是得會調度人才,不可苛求人才全如你心意。
擅謀略的,肚子里滿腹折曲,往往也會有多疑的病;擅營兵布陣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最是重視報,但敵多變,有時探子不一定能鋪出去,常常人閉目塞聽。
也同樣需要有葛家兄弟這樣的莽夫,憑著一莽悍剽勇,毫不顧慮地往前沖,往往有奇效。
Advertisement
可惜……
晏昰目從他臉上移走,轉到腦子里的是另一重猶豫。
葛規表帶的兵,軍中謔稱“蠻牛陣”,也常常有人胡,喊他“牛將軍”。這一支兵練兵練的是穿重甲、騎悍馬,馬也是肚腹披甲,連人帶馬加上鐵甲,一將近三千斤。
一遇大戰,立刻轉為前鋒營,因為分量太重,馬跑不快也跑不遠,專門用來沖散蒙古騎兵軍團,一旦能沖進去,就如蠻牛一樣在敵人上狠狠掀開了口子。
只是前鋒營,怕是有去難回,這一戰起碼要折損十之七八。
葛循良戰死,他那獨子還是沒消息,葛家就剩這一個男丁了。一臉大胡子底下全是因寒風和干燥崩裂的口,常常人忘了、又冷不丁地想起來。
——這青年今年二十四,還沒娶妻生子。
葛規表正拿著遠鏡挨個檢查,后頭一排將領魚貫而。
“老遠就看見牛將軍扛著好東西回來啦!是不是咱們的千里眼到啦?”
“可算是能人手一個了。”監揶揄道:“殿下寶貝他那個,誰借也不讓,弄得咱們一伙人只能著用一個千里眼,每回爭來搶去的,新的再不送來,遲早打架。”
沒法兒。廿一心里發笑:誰讓姑娘只親手做了倆,還刻了“平安”二字,殿下平常都拿棉套包著,能舍得拿出來敵都算是不容易了。
“走走走,上城墻試試這新寶貝去!”
一群將軍前后腳爬上了城樓,登高遠。
城墻上寒風凌冽,又因為圍護城門的甕城與左右兩箭樓,擾得大風向,雪籽刮在臉上如刀割。
天天見雪籽,卻連地皮都覆不住,這地方始終下不起一場像樣的雪來。
“怎麼灰茫茫一片?我這眼是不是壞的?”
“哈哈哈蠢驢,你得調這旋,自個兒轉一轉。”
“胡監,你拿反了。”
“好家伙!當真是千里眼,得可真遠啊,我怎覺得這套千里眼比頭一套看得還遠?”
“想是改良過了——殿下來瞧瞧!”
晏昰接了一個新的,看見上頭拴了繩,一猜就知道用意了。
這群糙漢,看著不修邊幅,其實常年在邊關苦寒之地駐守的將領,都知道憐惜力。
這千里眼他們用得很珍惜,知道燒琉璃不是容易事兒,新的一送過來,就往側面鑿了眼兒,拴脖子上,這樣不會摔了磕了。
晏昰:“確實是改良過了。”比他那套能得更清楚,視野里的線很好。
廿一上前道:“還有一套更大的千里眼,殿下可要裝上瞧瞧?”
不用晏昰說,一群將軍已經嗷嗷地催了。
這套遠鏡比所有千里眼都金貴,傳令兵提著箱子上城樓,不過是上了幾道臺階,后的文士連聲叮囑:“慢點慢點,這東西經不住一點磕磕。”
傳令兵只得兩夾著走,步子都不敢邁大了。
這臺遠鏡是個大家伙,只有一個筒,模樣像個袖珍的火炮,將近有一條胳膊長,鏡片也大,下邊帶三條的木架。
那文士小心翼翼,并不敢往城墻上架,說是“怕風吹走”,惹得一群將軍罵他事兒多。最后搬來主帥桌案,把這臺千里眼穩穩地支在了桌上。
天正亮,草原上只有清早霧大,日出之后永遠是一片綠汪汪的原野,視野很好。
文士撅著屁蹲在千里眼前,姿勢不雅,他只調試了一小會兒便起了,展臂笑說:“殿下請。”
晏昰沉腰扎了個馬步,學他剛才的樣子瞇起一只眼睛去看。
他呼吸陡然一輕。
“那是……?”
北元草原作戰,千里行軍,背后沒城防可倚靠。他們的軍帳蔓延開幾里地,用眼是看不清的,只能看著地平線上浮著一條花白的細線,那是蒙古氈包的。
戴上唐荼荼送他的千里眼,能多看到無數麻麻的黑點,知道那是兵,那些兵在做什麼完全看不清。
即便如此,那也是難以想象的便利了,足不出城,遠隔十里地之外就能知道敵方向,任哪一位將軍都得倒吸一口冷氣。
而罩上這一臂長的筒狀千里眼,敵營里的人竟然顯了形,雖然線不足,敵兵只是影影綽綽有一個影,卻足夠他們連看帶猜地知道敵軍在干什麼了。
旁邊幾位將軍與監連尊卑都不顧了,幾乎是把晏昰了開,貓著腰湊上去,驚得亮嗓子嚎了兩聲。
“這得多遠?”
“得有二十里地了吧!”
“老牛別晃我,頭暈得不行!”
晏昰招手喚來那文士:“這是誰做的?是賀……是唐姑娘留下的圖?”
文士喜上眉梢:“不是唐姑娘,是知驥樓一位大才,與工部的師傅嘗試半月,做出了這套能得最遠的。”
要是唐荼荼在這兒,大概會驚喜地抱起那文士轉三個圈,這文士實在厲害。
唐荼荼走前只留了十套鏡像圖,各種尺寸與厚薄的鏡片都有,讓琉璃廠盡量多燒各種厚度和尺寸的鏡片,給知驥樓的文士們,讓他們多組裝,多嘗試。
鏡學有非常非常多的應用,遠遠不止放映機用到的聚鏡、放大鏡倆作用。但唐荼荼絕沒有想到丟給他們一個思路,他們能做得這樣好。
遠鏡的清晰度、張角(就是取像范圍)、最遠距離,全會到鏡片質量影響。后世,普通的手持雙筒遠鏡一般是10倍放大,可以理解為把1000米外的拉近到100米再看;或者理解為讓遠原本1米高的,看起來像是以眼在看10米高的。
倍率再高的遠鏡全要帶三腳架固定,不然手一哆嗦,眼里的圖像就錯開幾百米了。
倍數越高,對鏡片質量要求也越高,越厚的鏡片,其路折反越復雜……燒琉璃的過程中哪怕混塵土那麼大的一丁點雜,鏡片就不是高的了,遠能看出一朵花來。
遠牛羊群,民屯里的百姓安居,哪里是草原,哪里有小片的沙丘,全能看在眼中。
可惜將里邊沒雅人,不樂意看草看羊,鏡頭對著敵營一個勁兒地瞅。
“真近啊,這怎麼能千里眼,該萬里眼、萬萬里眼才對!”
“一定要藏好這東西,誰敢弄丟了、弄壞了,軍法置。”
他們挪著鏡頭,看到眼花頭暈之時,甚至從敵營中找見了敵方主帥的營帳。
軍隊宿營時,往往不會把主將包裹到軍營最中間,不然遇上了夜襲,敵軍一門心思往最中間沖,主將也得栽個跟頭。
但主將下榻之,一定有最多的軍士圍護。
“哈哈,找著蒙哥營帳啦!”
“取弓來——他老子的!”
剛說完這話的將軍就被痛罵豬腦子了。
……
真厲害。
晏昰聽著他們的笑鬧聲,手指微蜷,習慣地蹭了蹭,像是隔著半個營,挲到了他那套遠鏡上“平安”二字。
浩瀚無邊的草原是荒涼的,城墻下,只有背各旗的傳令兵進進出出,帶來各方消息。
這是關第二城,位于赤城東南面的上馬關。
上馬關本是一座中型關,因為城下是一座矮山,在地勢平緩的北境肖似一塊突然長出來的上馬石,借著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之勢,取名就選了這一優勢。
這座關,兵甲重都不算太富余,好在月從大同和承德兩個方向急調來邊兵五萬,將此地簇擁重關。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本文齁甜,雙潔,雙強,雙寵,雙黑)世間有三不可:不可見木蘭芳尊執劍,不可聞太華魔君撫琴,不可直麵勝楚衣的笑。很多年前,木蘭芳尊最後一次執劍,半座神都就冇了。很多年前,太華魔君陣前撫琴,偌大的上邪王朝就冇了。很多年後,有個人見了勝楚衣的笑,她的魂就冇了。——朔方王朝九皇子蕭憐,號雲極,女扮男裝位至儲君。乃京城的紈絝之首,旁人口中的九爺,眼中的祖宗,心中的閻王。這一世,她隻想帶著府中的成群妻妾,過著殺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奢侈糜爛生活,做朵安靜的黑心蓮,順便將甜膩膩的小包子拉扯大。可冇想到竟然被那來路不明的妖魔國師給盯上了。搶她也就罷了,竟敢還搶她包子!蕭憐端著腮幫子琢磨,勝楚衣跟大劍聖木蘭芳尊是親戚,跟東煌帝國的太華魔君還是親戚。都怪她當年見
118.2萬字8 18555 -
完結310 章

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李泠瑯同江琮琴瑟和鳴,至少她自己這麼覺得。二人成婚幾個月,雖不說如膠似漆,也算平淡溫馨。她處處細致體貼,小意呵護,給足了作為新婚妻子該給的體面。江琮雖身有沉疴、體虛孱弱,但生得頗為清俊,待她也溫柔有禮。泠瑯以為就能這麼安逸地過著。直到某個月…
47萬字8 684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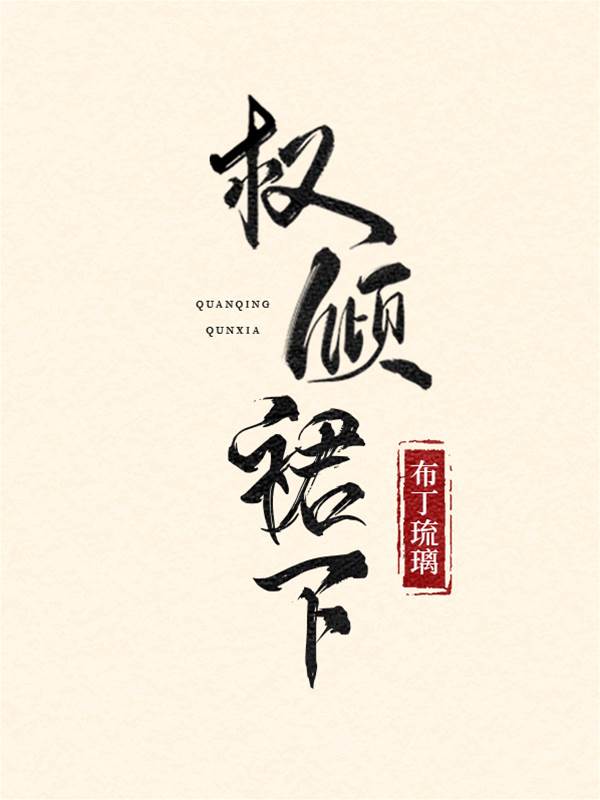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019 章

攝政王今天又在哄王妃
穿成了被繼母虐待被繼妹搶婚的懦弱伯府大小姐。云嫵踹掉渣男虐廢小三,攪得伯府天翻地覆。接著一道圣旨將她賜給了攝政王。攝政王權傾朝野,卻冷血無情,虐殺成性。人人都以為云嫵必死無疑,仇人們更是舉杯相慶等看好戲,豈料……在外冷血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卻天天柔聲哄著她:“寶貝,今天想虐哪個仇人。”
184.8萬字8 38042 -
完結183 章

誤酒
朝和小郡主黎梨,自幼榮華嬌寵,樂識春風與桃花,萬般皆順遂。 平日裏僅有的不痛快,全都來源於她的死對頭——將府嫡子,雲諫。 那人桀驁恣肆,打小與她勢同水火,二人見面就能掐。 然而,一壺誤酒,一夜荒唐。 待惺忪轉醒,向來張揚的少年赧然別開了臉:“今日!今日我就請父親上門提親!” 黎梨不敢置信:“……你竟是這樣的老古板?” * 長公主姨母說了,男人是塊寶,囤得越多就越好。 黎梨果斷拒了雲諫送上門的長街紅聘,轉身就與新科探花郎打得火熱。 沒承想,那酒藥還會猝然復發。 先是在三鄉改政的山野。 雲諫一身是血,拼死將她帶出狼窩。 二人跌入山洞茅堆,黎梨驚詫於他臂上的淋漓刀傷,少年卻緊緊圈她入懷,晦暗眼底盡是抑制不住的戾氣與委屈。 “與我中的藥,難不成你真的想讓他解?” …… 後來,是在上元節的翌日。 雲諫跳下她院中的高牆,他親手扎的花燈猶掛層檐。 沒心沒肺的小郡主蜷縮在梨花樹下,身旁是繡了一半的香囊,還有羌搖小可汗的定情彎刀。 他自嘲般一笑,上前將她抱起:“昨日才說喜歡我……朝和郡主真是襟懷曠達,見一個就能愛一個。” * 雲諫出身將府高門,鮮衣怒馬,意氣風發,是長安城裏最奪目的天驕。 少年不知愁緒,但知曉兩樣酸楚。 一則,是自幼心儀的姑娘將自己看作死對頭。 另一則,是她不肯嫁。
27.1萬字8 8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