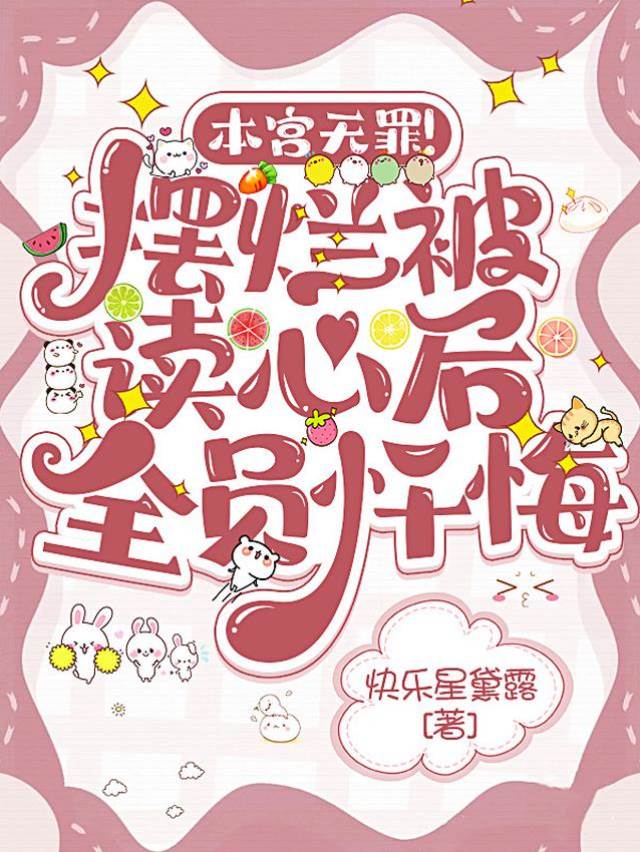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209章 第 209 章
一上車, 不停當地問了好多話。
“二哥你怎麼來啦?你從哪兒過來的?你過年是回京了嗎?京城里邊一切可好?我這兒都好長時間沒收過京城的信兒了。”
晏昰一句不進去,自個兒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唐荼荼忽然頓住口,臉上有點燒:“你怎麼一直看著我啊?”
他靠在車壁上, 好像有點疲憊, 也分不清是疲憊,還是為了靠后坐坐、借著細細打量。
窗外的冷不盛, 照得這雙眼睛愈發幽邃,可他下眼瞼的笑弧也明顯, 淺淺一條,兜住了兩汪暖意。
唐荼荼臉:“殿下不認得我了?我臉上沾墨了?”
晏昰笑說:“瘦了。”
“沒瘦。”唐荼荼耳有淺淺的熱意涌上去, 裝模作樣避開視線:“今兒不冷嘛, 穿得了點。”
“這邊口味吃不慣?”
“吃得慣,很好吃, 二哥還沒嘗過正宗的天津菜吧?我請你吃!哎呀,還沒到飯點呢。”
“不急。”晏昰掀起車簾看前頭, 大門前的隊伍曳了長長的尾, 拖到了側巷。
他不知道這是在做什麼, 的傳信大概是岔在路上了,看見這麼些人,奇道:“這又是什麼新鮮主意?”
不論他問什麼,唐荼荼都止不住笑,把養生順口溜和全民健大比的事兒全給他講。
“今兒初六, 從今日開始報名,截止到正月十二,大比從十五元宵節開始, 一連比到月底……我還學了捶丸, 跟我們那時候的高爾夫很像。”
講得眉飛舞, 晏昰笑著聽著,分神觀察著四周位置。
這地方選得不偏,挨著縣道,南邊又臨著那條泄洪河,水的時候,干涸的時候多,剝蝕出一片碎石塊。以前用作磚廠,就地取材,位置倒是選得不錯。
Advertisement
但是印坊。
“怎麼想起來建印坊?”
唐荼荼:“那當然是做過調研啦,全天津就一個刻坊,挨著津灣口,我們這縣里頭什麼也沒有。縣學里頭的學生有四五百人,除了孔孟書沒缺過短過,剩下的教材書,常常都是學生自己手抄的——二哥在京城沒見過這樣的事兒吧?”
“雖然老話說‘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但教材書最重要的是準確,不可錯一字,這樣來回抄寫,總會有錯的地方。”
“提振民生,先抓教育嘛。再者說,建一個印坊好多多,趙大人已經去求見漕司了,要是漕司那邊沒什麼話,我們甚至能印報紙。”
晏昰被的話引著走:“報紙?”
“二哥你是不知道啊,縣衙的邸報來得特別慢,我今兒早上看著的報紙是臘月初三的,這都一個月前的事兒了——這還是衙門報,都來這麼慢,像咱京城《崇實》這樣的民報,幾乎是見不著的。”
問:“京城的民報是誰編寫的?”
晏昰問住了,想了半天。
“各上府皆有進奏,向京城部首陳事。最要的事兒送宮,那些不值當皇上看的事全編寫民報,分發給國子監和各書院,坊間書肆可以自行印刷。”
唐荼荼:“原來如此,難怪天下學子都向往京城,教學資源差太多了——二哥你等著看吧,到我爹離任,我們縣肯定能看上最新的報紙。”
晏昰低低笑了聲:“我信。”
外頭的影衛一聲不吭,呼吸都輕淺了。總有這樣的本事,讓周圍人都認真聽說話。
晏昰又了外頭連綿十畝地的印坊,只用了一半,左半邊還空著,不知道要用作什麼。
Advertisement
“這些,都是你想出來的?”
唐荼荼上了車就沒停過笑:“那哪兒能啊!我爹、趙大人都出了不力,還有一位縣丞,也是厲害人,總能想到別人想不著的細。”
的來信里,從不吝嗇言語,吃著了什麼好吃的,著了什麼有意思的,通通要寫給他,更多的時候,卻是天馬行空的想象——這顆腦袋瓜里藏了無數鮮活有趣的想象。
而這樣的正事、大事,從來都是一言帶過去。
每回接著信,晏昰只看著高興了,竟忘了也天天做著正事。
像一只志存高遠的鶴,見過的世面越多,雙翅越健壯,什麼也降不住,總要揮扇著翅膀,飛往越高越遠的地方去。
“那順口溜比我想象中傳得更快,最開始想著,怎麼也得先印出來吧。誰知這邊才往布告欄上,坊間就已經傳抄開了——二哥你們一路進城,聽著街上唱順口溜的沒有?”
晏昰:“聽著了,我們沿河過來的,河上結了凍,有人冰玩。街邊曲苑班子全在念這順口溜,打著梆子七件編了曲。”
唐荼荼:“嘿嘿,見笑了見笑了。不知怎麼傳得那麼快,葉先生說快要傳遍城里了,我還沒信呢。”
說著這些,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彩。
這攪神的家伙,晏昰什麼正事兒都聽不進去了,只看著笑,下頷鋒銳的線條都圓了角。
他下上那一條道道,迎著天,總算了些端倪。
唐荼荼吃了一驚:“二哥你臉怎麼啦?”
晏昰抬手作勢輕輕了,其實指頭都沒敢挨上去,怕這麼一就把干涸的痂蹭下來。
他這樣的小心,那一定是疼的。
唐荼荼不著他臉看,自然分不清這是新傷舊傷、深傷還是淺傷,滿眼憂慮:“戰場上傷著的吧?刀劍無眼,要當心啊。”
Advertisement
“我省得。”
唐荼荼:“您不是坐鎮后方指揮調度麼,怎麼還親自上戰場啊?”
智計過人的二殿下,忽悠人從不需要打腹稿:“為帥者,偶爾,也是要上上戰場的,好提振士氣。”
外頭趕車的、牽馬的,全寂了聲,不知哪個笑點低憋不住的,出“噗噗”兩聲笑,很快又沒了靜。
晏昰把臉面徹底扔到了一邊去。
印坊門外的鑼聲就沒停過,都是警示用的,怕百姓鬧生事。卻忽然傳來一陣喧天的鑼鼓聲,配著吹吹打打的樂聲走近前了。
“外頭在做什麼?”
唐荼荼掀簾去看。
那竟是個舞獅班子,紅的黃的獅子站了五頭,滿地蹦跳打滾撒著歡兒,全是一順溜的。班底像是練過武的,作威風凜凜,比平常的舞獅更好看。
舞獅隊后頭有一群人下了車,邊圍了家仆無數,被遮擋得嚴實,看不清中間那是什麼人。
唐荼荼:“二哥且等等,我得去看看。”
目力不佳,看不清太遠,晏昰只消掃一眼,便知那是家規制的馬車。
“我與你一塊去罷,來得匆忙,還沒來得及看看你這印坊。”
唐荼荼莞爾:“行,我去找個斗笠,遮住點臉,您這張臉可不得。”
“不必。”
晏昰說著,翹起半,從左邊扶手取了點東西。
他這馬車外邊里邊看著都不大,除了雙騎一般人駕不起,乍看和富貴人家的馬車沒什麼分別。只在座旁突起兩個扶靠,上頭的墊掀開,里邊藏著幾個小巧的黃銅屜。
“這是?”
唐荼荼看著他掀開一只小圓盒,取出一塊淋淋的、被藥浸的面餅,展了開。
那東西薄如蟬翼,展開后,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竟是一張人|皮|面|!
Advertisement
唐荼荼驚得聲兒都小了,喃喃:“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這等潛藏份之利,他備在馬車里,可見平時常在民間行走。
外邊的鑼鼓聲越響亮了,唐荼荼被這更驚奇的東西占住了眼,舍不得走了,看著他一點一點去藥,像片面似的,極其細致地糊上臉,一寸一寸平。
分明眉、眼、耳、口、鼻,五只有鼻翼兩側增了點厚度,很細微得深了一點,別的瞧不出什麼改變,可這麼一下子竟變了完全不一樣的人!
遮住了英俊的容貌,眼前人立刻了個相貌平平無奇的中年人。
“神了……”
唐荼荼上手了,更驚奇,皮質竟像在真的皮上,連細小的孔、鼻頭與下上微微凸起的脂栓,都與真人一般無二。
手指在這張面上一寸一寸地挪,得實在仔細,晏昰仰著躲了躲,忍俊不:“別了,還不下去?”
唐荼荼這才想起正事來,彎腰出了馬車,地上已經放好了腳凳,他手下的影衛總是事事妥帖的。
才走出兩步,后腰輕輕一點牽扯。
唐荼荼扭頭:“怎麼了?”
晏昰低著頭:“別。你那帽帶,纏住了。”
何止纏住,上下結了兩個死疙瘩,帽帶輕飄飄的,打了結也沒察覺。
他左怕唐突,右怕冒犯,拇指與食指指尖勾著那結,怎麼解都不合適了。
唐荼荼后仰著頭,吃吃地笑,忍著沒躲:“好了沒有?我腰全是。”
這丫頭,葷素不忌,什麼也敢講……
晏昰:“我沒挨著。”他分明把帽帶扯得離腰遠遠的,懸空著解的。
唐荼荼:“那也不行,你站我后邊我就想笑。”
好不容易解了開,晏昰背回手,指肚磨了磨,蹭去意。
“好了,走罷。”
先頭那一行人已經進了二門,看見這左曲右拐的黃河陣,沒往里頭,趟著邊上的林道過去了,各個踩了兩腳泥。
一路喊著:“茶花兒,茶花兒,我們來給你送開張禮了!”
唐荼荼連走帶跑追上去,撂下一句:“二哥我先去忙了,你自己參觀參觀。”
頭也不回地跑了,總算在后堂追上了人。
那是公孫景逸的表弟鵲公子,還有瑞方公子,上回腳底抹油溜得飛快的盛公子赫然也在里頭。
他們抬著好幾箱的賀禮,上頭蓋了一小面金線繡字的吉布,半遮半掩著,底下的金蟾蜍、玉貔貅、招財樹了半個子。
唐荼荼心提起一分,笑著招呼:“稀客呀,你們怎麼來了?”
瑞公子瑞方嗓音清亮,當日糕點噎,沒給他留下丁點后癥,拱手折腰作了一禮:“自然是來給你道喜的,一賀茶花兒開張大吉,二賀小杜爺懸壺之喜!”
坐堂的醫士都是本地人,識得這幾位份,一時間好聲不斷。
唐荼荼上回見瑞公子,還是赴宴那日,當時他說話可沒這麼客氣。
這賀開張的禮實在是貴重了,唐荼荼擺擺手:“沒什麼喜的,我這兒無償把脈,免費看診,這是縣印坊——縣衙出錢,縣衙收,我可不拿一個子兒,開張大吉也得沖著縣衙說。”
周圍這麼些人,這群公子哥行事只圖爽快,不顧后手,唐荼荼怕落人口舌,先劃清了界限。
今日來報名的、來堂后義診的多是貧戶,多多有點小病,其中也混著不的疑難雜癥。因為往常諱疾忌醫,許多人連自己是什麼病、病了多久都說不出來,只能指著哪兒哪兒說疼。
一群醫士診完了,拿不準的,就請到杜仲那頭再診一遍。
杜仲脈的時間長,一邊起碼要兩分鐘,他嫌耽誤工夫,便一心二用,左手診脈,右手提筆記錄脈相,積攢醫案,回去和脈經做比對。到尺部五十左右,才換下一只手。
沒什麼大問題的,他眼也不眨地喊“下一個”,骨虛弱的,他得多費些工夫,也不自己寫藥方,只點出關節來,兩側醫士對癥下藥了,他再看一遍。
這群縣學學生念書勤苦,背醫書也背得,雖然還不開書本,卻已經有了活學活用的架勢,會按著經典單方酌增減。經典單方都是各代醫圣留下的好方子,君臣佐使配得利索。
公孫景逸和和還在中院忙,騰不開手,唐荼荼與這幾人不算,瞧他們被晾在這兒也不合適。
瞅了瞅,跟最的鵲搭上話:“大哥要個隊不?小神醫懸壺,今日看診不收錢啊。”
鵲師從本家的老儒,別的不說,脾氣在這里邊是最好的,合攏玉骨扇,笑坐下:“行,那我就討一個開張的吉利。”
他坐到了杜仲桌前,右手往脈枕上一放,五指虛虛攏起。
左手心肝腎,右手肺脾命,杜仲切完右手切左手,輕輕一眼皮:“下一個。”
眾人一愣。
瑞方哂笑:“好!鵲兒這是健康得很,小神醫都懶得給你講脈象啦。”
鵲溫文一笑,起讓開了位置。
修養的人家,富過三代又知飲食,這種人家的孩子子骨都差不到哪里去。
瑞方提提袖口:“我來。上回噎了,我娘怕我落下病,非要府醫給我診診。府醫非說我有慢痹,梅核氣,吃了一兜子藥——您給瞧瞧有這病嗎?”
杜仲這回連脈也沒了,怕這公子哥不好說話,給姑娘惹麻煩,他把話說得溫和。
“醫不二診,聽你家大夫的,你吃他藥吃上兩月,要是咽還覺得干,你再來找我。”
“還有這規矩?”瑞方四下了,見醫士們個個點頭,嘆口氣站起來。
椅子又騰開了,盛公子施施然上前:“來都來了,我也湊個熱鬧罷。”
可他這脈象診得磨蹭,左右手全完一遍了,杜仲微不可見地皺了眉。疑心有錯,又去切他左手,著寸位細沉的脈象又診了半晌。
最后,竟從醫箱中取出一個手心大小、斗狀的東西,扣到他口聽了聽心音。
盛公子心里一咯噔,惶恐之迅速上了臉:“……怎麼了?”
他驚疑不定地看了看唐荼荼,想起年前自己那話——弟兄五個里頭,四個全讓唐荼荼親手救過,就他一人幸存了,難不今兒也得栽在這兒?
鵲、瑞方也被驚得不輕,看那斗著心臟,忙問:“心上頭有病?”
杜仲一時沒斷言,又瞧了瞧盛公子的面,問他:“你坐下這半天,怎麼還沒停了?”
盛公子呆怔著:“我往常就累得快,回復慢,坐下喝杯茶、喚勻氣兒就好了。”
杜仲問:“昨夜累著了?”
問的是“昨夜”,盛公子囁嚅道:“昨夜安穩睡下了,今晨……”他臉上紅臊的,就差寫一個“白日宣”在臉上了。
杜仲又重新切上脈,這次遲遲沒松開:“公子心臟過外傷?”
“并無啊……平時,有姑娘著拳捶兩下,這算麼……”
一群人啞口無言。
唐荼荼差點沒能憋住臉上表,要是“小拳拳捶你口”捶出來的心臟病,那可真是夭壽了。
杜仲:“年呢?”
“家里看護得好,從沒過什麼傷。”
杜仲又問:“你爹娘可有心疾?”
猜你喜歡
-
完結1140 章

穿書之貴女咸魚日常
十三年后,那個科考落榜的少年郎李臨拿著一塊玉佩上門來要娶晉寧侯府的千金小姐。帝城轟動,紛紛在猜想晉寧侯府哪個千金倒了八輩子的霉,要嫁給這個癩蛤蟆。穿書的蘇莞暗搓搓地想,大伯家的嫡女是重生的,二伯家庶女是穿越的,她這個開局第一場就被炮灰掉的小炮灰,要智商沒智商,要情商沒情商,算了,咸魚點,還是趕緊溜吧。可是沒想到,她...
206.7萬字8.18 27162 -
完結1433 章

醫妃張狂:厲王靠邊站!
前腳被渣男退婚,厲王后腳就把聘禮抬入府了,莫名其妙成了厲王妃,新婚夜差點清白不保,月如霜表示很憤怒。老虎不發威,當她是病貓?整不死你丫的!…
221.3萬字5 93988 -
完結622 章

重生後,將軍她被冷戾王爺嬌寵了
她是北國赫赫有名的女戰神,守住了天下,卻防不住最信任的人反手一刀。 被渣男親妹算計隕命奪子,慘死重生后成了逃命的小可憐,轉頭嫁給了渣男他弟。 外阻南境,內聯七絕,天下消息盡在她手。 這一次,渣男的江山,狠毒妹妹的狗命,她全部都要! 她手段果斷狠辣,卻在那個清冷病弱的王爺面前破了功 磕磕巴巴:“我,我也不清楚是原來孩子是你的......” 冷戾的男人眼眶通紅:“你的前世是,今生也是我,生生世世我都不會放過你。 ”
110.5萬字8 34883 -
連載2433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于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不過,不是不能人道嗎?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只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里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542.7萬字8.18 13890 -
連載50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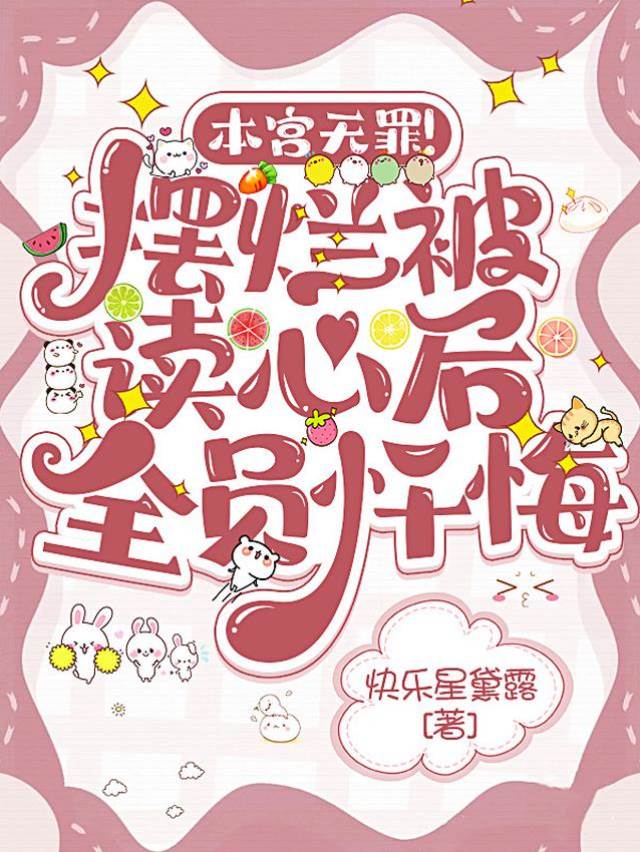
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
微風小說網提供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在線閱讀,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由快樂星黛露創作,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最新章節及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就上微風小說網。
85.5萬字8.18 3813 -
完結200 章

開局當兵發媳婦,我激活了斬首系統
穿越到古代,別人都因當兵發媳婦逃跑,就我激活了系統先挑了個潛力股,別人拼命練武殺敵攢軍功想當大將軍,我殺敵變強還能召喚千軍萬馬,一統天下不就是我的人生巔峰嗎?
37.3萬字8 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