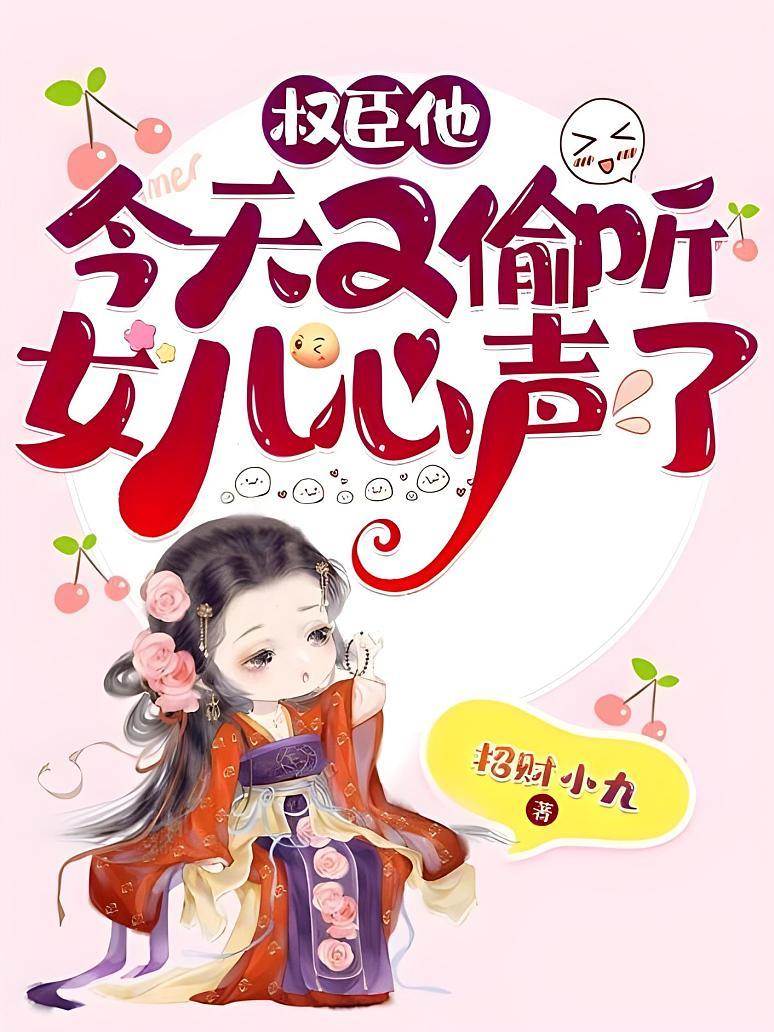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穿成流放反派他元配》 第7章 第七章
雨下到傍晚,終于是停了。
葉嘉喂了一把粟米給小崽,正在院子后頭看地。周家是沒有地的,口糧都是從鎮上的糧鋪來。
因著囊中,蛋菜很買,日日就吃粥配咸菜。葉嘉下午無事時揭了那咸菜罐子,那味兒,一塌糊涂。若非真的窮,葉嘉都想把那兩大罐給扔了。把那兩罐子菜都給泡了水,后來再吃倒是沒那麼齁咸。又費了些功夫將那些菜重新理。
忙活到傍晚才瞧見了周家后院空了老大一塊地。
真的窮到份上,人的底線是可以放低的。之前很討厭小區里一些老人把花草拔掉種菜的葉嘉,現在也琢磨著是不是可以把后院這塊空利用起來。比如翻出來種點能吃的菜。余氏是傍晚的時候才回來的,葉嘉扭頭見從院子外頭路過喊了一聲。余氏應了聲,進屋坐下就在那唉聲嘆氣。
原來,上午是同村的劉大娘來喊。兩人歡歡喜喜結伴去了鎮上,找繡房掌柜的結錢。
在繡房磨了一日,工錢是結到了,但把東家給得罪了。東家這次去走貨傷了元氣,繡房里不要那麼多人。余氏去這一趟拿了快一兩銀子,把活兒給丟了。
“這往后的日子可怎麼過啊!”余氏真是哭都沒眼淚,也不是不給東家息的機會。實在是家里沒銀子不行,“沒了糊口的營生,咱一家四口真要喝西北風了!”
葉嘉冷靜道:“家里米糧都有,撐三個月沒問題。”
“那三個月之后呢?”余氏如今其實更多的是懊悔,早知今日就不該走這一趟。可事到如今,又沒法子求人家讓再回去做工。東家把話都說絕了,一點轉圜的余地都沒有。
絮絮叨叨地哭,葉嘉也不知怎麼勸。去后廚端了幾個蘿卜兒餅過來讓余氏吃點。
Advertisement
余氏搖了搖頭,低頭抹著眼淚直說吃不下。
葉嘉嘆了口氣,轉回屋。
這一夜,周家靜得連聲兒都沒有。余氏也沒心思管蕤姐兒,蕤姐兒人小不知事兒,祖母說跟著嬸娘,便跟著葉嘉后打轉。葉嘉晚上熱了幾個餅,跟蕤姐兒隨便對付一下。轉頭就給周憬琛送了一碗粥去。周憬琛靠坐在床上,應該是聽見外頭余氏的話了,神十分凝重。
他一條還斷著,額頭的傷沒好。下午出屋子那一會兒耗盡了他的力氣,此時彈不得。不過抬眸看向葉嘉時一雙眼睛幽沉沉的泛著。
心口跳了一下,葉嘉垂下眼簾只說了一句:“明日你在家看著些蕤姐兒,我要去鎮上一趟。”
說罷,轉便出了東屋。
后的目一直凝著,葉嘉倒沒覺得怎樣。夜里余氏翻來覆去,葉嘉也沒管。翻了睡,翌日天還沒亮。就背了個背簍抓了把傘出門。
出門時余氏還沒醒,昨夜翻到三更天還沒睡,天蒙蒙亮才睡著。葉嘉才走到院子,發現東屋的窗邊站著一個人。周憬琛不知在看什麼,聽到靜看過來。四目相對,葉嘉愣了一下。正好代他若起得來,記得給后廚的喂食。起不來就蕤姐兒。
“我省的。”他不知在窗邊站了多久,緩緩掀皮,嗓音如玉石相擊,清冽非常。
葉嘉克制住耳朵的沖,木著臉開院子門走了。
不下雨,鎮上的商鋪開門的多了很多。葉嘉驚喜地發現,李北鎮這種小地方竟然有瓦市。不過因著時辰尚早,瓦市未開。好些不知打哪兒來的商販擔著東西,趕著羊往瓦市聚集。
就一空地,弄了一排鹿砦擋著。兩個彪形壯漢守在門口,旁邊掛了一張銅鑼。
Advertisement
葉嘉站在外頭等了一會兒,見這些人都在瓦市的鹿砦后頭等著。
這些商販有些是下鄉的,有些是外來的。賣糧食的、賣自家種菜的,賣魚賣的都有。葉嘉瞅見好幾個卷的商販混在其中。天還早,擔子放在腳邊,街邊也沒個賣吃食的。帶了干糧的,蹲在地上啃干餅子,沒帶的,聞著別人吃得香就直吞口水。
葉嘉心一,溜邊兒去看。賣食的一個沒有。湊了巧,聽見一個得實在眼綠的卷大胡子著不太地道的大燕話,跟旁邊一個黑臉賣羊的老漢買餅子吃。
餅子老漢自家烙的,估計才出鍋,聞著一焦香味兒:“十文錢一個,兩個十五文。”
這一要價,葉嘉耳朵都豎起來。眼睛不住地往那塊餅上瞥,跟燒餅差不多大。約莫比蘿卜餅大一半。敢要價十文。旁邊那卷大胡子估計真了,一咬牙掏了十五文:“給我兩個。”
葉嘉這一顆心頓時就咚咚跳起來了。又繞著走了一圈,似這般臨時買餅的不。十文五文的,掏的那一個爽快。
一陣冷風吹得,葉嘉激靈靈打了個寒。了手,守門口的壯漢銅鑼一敲,鹿砦就拉開了。小商販們擔起東西魚貫而。有那趕羊的落在最后頭,葉嘉瞥見一頭母羊下墜著鼓脹脹的。跟上去,張口問那趕羊的老漢羊賣不賣。
這年頭,尋常普通人家是不吃羊、牛的。家里養羊的能喝上幾回,但也嫌味道腥膻。不多喝。趕羊的還是頭一回遇上不買羊,只要羊的。
那老漢約莫有點西域人的統,黑紅的臉,廓很深:“你要多?”
“你小半桶給我。”葉嘉知道羊有很多種吃法,但不是專業廚師,不會做。要太多放著也壞了。吃不起,喝點補補。
Advertisement
“十文錢!”老漢沒賣過羊,但第一回賣,他膽大地喊,“我給你一桶。”
“不用不用。”一桶也喝不完啊,葉嘉只想要小半桶。
“不要一桶,那不賣。”老漢估計是瞧出來葉嘉真想要。見他喊出十文還不走,心里就有底了。
葉嘉倒不是計較那十文五文的。這老頭兒強買強賣的態度確實令人著惱。跟老頭兒扯了半天,直說若是吃習慣了,往后還來買。老頭兒才狐疑地給答應了。弄了個木盆去母羊肚子下面,他沒一會兒就了小半盆。葉嘉蹲在一邊看著,順口問了他在這擺攤,要多錢。
老頭兒一邊忙活一邊答應兩句。葉嘉搞了半天弄明白,只要十文就能進來擺攤。位置好壞看運氣,搶到哪兒就是哪兒,一天一換。
六文錢換了大半盆新鮮羊,葉嘉又去買了個小桶:“你明兒還來?”
“明兒不來,后日來。”
葉嘉拎著小半桶的羊在人群里竄,別說,拎起來不重。拎久了胳膊疼。想想,又去鎮子上走了一遭。從前頭看到后頭,鎮上確實不止一家賣吃食。但也一手能數過來,三家的樣子。酒肆的那家專賣,鹵羊,還有鹵牛。葉嘉是知道古時候不準吃牛的,沒想到一個小店有牛賣。
過去問了一,一斤牛要五十文,一斤羊也三十文。這麼貴,這店賣的還不錯。葉嘉問的時候,他都說沒了,明兒來。另外兩家一個做客棧的。客棧,兼賣吃食。唯一一個就賣吃食的,做的是馕和面。一個馕五文錢,面十文一碗。
葉嘉買了個馕嘗嘗,就普通的馕。吃著就單純的糧食味兒,頂飽。
轉悠了一圈,葉嘉心里有了底。一點不耽誤,扭頭就去鐵匠鋪子找鐵匠打煎鍋。那種底是平的,后世做水煎包那種大煎鍋。家里沒那好爐子,又去買了一個。
Advertisement
這一通花下來,手里攥著的那兩銀子只剩幾個銅板。葉嘉也是夠心狠,下得去手。就剩那麼幾個銅板,還了個牛車,把爐子和羊一車拖回去。
坐在牛車上晃晃悠悠地到了家門口,余氏正蹲在井邊上打水。
估計是剛起來沒多久,臉上還掛著愁容。扭頭看到葉嘉又一大車的拖回來,扔下瓢就小碎步跑過來。這一大早的,余氏心里就懊悔昨日不該當著葉嘉的面哭。真的怕曉得周家沒活路,徹底嫌了周家,跑去鎮上找那個男人:“這是打哪兒回來?”
葉嘉自己拎著羊,請了趕車的老漢幫忙把爐子給卸下,轉頭語速極快地跟余氏說了自己的打算。
余氏聽得心里又是驚又是沒底:“這生意真能做嗎?要是賠了可咋辦?”
古時候朝廷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人最是地位低下被瞧不起的。余氏是宦之家出,雖然流放了三年,這個心里固有的想法沒那麼容易變。此時猶猶豫豫的一是心里對商人低人一等介懷。二是像詩人嘆的晨起征鐸,客行悲故鄉。商人的活計是最沒有著落的。心里沒底。
但葉嘉都已經把爐子買回來了,鍋在打,三日后就能取,工錢也給了,也說不出反對的話。心里嘀咕著葉氏沉不住氣,還是過來搭把手,跟葉嘉一起把爐子給抬回了屋。
葉嘉沒留心余氏滿面愁容,把自己缺銀子買食材的事直說了。
余氏著昨日才結的一兩銀子手背都出青筋了,舍不得。蕤姐兒蹬蹬地從后廚跑過來,一面跑一面喊嬸娘:“崽,喂過了。嬸娘,早上吃餅餅呀!”
看來是真的好吃,小孩兒昨日吃過,早上還盼著餅呢。
葉嘉也沒強迫拿,原主的前科太多了。次次要到錢轉頭就填補了娘家。葉嘉琢磨著要去鎮上賣吃食,往后就得吃苦。瓦市趕早,不能錯過了高峰期。二鍋跟灶都很重,要生意好得現場做。這些東西搬過去需要車。不過好在王家村離鎮子不遠,費點力氣抬過去也可以。
雖然吃點苦,但跟人家挑擔子的比起來,也不算太苦。
心道余氏定沒有那麼快答應,葉嘉拎著羊去了后廚。
既然要干活,就得吃得好。不然沒力氣。葉嘉特意用了點糖,煮了一鍋羊。從懷里掏出一小袋杏仁,往里頭扔了些去腥氣。轉頭又熱了幾個餅子。
一大碗熱羊喝下肚,葉嘉覺自己凍麻了的手腳都暖了。給小孩兒盛了一碗。有些喝不慣,但葉嘉讓喝,聽話地乖乖的喝。喝了幾口過后,跟葉嘉小聲的說好喝。果然小孩子就是喜歡味兒,等葉嘉跟小孩兒吃飽出來,余氏不在院子里。
葉嘉想著又返回后廚,盛了一碗羊送去東屋。
一掀簾子,余氏在東屋。周憬琛正在說服同意葉嘉的要求,把銀子給。
余氏言又止的,到底沒有說葉嘉撈錢填補娘家的事。本來兒子就不喜葉氏,再說怕是這輩子都不會有孫子抱。
葉嘉揚了揚眉,把羊放到周憬琛手中:“喝點羊,補好了替我干活。往后搬鍋灶還得靠你。”
周憬琛:“……”
猜你喜歡
-
完結1566 章

來人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啥? 身為王牌軍醫的我穿越了, 但是要馬上跟著王爺一起下葬? 還封棺兩次? 你們咋不上天呢! 司夜雲掀開棺材板,拳拳到肉乾翻反派們。 躺在棺材板裡的軒轅靖敲敲棺材蓋: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282.6萬字8.18 227621 -
連載1841 章

重生後我嫁了未婚夫的皇叔
前世,她是貴門嫡女,為了他鋪平道路成為太子,卻慘遭背叛,冠上謀逆之名,滿門無一倖免。一朝重生回十七歲,鬼手神醫,天生靈體,明明是罵名滿天下的醜女,卻一朝轉變,萬人驚。未婚夫後悔癡纏?她直接嫁給未婚夫權勢滔天的皇叔,讓他高攀不起!冇想到這聲名赫赫冷血鐵麵的皇叔竟然是個寵妻狂魔?“我夫人醫術卓絕。”“我夫人廚藝精湛。”“我夫人貌比天仙。”從皇城第一醜女到風靡天下的偶像,皇叔直接捧上天!
331.1萬字8 71759 -
完結332 章

首輔寵妻錄
侯府嫡女沈沅生得芙蓉面,凝脂肌,是揚州府的第一美人。她與康平伯陸諶定下婚約後,便做了個夢。 夢中她被夫君冷落,只因陸諶娶她的緣由是她同她庶妹容貌肖似,待失蹤的庶妹歸來後,沈沅很快便悽慘離世。 而陸諶的五叔——權傾朝野,鐵腕狠辣的當朝首輔,兼鎮國公陸之昀。每月卻會獨自來她墳前,靜默陪伴。 彼時沈沅已故多年。 卻沒成想,陸之昀一直未娶,最後親登侯府,娶了她的靈牌。 重生後,沈沅不願重蹈覆轍,便將目標瞄準了這位冷肅權臣。 韶園宴上,年過而立的男人成熟英俊,身着緋袍公服,佩革帶樑冠,氣度鎮重威嚴。 待他即從她身旁而過時,沈沅故意將手中軟帕落地,想借此靠近試探。 陸之昀不近女色,平生最厭惡脂粉味,衆人都在靜看沈沅的笑話。誰料,一貫冷心冷面的首輔竟幫沈沅拾起了帕子。 男人神情淡漠,只低聲道:“拿好。” 無人知曉,他惦念了這個美人整整兩世。
53.2萬字8.33 6779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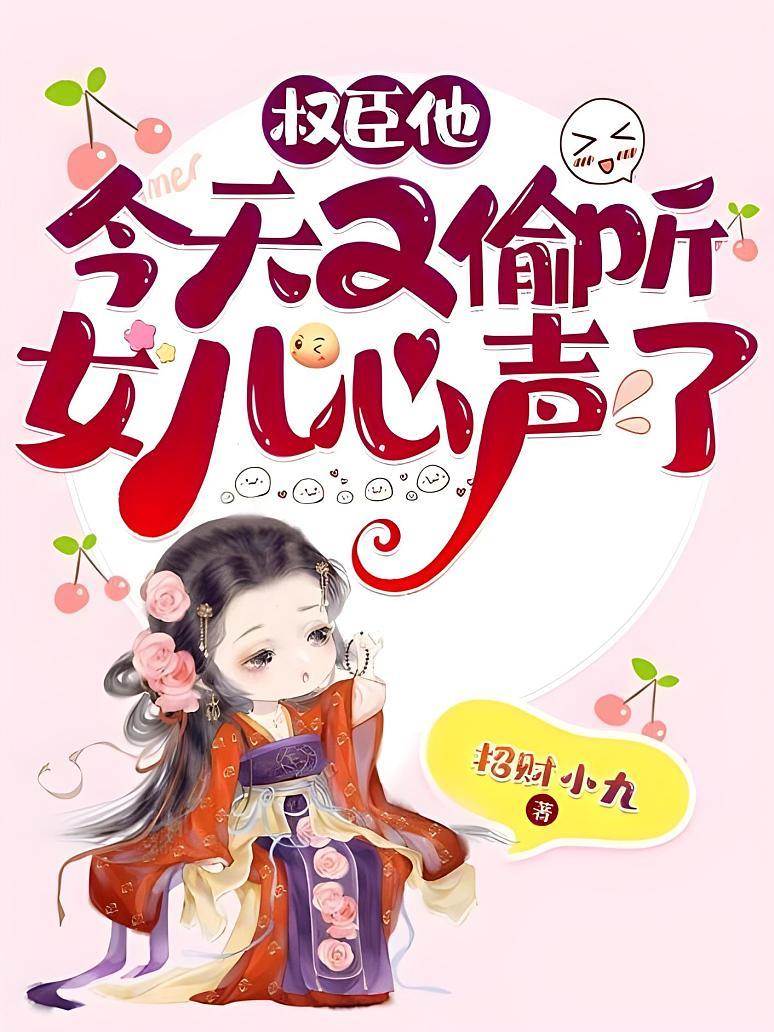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