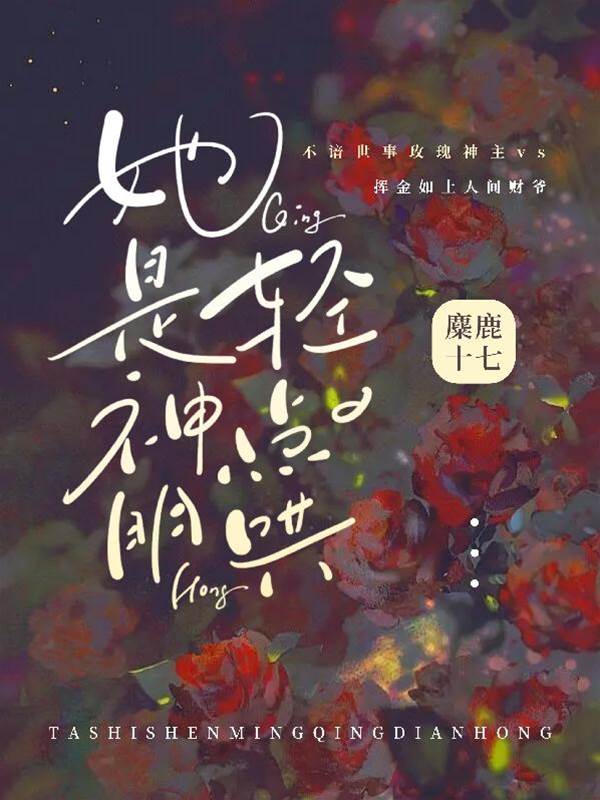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攤牌了周總老婆就是我》 [攤牌了周總老婆就是我] - 第二章 這不合規矩
花云然一笑,邊掛著兩個酒窩。
路千寧詫異的看了一眼,可不認為花云然會因為的工作能力不錯就十分欣賞的要跟朋友。
卻也猜不花云然加微信是想干什麼。
花云然看不說話,又問了一句,“你不愿意嗎?”
“當然不是。”路千寧客氣一笑,從口袋里拿出手機,“我掃您吧。”
沒理由不加。
花云然趕打開微信,讓掃了一下名片,互加了好友。
花云然還想說什麼,可路千寧發現周北競已經不見了蹤影,提醒道,“花小姐,別讓周總等太久,我們還是先出去吧。”
“好。”花云然這才繼續往前小跑。
深夜的公路上車很,黑奔馳商務車猶如一道閃電疾馳。
路千寧開著車,周北競和花云然坐在后面。
目視前方,可注意力卻很不集中,耳旁全是后面那兩人的低聲細語。
像是熱中的小打罵俏,也像是甚好的小夫妻說笑日常。
能聽到他們說話還好,可路千寧就怕聽不到!
后面忽然安靜了幾秒,腦海里忽然劃過兩人在后座上的可能。
路千寧將頭歪了歪,這才看到后面的場景。
周北競長眸淺垂,眉尾上揚看起來心不錯,薄輕輕勾著,十指穿在一起放在翹起的長上。
花云然朝他那邊傾斜,若不是兩人中間隔著很大的距離,都要鉆他懷里去了。
大概是兩人結束的話語勾起了回憶,才沉默下來。
來不及想什麼,冷不丁撞周北競漆黑如墨的眼底。
那雙眼睛像是會勾人心一樣,過鏡子折到臉上,迅速就把歪了的頭擺正。
清了清嗓子說道,“周總,前面左拐就到花家了,咱們是將車子開進去還是停在小區門口?”
Advertisement
倉促問下的問題后,又后悔了。
花家住的是七里香溪別墅,從小區門口進去距離最近的別墅走路也要十幾分鐘,周北競怎麼可能讓花云然拎著行李箱走進去呢?
“阿競,你怎麼把我送回家來了?”
花云然似乎才發現快到家門口了,抿了抿說,“我不想回家。”
“你都好幾年沒回來了,該第一時間回去跟家里人聚一聚。”周北競說完,看向路千寧,“在小區門口停。”
花云然不說話了,車廂陷一令人窒息的死氣沉沉。
待車一停,路千寧就迅速從車上下來,將后面的車門打開。
“周總,花小姐,到了。”
說完又去后備箱拿花云然的行李,再回頭便看到從小區里走出來一個男人。
一套阿瑪尼的運裝掛在上,頂著月緩步朝他們走過來。
花封比周北競大了兩歲,打理著整個花家,同周北競一樣是江城赫赫有名的人。
兩人經常湊到一起,所以路千寧經常能見到他。
男人那和的五和一雙勾人的桃花眼,讓他看起來很是浪不羈。
可路千寧知道,他是個笑面虎,誰敢惹了他不高興,他比周北競還狠。
而花云然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妹妹,也是花家的掌上明珠。
路千寧率先笑著打了個招呼,“花。”
花封同頷首示意,然后便走過去張開雙臂把花云然抱在懷里。
“你個小沒良心的,一走就是六年,看這一臉不高興,難道剛回來還不想回家?”
花云然見到他雖然心里高興,可還是為了周北競招呼不打一聲送回家而悶悶不樂。
這次……可專門是為了彌補他回來的,這種連家人都不陪也要先哄他,多能讓他高興一些吧?
Advertisement
“好了,是我讓阿競把你先送回家的,爸媽已經等了你好幾個小時了。”花封譴責道,“以后你跟阿競來日方長,急什麼?”
花云然心里這才舒服一些,回頭笑著看了一眼周北競,“我就是想多跟阿競呆一會兒,不過既然都已經回來了,我就先回家。”
周北競面看不出喜怒,單手在西裝里,微微靠在車上,點了點頭。
“人送過來,我就先回去了。”
路千寧一聽,趕過去把車門打開,周北競轉上了車,還沒等路千寧把車門關上。
花云然就湊過來阻止了的作,探頭跟車的男人說話。
“阿競,明天早上我去周宅看周,好不好?”
車廂里線很暗,過車窗路千寧只能依稀看到男人棱角分明的線條。
他薄輕啟,吐出一個字,“好。”
然后花云然才心滿意足的退回到花封邊,揮了揮手。
路千寧將車門關上,回頭跟花封和花云然說了句,“花,花小姐,再見。”
然后繞過車上了駕駛位,系上安全帶,發引擎離開。
作一氣呵,可心像塞了一團棉花似的,不過氣來。
他們還得回北周,因為周北競有個國際會議要開,路千寧這個特助幾乎是二十四小時跟著他的。
他回家才能離開,所以凌晨兩點多鐘,卻還在外面的工作崗位上等著他會議結束。
線被打通,男人清冽好聽的聲音從電話里傳出來,“進來。”
言簡意賅的兩個字,都不需要問在不在,雖然才短短三年,可兩個人的默契……
不論從床上還是從工作上,都是天無的。
拿起離婚協議書,走進辦公室,不等轉過來,就猛地被一只強而有力的臂膀拉進懷里。
Advertisement
下一秒,男人鋪天蓋地的吻落下來,一雙手也并不安分。
路千寧愣了幾秒,然后后傾避開他落下的,詫異的明眸中倒映著男人求不滿的樣子。
“怎麼了?”他聲音接近沙啞,已然是箭在弦上的狀態。
路千寧抿了抿,將手里的離婚協議書遞過去,“周總,這是您的離婚協議書,您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周北競沉一口氣,將協議書拿過來看都不看一眼丟在了桌子上,深沉的目看著。
“路千寧,你今天狀態好像不太對。”
聽不出這個狀態是指在車上看他們,還是現在,扯出一個笑容來轉移話題。
“周總,時間不早了,我送您回去休息吧,明日一早不是還要去周宅?”
周北競頭往休息室的方向甩了甩,“來不及回去了,今晚就歇在這里吧。”
路千寧在休息室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小時過,幾乎每次都是他‘彈盡糧絕’后,就穿上服離開。
唯一一次時間最長的,是兩條發實在下不了床,這才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
這是周北競第一次邀請在這里過夜。
也是第一次拒絕周北競,“周總,這不合規矩,何況……”
花云然已經回來了。
但的話沒說完,就被周北競打斷了,“路千寧,你在拒絕我?”
路千寧柳葉眉皺著,難道不該拒絕他嗎?
為妻子都要被離婚了,一個人還能留的住?
但他既然想要,今天為什麼不留花云然,主留下明明就有獻的意思。
可這些話不到來問,縱然心里在疑也只能下去。
“周總,我回家還有事。”
雖然委婉但依舊是拒絕的意思,周北競忽然低頭,低頭抵在肩膀上,熱氣噴灑在鎖骨,又又麻。
Advertisement
“那順路送我回西園小筑吧,明日一早帶上離婚協議書接我去周宅。”
他聲音從頸肩傳來,下一秒就站直了,折回辦公桌前拿了西裝外套離開。
路千寧一言不發的跟上,說回家有事并不完全是借口。
把周北競送回家后,開車只用了十分鐘就到了單公寓。
那是一套復式公寓,面積不大但有個二層隔斷,在這寸土寸金的地方價值兩百多萬。
是去年過生日的時候周北競送的,剛好那晚陪了他。
回到家里將包和車鑰匙放下,打開燈上了二樓,從床頭的柜子里拿出戶口本和結婚證,又回到樓下放到自己包里。
只要明天周答應了花云然和周北競重歸于好,接下來便是和簽字,扯離婚證的流程。
總不能再回來拿一趟。
而且一旦妻子這個份曝,周北競特助的位置肯定也做不下去了。
在考慮……明天該怎麼開口告訴周北競就是他忘到腦后的妻子。
周北競會不會信當初來北周真的不是沖著他來的?
因為當初周北競本認不出,又急需這份工作,便沒有主承認。
后來事態愈發超出的想象,周北競是個討厭善用心計的人。
就更不敢說了。
可現在騎虎難下,只能祈求……明天自己不會太難看。
迷迷糊糊的,倒在沙發上就睡著了,早上六點的鬧鈴間隔十分鐘后又響了一次,才把喊醒。
看了看時間迅速爬起來洗漱,化了一個致的妝容卻掩飾不住黑眼圈。
煮了兩個蛋熱敷一下,然后喝瓶牛又把蛋剝開吃了,這才開車去西園小筑。
雖然不,可還是得吃,因為辦完了離婚協議就得立刻去找工作,沒點兒力怎麼能行?
周北競看起來休息的也不好,上車之后就在后座上閉目養神,這讓沉悶的心更加不過氣。
猜你喜歡
-
完結551 章

總裁聽我的
顏可欣單槍匹馬去找未婚夫尋歡作樂的證據卻沒想被吃干抹凈血本無歸反擊不成?那逃總可以了卻沒想這男人恬不知恥找上門,百般無賴的表示。“睡了我,還想就這麼跑了嗎?”
97.1萬字8 19077 -
完結242 章

冷少的逃跑嬌妻
在陸琪琪20歲生日那天,不小心誤睡了總裁,還將他當成了牛郎,隨后甩下100塊大洋離開。向來不注重感情的冷慕晨卻對陸琪琪香腸掛肚了5年。5年后,陸琪琪帶著天才可愛寶寶回國,再次偶遇了冷慕晨——“5年前,我讓你逃走了,這一次,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了的。”冷慕晨對著陸琪琪愣愣的說道。
56.9萬字8.14 28173 -
完結1094 章

南太太馬甲A爆了
父母從小雙亡,蘇清歡從小受盡各種寵愛,來到城市卻被誤以為是鄉下來的。姑姑是國際級別影后,干爹是世界首富。蘇清歡不僅在十五歲時就已經畢業修得雙學位,更是頂級神秘婚紗設計師Lily,世界第一賽車手,頂級黑客H。當蘇清歡遇上南家五個少爺,少爺們紛紛嗤之以鼻……直到蘇清歡馬甲一個個暴露,五位少爺對她從嫌棄分別轉變成了喜歡愛慕崇拜各種……
193.8萬字8 127400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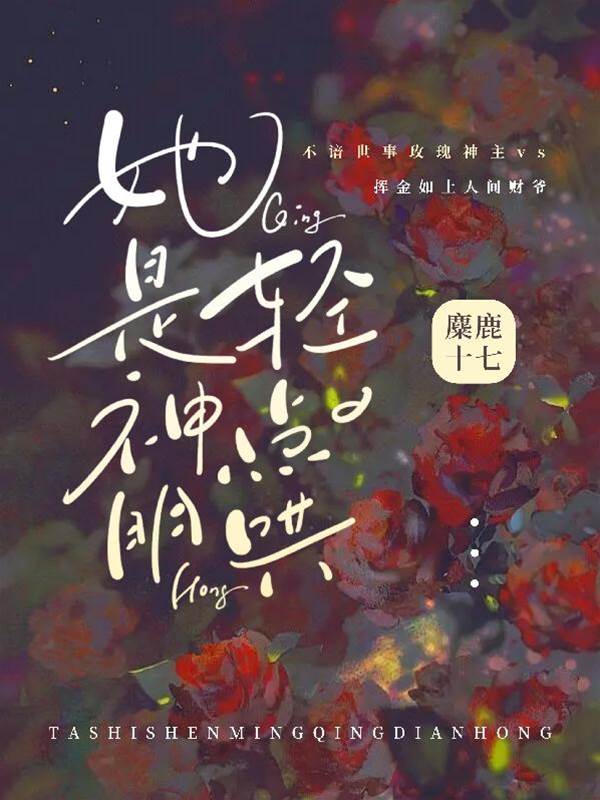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連載138 章

蓄意嬌養誘她入懷
【蓄謀已久+甜寵 + 曖昧拉扯 + 雙潔1V1 + 6歲年齡差】【人間水蜜桃x悶騷高嶺花】 南知做夢也沒想到,真假千金這種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狗血的是,她被下藥,把叫了12年的顧家小叔叔給睡了。 怎麼辦?跑路唄。 花光積蓄在暗網更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親手養大的水蜜桃,剛啃了一口,長腿跑了。 找她了三年的顧北期忍著怒氣,把她抵在車座角落,“睡了就跑,我算什麼?” 南知:“算…算你倒霉?” 顧北期:“這事兒怪我,教你那麼多,唯獨沒教過怎麼談戀愛。” 南知:“你自己都沒談過,怎麼教我?” 顧北期:“不如咱倆談,彼此學習,互相摸索。” - 顧家小三爺生性涼薄,親緣淺淡。 唯獨對那個跟自己侄子定了娃娃親的小姑娘不同。 他謀算多年,費盡心思,卻敵不過天意。 被家人找到的南知再次失蹤。 在她訂婚宴上,男人一步一句地乞求,“不是說再也不會離開我?懷了我的崽,怎麼能嫁別人。”
1.8萬字8 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