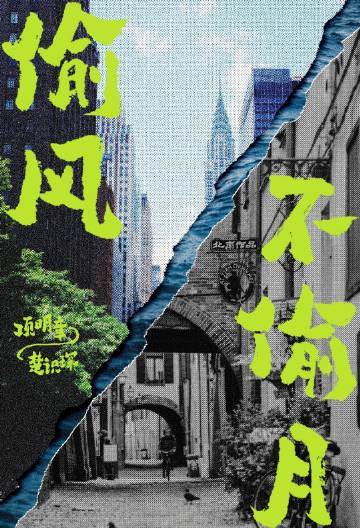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誘妻成婚:前任蓄謀已久》 第223章 她的淚灼傷他的心
誰能告訴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一切都和管家彙報的本不是一個樣子。
厲尊大步到床邊,看清被綁在床上的人真的是如可時,他全的每一神經都在漲疼。
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弓下子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從哪裏發出來的。
「如可,醒醒,如可,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他除了渾的抖,連低音都在發。
如可聽到了聲音,恐懼的睜開滿是的眼睛,怔怔的看著出現在自己眼前的人。
淚水,本不控制的往下滴落,是老天爺聽到了的禱告嗎?
他,終於回來了。
即使他是全世界最狠,最殘忍,最冷漠,最嗜的男人,他也是唯一能救的男人。
他把關在地獄里,卻是這地獄里唯一能讓活下去的人。
哭了,憋了十幾年的眼淚,終於崩陷,到底做錯了什麼?到底是為什麼?
哭了,即使他對再壞再冷漠,倔強的都沒有在他面前掉過一滴眼淚。
可現在,哭了,泣不聲,淚如雨下。
看著他,任由淚水不停的往下掉,淚水打在他的手背上,卻如濃硫酸一樣侵蝕著他的心臟。
他以為只要他不出現在的面前,就會慢慢好起來,會開心的笑,無憂的生活。
他想著,就算這三個月,再次逃跑了,那就讓走吧,只要那是最想要的就行。
早已不知道從何時開始,他最無能無力的,是留不住,還不能給歡笑。
是他錯了,從一開始,就是他錯了。
「發生了什麼事?」他蹙著眉心,眼眸之中,還是第一次沒有遮攔對的心疼。
他的一句話,讓他的淚水掉的更多,是不是在果以日記里看到的那些,是真的?
Advertisement
保鏢先聽到如可房間的靜,以為如可半夜又瞎鬧,很不耐煩的過來,啪的一下就打開了房間里的燈。
等保鏢看到臥室里站在的人時,嚇得倒退兩步,差點沒直接坐到地上。
厲尊一雙鷙的冷眸嗜的冷盯著站在門口已開始慌的保鏢。
他說過要他們好好照顧好如可,但不是讓他們這樣照顧的。
他現在,殺人的心都有。
「厲爺,是如可小姐鬧的太厲害,有的時候半夜犯病,把家裏所有人都……」
鬧的厲害,厲尊還聽的下去,『犯病』兩個字,卻是犯到他的底線。
攉的一腳,猝不及防的就踢在了保鏢的腹部,頓時疼的保鏢弓起了腰。
要說他也算是功夫高手,但在厲尊面前,他就是一隻被獵豹侵住死的野狗,本毫無反擊之力。
另一名保鏢,還有管家傭人都聽到房間里的打鬥聲,還以為是如可解開了繩子,又開始扔東西。
一位好不容易睡著的傭人邊走變發牢,「是真的打算把我們都折騰死才罷休,真是不明白,厲爺為什麼讓我們照顧一個瘋子,這要是……」
「厲……厲……厲爺……」發牢的那個傭人在看到大家都直直的站著,也不敢,氣都不敢的事,覺得自己的死期也已經到了。
大概十分鐘后,兩名保鏢在毫無還手之力的況下,被厲尊打趴在地上,起都起不來,也不敢。
所有的傭人嚇得渾都在抖,特別是管家,全都在冒冷汗。
他每天都和厲尊彙報如可小姐的況,卻是從來都沒敢說過,他們是這樣對待如可小姐的。
當厲尊威懾嗜的眸轉到管家的方向時,管家瞬間都了。
「厲爺,如可小姐每次發作,我們實在都控制不了,家裏的東西能砸的基本都被砸了,還……還砸傷了我們……」
Advertisement
厲尊一言不發,如地獄里走出來的使者,一步一步緩慢的走到管家站著的地方。
砸東西怎麼了,他的東西怎麼砸怎麼砸,他都沒說什麼,誰管得著啊!
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一個手,管家睡的領口已經被厲尊拽在手。
「信不信我殺了你們!」
他的話絕不是威脅,冷戾的眼神足以嚇掉他們的半條命。
那兩個手很高的保鏢都已經被打傷在地,如果真的要殺死們幾個,完全不需要費任何力氣。
他是個神的人,在他這裏工作了很久,都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黑道還是白道?對這裏的每個人而言,他是神,天神還是死神就都在他的一念之間。
「厲……厲爺,我們真的也是被如可小姐的沒有辦法,我們才……」
管家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砰的一聲巨響嚇得癱在地。
厲尊攥的拳頭狠狠的砸在旁的玻璃魚缸上,嘩啦一聲,裏面的水和魚還有水草都瞬間溢了出來。
管家年紀不小了,跟了他十幾年,他不手,不代表他原諒。
「都tm的給我滾!」一聲威懾的怒吼,讓所有人都嚇得連滾帶爬的打著哆嗦離開。
所有人離開后,整棟別墅安靜極了,從魚缸里蹦出來的小魚『啪嗒啪嗒』的求生中。
厲尊腦海里都是過去三個月如可經歷了什麼?
就如同在地上蹦,回到水裏的小魚,而他把一個人扔在這裏,任由自己求生。
他頹廢無力的坐在旁邊沙發上,口堵的難以呼吸。
抬眸間,一道弱纖細,骨瘦如柴的影定在他的眼眸之中。
兩人幾米遠的距離,四目相對,誰也看不懂對方。
如可一步一步腳步極輕的往他邊走,赤腳走在冰涼的地面上,上面的水和玻璃碎片都像是毫無知覺一樣。
Advertisement
厲尊忍著心痛眼睜睜看著走了過來,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組織往前走,為什麼不過去將他抱到自己邊來。
他的心太矛盾,太糾結,看著痛,他會難,可如果看不到呢?
過去三個月,他覺得自己和死了沒有任何區別。
如可在他的旁坐下,現在就連自己都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個神不正常的人?
輕笑一聲,太久沒說話的關係,聲音啞的幾乎說不出話來,「看到我變現在這個樣子,你開心嗎?」
厲尊扭頭看著坐在旁的,面無表,無波無瀾,像極了一個沒有生命的布偶。
開心嗎?
呵呵,開心嗎?
他嘲諷的冷笑著,手背上的明明是因為剛才打碎魚缸而流出的,他能覺到的,卻是他回來時,那一滴一滴嗜的淚。
他看著,空毫無焦距的目直直的盯著那條還在拚死掙扎的小魚。
突然,他再也做不到抑自己,他覺自己再抑制下去,會崩潰的。
他兩隻冰涼的大手用力的捧住消瘦的臉,整個撲了過去,長一,被嚴實的錮在沙發里,無法彈。
以為會拚死掙扎的,以為會已死抵抗,以為會瘋狂打他的……
但都沒有,最狠的,就是無於衷,若無其事。
就是一毫無溫度,沒有任何緒,封了心,定了的軀。
他想做什麼,本不會在乎。
越是沒有任何的反應,他的吻就變越深,不拒絕,不回應,他就用力的吸,吮著,讓覺到疼,讓不要再像一樣的麻木。
此時的他,不是憤怒,不是宣洩,不是佔有,而是對,對自己,的無能為力。
突然,在他下的軀了一下,他以為終於忍無可忍要反抗了,卻是聽到帶著憐人哭腔的哀求了一聲,「疼,我疼……」
Advertisement
厲尊一顆心瞬間就如同被巨石碾一般的疼痛難忍,他再也無法繼續,抖的在的邊一呼一吸,嚨撕裂的痛讓他說不出一個字。
他額頭抵在的額頭,兩人的呼吸來回換,他大手在的臉上無助的輕著。
的一聲疼,已經讓他潰不軍。
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沒有,只能說,如可,你贏了,而他,輸得一敗塗地。
當結實的後背覺到兩隻雙手在上面輕拍著的時候,他知道,一直都知道。
知道他的無助,他的脆弱,他的心……
整張臉埋在的頸間,已經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有掉過眼淚,哥哥還活著的時候就經常罵他,沒心沒肺,爸媽死的時候,他都沒掉過一滴眼淚。
今天,他了眼眶,想要在的面前,弱一次,他就是想要乞討一次的擁抱,的安。
的手一直在他的背上輕拍著,他們兩個人,更需要安的那個,傷最深的那個,明明就是,現在卻是在心疼他。
厲尊猛然的推開,站在的面前,他真是個怪人,這麼快的時間,就瞬間恢復到之前的居高臨下。
他冷漠的凝著,如可微仰著頭和他對視著,剛才自己一定是瘋了,不對,本來就是個瘋子。
竟然會同他這麼久以來的忍,竟然會想要安他,呵呵。
厲尊倏然的手將坐在沙發上的如可拉拽起來,輕的一拉就能拽好遠,他大手桎梏在細瘦的手腕上都不敢太用力,真怕他一個用力,的手腕就會斷掉。
.等到了臥室,他手臂上的力量用力一甩,便將手無縛之力的如可扔在了床上。
.....
猜你喜歡
-
完結2579 章
蝕骨危情:爹地,媽咪又跑了
被親人設計陷害,替罪入牢,葉如兮一夕之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監獄產子,骨肉分離,繼妹帶走孩子,頂替身份成了謝總的未婚妻。六年監獄,葉如兮恨,恨不得吃血扒肉。一朝出獄,她發現繼妹和謝總的兒子竟和自己的女兒長得一模一樣……在眾人眼中不解風情,冷漠至極的謝總某一天宣佈退婚,將神秘女人壁咚在角落裡。葉如兮掙紮低喘:“謝總,請你自重!”謝池鋮勾唇輕笑,聲音暗啞:“乖,這一次冇找錯人。”一男一女兩個萌娃:“爹地,媽咪帶著小寶寶離家出走啦!”
230.7萬字7.35 475716 -
完結787 章

閃婚密愛:我的老公是大佬
童年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總裁夫人,更不會想到這位總裁竟然是自己上司的上司。幸虧她只是個小職員,跟這位總裁沒什麼交集。要不然她跟總裁隱婚的消息遲早得露餡。不過童年想方設法的隱瞞自己的婚史,總裁倒是想方設法的證明自己結婚的事實。 “當初不是說好了對外隱婚,你巴不得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面對童年的掐腰質問,許錦城戴上耳機看文件假裝聽不到。反正證已經領到手了,童年現在想反悔也沒用了。某人露出了深不可測的笑容。
100.6萬字8 34339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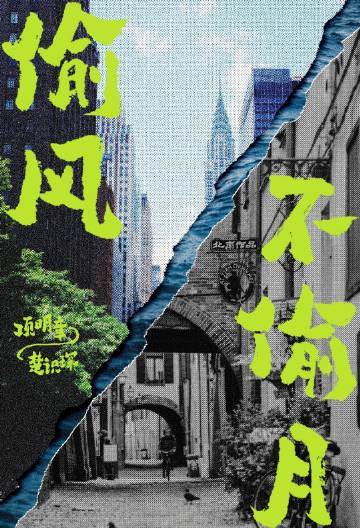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511 章

大院嬌妻純又欲,高冷硬漢破戒了
軍婚+先婚后愛一睜眼,溫淺穿成了八十年代小軍嫂。原主名聲壞、人緣差,在家屬院作天作地、人嫌狗厭,夫妻感情冷若冰山。開局就是一手爛牌!溫淺表示拿到爛牌不要慌,看她如何將一手爛牌打得精彩絕倫,做生意、拿訂單、開工廠、上大學、買房投資等升值,文工團里當大腕,一步步從聲名狼藉的小媳婦變成納稅大戶,憑著自己的一雙手打下一片天。——周時凜,全軍最強飛行員,他不喜歡這個算計了自己的妻子,不喜歡她年紀小,更不喜歡她長得嬌。初見紅顏都是禍水!后來媳婦只能禍害我!
94.6萬字8.18 10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