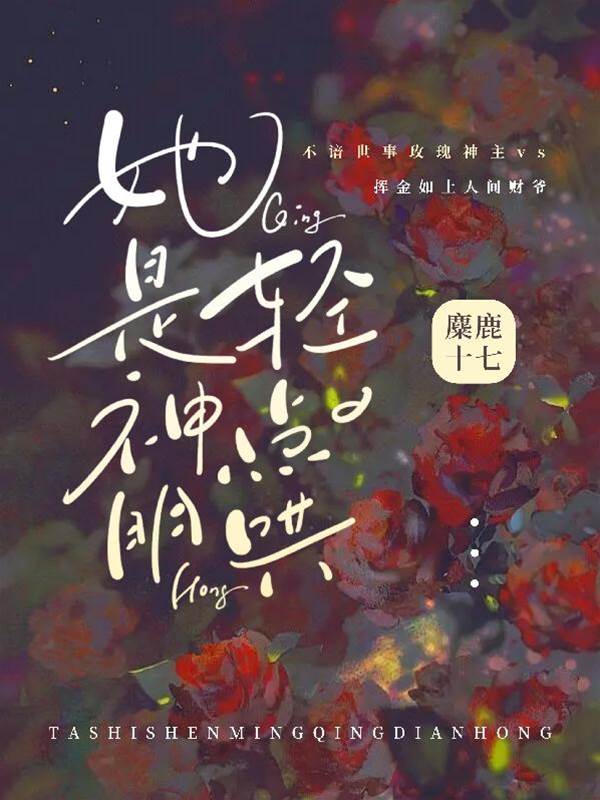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禁欲大佬他淪陷了》 第212章 她得這個病,是因為我
那一下下,都打在聿執的口,沉悶、有力,用了十足的力氣,不可能不疼。
許言傾完全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就看到汪詩詩一夜之間,好像瘋了。
而聿執那麼矜貴的一個人,居然也任由打,手上的有幾滴濺到了男人的領口上、臉上,斑駁的漬涂染開。許言傾看了眼他的表,冷到蝕骨。
汪詩詩打累了,往下坐到地上,爬不起來,就用雙手雙爬著回到原來的地方。
許言傾看到抱著一個壇子,哭得撕心裂肺,兩手拭著上面的泥漬。
泥地黏著壇,看來那壇子埋的時間長了。
汪詩詩喊著一個名字,是個男人的名字。
江懷拎了一個急救箱過來,聿執翻出紗布,走過去想給包扎。
“走啊,走開——”
汪詩詩滿眼都是恨,疼痛肆意撕開了那張漂亮的臉蛋,“我不要你假惺惺的,你們都騙我,為什麼!”
許言傾站在雨幕中,江懷替打著傘。
他看著聿執一次次被推開,但他不打算不管,也很執拗。
“江懷,你能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嗎?”
有雨珠順著傘骨往下掉,許言傾看在眼里的人影,也不再是完整的。
江懷一瞬不瞬地盯著汪詩詩懷里的壇子,“那里面裝著的,是汪小姐的男朋友。”
“就是之前說的,跟有著紋的男友嗎?”
許言傾不由唏噓,鼻子跟著發酸,還記得那晚汪詩詩說起這個紋時,臉上笑得有多開心。
江懷點了頭,“我跟汪小姐的男朋友,都是跟著小爺的。三年前他替小爺外出辦事,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撐不住了。唯一的愿就是瞞著汪小姐,告訴,他還活著。他說想要一輩子陪著,就讓小爺把骨灰埋在了離最近的地方。”
Advertisement
許言傾聽著一個字一個字蹦進了耳朵里,有些膽戰心驚,有些害怕。
聿執也有些惱了,強行按住汪詩詩,把紗布往手臂上裹。
汪詩詩在地上打滾,用腳踹他,聿執氣得毫無法子。
“那他這一路走來,是不是很崎嶇危險?”
“你說的是小爺嗎?”
許言傾看到聿執上都了,他站在那里,雨水嘩嘩地沖刷過他的臉龐、肩頭。
“嗯。”給了一聲很輕的回應。
“名利場,也就是最殘酷的角斗場,群狼環伺,天天同猛斗,同最狡猾的狐貍斗。倘若自修煉不夠,那被一口吞掉的悲劇,每天都在發生。”
許言傾從江懷手里接過傘,經過了聿執的面前,然后蹲了下去。
汪詩詩沖看眼,撲過去將抱住,“我等了他三年啊,每天都在等他回來,現在你們告訴我他死了……”
“他居然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的院子里,哈哈哈——”
換了許言傾,也會瘋。
一手摟汪詩詩,將抱到懷里,許言傾沒法安,那就讓發泄吧,大哭一場,或者大病一場,都無所謂。
只要別去死,保著這條命就好。
四合院的檐角,搭著古古香的青磚,雨水順著瓦楞往下落,滴滴答答落到地上。
房間,許言傾幫汪詩詩換掉了的服,幫干子,泡了一杯姜茶。
床頭柜上,擺著那個已經沖洗干凈的壇子,汪詩詩了眼許言傾正在忙碌的影。
“別勸我了,我活不下去了。”
屋外的走廊上,聿執靠著窗邊正在煙。
他一步不敢離開,雨水的氣拼了命地通過窗的隙往里鉆,而屋兩人的對話,也在縷縷往外。
Advertisement
“他至在陪你的這一程,把最好的自己都給你了。”
“那又怎樣,還不是拋下我走了?”汪詩詩這會渾無力,說話聲也很弱。
許言傾坐在床邊,雙手撐在側,“那你怨恨他嗎?可最不能怨的就是他啊,他是想留在你邊的,哪怕是以這種方式……”
的目挪過去,到了那個壇子。
“他看到你這樣,他會哭的。”
“他都死了!”
許言傾不善安人,“死人也會哭吧,因為親人人的想念、眼淚,使得他們不愿意離開。其實很多時候,是活著的人心有執念……”
汪詩詩哭得眼睛紅腫,“那你呢,我知道你有個妹妹。”
垂下了眼簾,聿執聽到屋許久沒有聲音。
許言傾盯著自己的腳尖看,“有時候我在想,我想讓安安活著,這是不是也是我的執念?”
“可病得那麼重,即便有一天……那也不是你的錯啊。”
許言傾手在被褥上掐下去,“可得這個病,是因為我……”
屋外,聿執又焚了一支煙,煙灰落在窗欞上,薄溢出淡淡的白霧。
“那會我還小,不懂,但我幫家里人干活。那時候醫院開的藥,還是用紙袋子裝著的。媽媽懷孕了,孕吐得厲害……”
許言傾想起那一段,心悸,也不愿意去回憶起來。
“我桌子的時候把桌上的兩袋藥灑了,我一顆顆撿起來,那些藥片都長得差不多,圓滾滾的,白的。是我把藥片混淆了,我把它們裝回了袋子里……”
許言傾聲音抑得很,“我們家沒有這方面的傳,可偏偏我妹妹就得了心臟病。”
那時候的產檢比較簡單,總有紕的時候,誰都不知道許安會病那樣。
Advertisement
“我爸媽從來沒跟我說過,更沒怪過我,是我有一次半夜醒來,聽到他們在議論。”
許言傾垮著雙肩,小時候很天真,還想過要把自己的心給許安。
聿執抿著一口煙,聽到煙燃燒的聲音呼鼻腔,難怪,為了許安的病都能豁得出去。
許安于許言傾而言,不止是妹妹這麼簡單。
汪詩詩臉沾著枕頭,半邊枕巾都了。
“他們跟我說……小爺本來想全力施救的,哪怕是缺了手腳都無所謂。可他不愿意。他全都被燒焦了,那麼多人都想讓他活著,只有他自己,他想死。”
汪詩詩說到這,哽咽到說不出話來。
許言傾彎下腰抱住,“那就讓他走吧。”
“我不……我要是在場,我會以死相,讓他活下去!”
“別這樣,讓他走吧。”
如果真能活,他一定不愿意放棄這個機會的。
有時候,人需要同自己和解,許言傾地抱著汪詩詩,只是到了這一刻,才醒悟過來。
也許在安安能否活著的這件事上,許言傾也需要跟自己和解。
猜你喜歡
-
完結551 章

總裁聽我的
顏可欣單槍匹馬去找未婚夫尋歡作樂的證據卻沒想被吃干抹凈血本無歸反擊不成?那逃總可以了卻沒想這男人恬不知恥找上門,百般無賴的表示。“睡了我,還想就這麼跑了嗎?”
97.1萬字8 19077 -
完結242 章

冷少的逃跑嬌妻
在陸琪琪20歲生日那天,不小心誤睡了總裁,還將他當成了牛郎,隨后甩下100塊大洋離開。向來不注重感情的冷慕晨卻對陸琪琪香腸掛肚了5年。5年后,陸琪琪帶著天才可愛寶寶回國,再次偶遇了冷慕晨——“5年前,我讓你逃走了,這一次,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了的。”冷慕晨對著陸琪琪愣愣的說道。
56.9萬字8.14 28173 -
完結1094 章

南太太馬甲A爆了
父母從小雙亡,蘇清歡從小受盡各種寵愛,來到城市卻被誤以為是鄉下來的。姑姑是國際級別影后,干爹是世界首富。蘇清歡不僅在十五歲時就已經畢業修得雙學位,更是頂級神秘婚紗設計師Lily,世界第一賽車手,頂級黑客H。當蘇清歡遇上南家五個少爺,少爺們紛紛嗤之以鼻……直到蘇清歡馬甲一個個暴露,五位少爺對她從嫌棄分別轉變成了喜歡愛慕崇拜各種……
193.8萬字8 127400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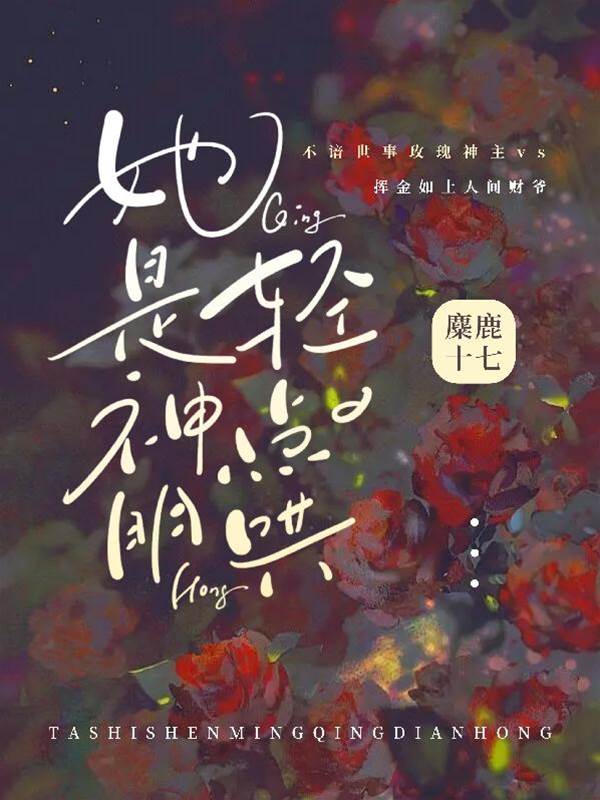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連載138 章

蓄意嬌養誘她入懷
【蓄謀已久+甜寵 + 曖昧拉扯 + 雙潔1V1 + 6歲年齡差】【人間水蜜桃x悶騷高嶺花】 南知做夢也沒想到,真假千金這種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狗血的是,她被下藥,把叫了12年的顧家小叔叔給睡了。 怎麼辦?跑路唄。 花光積蓄在暗網更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親手養大的水蜜桃,剛啃了一口,長腿跑了。 找她了三年的顧北期忍著怒氣,把她抵在車座角落,“睡了就跑,我算什麼?” 南知:“算…算你倒霉?” 顧北期:“這事兒怪我,教你那麼多,唯獨沒教過怎麼談戀愛。” 南知:“你自己都沒談過,怎麼教我?” 顧北期:“不如咱倆談,彼此學習,互相摸索。” - 顧家小三爺生性涼薄,親緣淺淡。 唯獨對那個跟自己侄子定了娃娃親的小姑娘不同。 他謀算多年,費盡心思,卻敵不過天意。 被家人找到的南知再次失蹤。 在她訂婚宴上,男人一步一句地乞求,“不是說再也不會離開我?懷了我的崽,怎麼能嫁別人。”
1.8萬字8 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