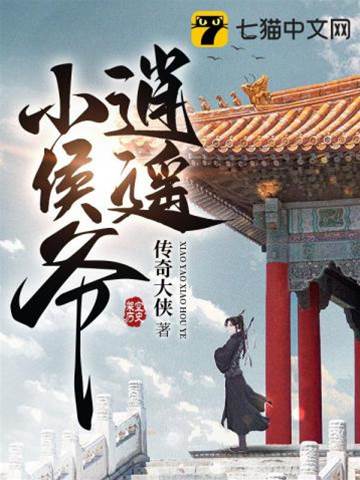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名醫貴女》 125,教育(萬更,求票哦)
嶽縣北郊,分佈著幾家農戶。
邊郊的農戶和村中的農戶不一樣,並非是每一戶房子挨,而是自家守著自家的田地,於是,房屋排列就較爲鬆散。
此時爲冬季,放眼一銀白一片,蘇漣漪不知此地的緯度爲多,竟會如此嚴寒,但聽說岳縣在鸞國中部偏東北,想來,是古時沒有溫室效應,所以比現代要寒冷許多罷。
漣漪將馬車簾子撂了下來,回頭看向那穿著紅披風的小子。“初螢,大晚上的,你帶我來這做什麼?”
初螢微微一笑,算了一下時辰正好,“你彆著急,一會便有好戲看。”說完,又代了車伕,在偏僻的一停下。
漣漪一頭霧水,便又將馬車簾子掀開一條小想外看,只見,馬車正前方是一間農家房屋,屋子不大,以在蘇家村居住的經驗來看,那屋子雖燈火通明,但其實平日卻鮮人居住,只因,院子中太過乾淨。
若是住人的屋子,在院子中定然要堆積一些平日裡用的工等,但這院子空無一,可見這家人已經搬走。
漣漪忍不住又回頭問,“初螢……”
“噓,”初螢打斷了的話,微微一笑,“你看。”說著,指著前方。
漣漪趕忙看過去,竟發現,從遠方來了一輛馬車。此時天已全黑,好在月圓亮,在銀的月下,那豪華的馬車如同從天上來,和這農家小院極爲不搭調,初螢到底讓看什麼?
當再一次定睛一看時,竟發現,那是李家的馬車。
蘇漣漪睜大了眼,看見車伕先是下車擺放車凳,而後一襲白之人從車廂鑽了出來。若那人穿著別的,也許看不清,但白的服在這黑夜中十分扎眼,何況其料是特殊的錦緞,更是被月照得盈白。
Advertisement
李玉堂!?他來這做什麼?
蘇漣漪的馬車通爲黑,馬車也不大,在一旁,兩棵樹後,無論是車上之人、車伕,還是拉車的那匹黑馬,都十分安靜,人外本發現不到。
只見,被李玉堂低聲吩咐,待他下了車,車伕載著墨濃便退到了一側,不再擋在這院子門口。這樣,便與漣漪的馬車距離拉開,更是無法發現漣漪。
那房燈火通明,應該有人在裡等待,卻不知是何人等候李玉堂。
漣漪的眉頭微微一皺,好奇地回頭看向初螢,“你的意思是說,有人想聯合李玉堂打擊我?但爲何要三更半夜在這偏僻的農戶見面?”只以爲是商業謀,哪能想到這是初螢想教導人心的險惡?
初螢微微一笑,“別急,一會你便知曉了。”的笑容神莫測、意味深長。
……
李玉堂懷著一顆忐忑又期待的心下了馬車,到了約定的房屋門口,當手剛要到那門時,理智終於戰勝了那瘋狂,開始發揮了作用。
他閉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氣,讓自己冷靜。漣漪的字跡因沒有自己的筆,如同孩的字跡一般,很好模仿。只要稍有些功底之人都能模仿得出,何況,將他半夜出私會,本就不是蘇漣漪的作風。
他在掙扎,理智告訴自己這他所來之人本不是蘇漣漪;但卻著他去上當,且心甘願的上當。
最後一次深吸氣,那白皙修長的手出,在門上敲了一敲,立刻,那門扉打開,出了一張嫵妖嬈的臉。
“李公子,快請進。”那聲音纏綿,爲這夜增添了幾許曖昧,也足夠將男人的心抓得十分。
可惜,李玉堂卻未覺得這人、這聲有什麼妙,只是冷了眼,“你是蘇府的丫鬟。”他還記得這名子,從前去蘇府時,那名爲初螢的子讓其在旁伺候,何爲會在此?
Advertisement
李玉堂隨即便猜出了個七八分,因他也在深宅大院出生,這種小把戲也見得多了。
若是平時,他轉便走,但如今他卻發現這種種太多,他必須要調查清楚,因爲這關係到蘇漣漪,這丫鬟只是個引子,其後定然還有人致使,他無法容忍漣漪邊有危險。
掙扎了一下,便了房屋,那門隨即也關了上。
初螢冷冷一笑,嘆了口氣,“原本我以爲這李玉堂是個種,原來也是個胚子。”隨後又譏諷一笑,好像是想到了自己的境,“罷了,也許男人也不過如此,送上門來的爲何不要?男人呵。”
漣漪能覺到初螢的悲觀,手將冰涼的小手握在手心,卻不知如何安。難道要說初螢遇人不淑?這不是在傷口上撒鹽嗎?
本就不是能言善辯之人,更不會安人,能做的,也許只能是將初螢的手握,告訴初螢,永遠都支持初螢罷了。
漣漪心中疼惜自己朋友的命運,但又忍不住納悶,那房是什麼人,李玉堂敲門,房門開了,李玉堂連問都不問直接,看來兩人定然是認識、勾結,難道真是初螢發現了什麼?
房。
那守株待兔的子正是詩北無誤,今日的詩北拿出了自己所有積蓄,添置了一件好子,面孔上濃妝淡抹,本就嫵妖嬈的容貌此時更是豔無比。
當看到那俊人的李家公子了房間時,簡直如同做夢一般,子都了半邊。
李玉堂連正眼都沒看一眼,“誰讓你來的。”冰冷道。
詩北一愣,隨後又是嫵之笑,“李公子,天寒地凍,讓奴婢爲您暖暖子吧。”說著,便準備迎上去。
Advertisement
李玉堂一手,將詩北推出了好遠,從懷中掏出一封信,正是用漣漪名義將他約出來的信。“這信,是誰寫的?”
詩北那雙嫵的大眼微微了一,知曉李公子這是準備興師問罪了,不會給他這個機會的。
想著,又是嫵一笑,“李公子,是這樣,二小姐今日太忙,也許要遲上一些,生怕李公子等得急了,便讓奴婢先在此等候,天寒地凍,奴婢這就沏一壺熱茶爲李公子暖。”
說完,也不等李玉堂同意與否,直接衝出了屋去,到了廚房,廚房有水壺,應是從前那戶人家留下,便在井中打了水,點火燒水。
這些活,從前是不會幹的,畢竟以的容貌和眼裡,都是伺候主子的。卻被那天殺的初螢賤人著在廚房中做活。
院子外,馬車,漣漪見門開了,有子從中出來,不解。再仔細一看,那人形看著眼,“是……”
初螢邪魅一笑,“詩北。”
這一下,漣漪算是徹徹底底明白初螢想幹什麼了,哭笑不得,“我說我的大公主,你想整詩北我是知道的,至於大費周折嗎,還把李公子牽連進來。”
初螢別有神地笑了一下,“若不是李公子進來,你是看不到人心險惡的,彆著急,一會我就讓你看到,這些賤人心底的卑鄙。”
漣漪雖不是很贊同,但卻知曉初螢是爲好。確實心,承認,因爲和初螢這些在古代從小爭鬥之人不同。現代社會雖也有一些明爭暗鬥卻本比不上古代殺人不見的爭鬥。
僅僅是個普通現代人,今日若不是蘇漣漪穿越到此,換任何一個現代子,也都這樣。
Advertisement
在現代連都不敢殺,跑古代就可以毫不心驚膽戰地奪人命?好吧,敢殺,卻不敢害人。
不大一會,廚房中水燒好了,詩北從懷中掏出了在蘇府出的上好茶葉,沏了壺茶,又從腰帶的小包裡拿出了一隻小小紙包,脣角勾著一抹笑,將那紙包之也投茶壺之中。
紙包中不是別的,正是春藥,只要那李公子喝了這茶,中了藥,生米煮飯,他也就不得不認了吧?何況,容貌自認尚佳,到時候再跪地哀求不求名分,只求爲李公子爲奴爲婢,想必那李公子也不會拒絕。
可不是想換個地方當奴婢,而是在李公子邊,近水樓臺先得月,總有一天被擡個姨娘,那樣榮華富貴還會了?
漣漪看著詩北端著托盤,其上放著茶壺茶杯,眉頭忍不住皺起,“那壺中不會有什麼蒙汗藥之類得吧?”
初螢噗嗤一笑,“漣漪你也不傻嘛,這些賤人的手段,你也能想出。”
漣漪哭笑不得,“我從來都不傻啊。”這些狗的鏡頭,也許對古代人還算是新鮮,但在現代電視劇裡,十個故事八個春藥,就是用膝蓋都能猜到。
只不過……
漣漪看著那房間,“若真是什麼迷藥,這詩北就到大黴了。”
“爲何?”初螢不解,其實倒是希既事實,一箭雙鵰,也算是幫小叔擊倒一個強敵。
漣漪微微一笑,“因爲李玉堂的鼻子靈得很,無論是迷藥、春藥,一聞之下都能辨識,詩北最好別搞這些小作,否則恐怕吃不完兜著走。”
初螢一愣,“他能辨識,爲什麼?”
反正閒來無事,漣漪便將從前與李玉堂如何被李夫人暗害,李玉堂又如何帶著去藥房解了藥,都一一說了。後來也順便說了爲初螢找尋麻藥,也是這李玉堂幫忙。
初螢大驚失,以爲自己所有事都瞭如指掌,卻沒想到,漣漪爲了,竟做了這麼多。
趕忙抓住了漣漪的手,將其袖子擼起,果然,見漣漪那修長白皙的手臂上有著兩道淡淡的疤痕。又檢查了另一隻手,有著同樣得疤痕。子抖,一雙淡淡小眉皺起。
“漣漪……你……爲何要對我這麼好?”初螢的聲音吶吶,帶了些許抖。
漣漪有些後悔將後面一件事說出來,趕忙安,“沒什麼,都是小事。”
初螢擡起頭,瀲灩的大眼眼圈通紅,帶著一種說不出得迷茫和,看向蘇漣漪,“我從未想過,這天下竟有一人能爲我心甘願做這些事,真的……我從未想過會有……”說著,哽咽得難以再語。
別說的夫君,就說的父皇和母后,都不會!
“怎麼哭了?至於嗎?”漣漪趕忙掏出懷中手帕爲其眼淚,“你千萬別自責,其實我只是抱著對醫學實驗的嚴謹態度罷了。”手忙腳地安。
初螢忍不住哭,心頭的和幸福滿滿。
漣漪嘆氣,將放開,哭吧哭吧,哭完了就好了,誰讓自己不會安人?
就在這時,被監視房間的大門被猛地打開,一襲白的李玉堂從房中出來,後跟著的踉蹌的詩北,哀求著哭著,說自己願,等等。
初螢此時有一些後悔,原本以爲李玉堂就是個肖想蘇漣漪的富家子弟,但剛剛漣漪將從前發生之事說出才知曉,李玉堂是個不錯的男子,何況他也算是間接救了和熙瞳的命。
畢竟,若非李玉堂,漣漪也找不到那些麻藥。
乾了淚,一車簾,下了車去。漣漪也趕忙跟著。
李玉堂正準備向自家馬車而去,不再管這不安分的丫鬟,也懶得再去追究那信到底是誰寫的,另一側卻有了響,一擡頭,很是一驚,因爲,向他走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初螢和蘇漣漪。
他不自覺停下腳步,回頭疑地看了一眼詩北,又看了一眼蘇漣漪,不解。
漣漪只覺得對李公子無言以對,慚愧地低了頭去,心中將初螢責備了一百零八遍。
初螢已重新帶上了咄咄人的面,似笑非笑地看著詩北,“真是一場好戲,詩北,你爲我的丫鬟,怎麼不在蘇府卻出現在這裡?”
李玉堂冷冷看了一眼初螢,心中猜想這一切都是這人所爲。在他心中,這子非即盜,漣漪待如同親姐妹一般,卻在背後做這種小作。
漣漪也不懂初螢轉了一圈到底想做什麼。
詩北啞口無言,腦子中轉得飛快。驚恐地看了看初螢,又看了一眼蘇漣漪,銀牙暗咬。
漣漪正想著如何將這場圓了,先解決了燃眉之急,再回家責備初螢。卻看見,那詩北走幾步到初螢面前,噗通跪倒,“初螢小姐開恩,這些都是……二小姐讓奴婢做的。”
蘇漣漪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回事?“詩北你瘋了?我讓你做什麼了?”一頭霧水,這到底事怎麼回事?
李玉堂也驚訝,原本很明瞭的態勢,如今卻看不清了。
初螢帶著淡笑,“哦?二小姐讓你做的?二小姐讓你做了什麼呢?”好像是配合詩北演戲一般。
那詩北明知前途兇險,但卻自有一套自己的判斷標準,“回初螢小姐,二小姐的意思是讓奴婢爲李公子下了春藥,而後二小姐來……就……就……”
蘇漣漪驚訝得忍不住長大了,“詩北,你有神經病嗎?我什麼時候讓你幹這種事了?”這詩北絕對是瘋了,明明一切都是初螢讓做的,難道這也是初螢計劃中的一步?初螢到底想做什麼?
疑問地看向初螢,初螢想害?但這樣下去,也沒什麼損害。難道初螢想破壞在李玉堂心中的印象?但這有必要嗎?不解!
李玉堂也是一愣,他徹底懵了。若是換了其他事,他自能明察秋毫,但一旦是牽扯到了蘇漣漪,他的腦子就不聽了使喚。
那詩北看了一眼初螢小姐,見眼中帶著讚許的笑意,便堅定了這栽贓的心。“就是二小姐,二小姐難道您忘了?前一日夜晚,您從初螢小姐的院子出來後,將奴婢到偏僻,代今日讓奴婢這麼做的。”
詩北心中是怎麼想的?雖不知這二小姐和初螢小姐之間到底是何種誼,既不是姐妹,又不是妯娌,卻日日相得如此好。但自從前幾日二小姐不知何故離開縣城半月,而初螢小姐接手了二小姐的生意,便逐漸有了一種猜測。
初螢小姐本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般簡單,尤其是對和對二小姐時,態度完全是判若兩人,人心險惡,認爲,初螢小姐是在暗暗架空二小姐的勢力,將這些生意、財產用巧妙的手段納爲己有。
而如今讓做的,便是挑撥二小姐和李公子之間的關係。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而詩北的秤便是偏向那種強勢的主子。因爲只有強勢的主子才能護下人們周全,那些心愚善的,往往自難保不說,下人們也是護不住的。
從前在有錢人家深宅後院伺候,這樣的事見多了。寧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所以,如今便只能委屈無辜的二小姐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連載617 章
大唐醫王
一個現代醫師回到貞觀年間,他能做些什麼?如果他正好還成爲了李淵的兒子,李世民的弟弟呢?李元嘉,大唐醫王。
117.4萬字8 29994 -
完結195 章
嗜寵夜王狂妃
世人皆傳:“相府嫡女,醜陋無鹽,懦弱無能”“她不但克父克母,還是個剋夫的不祥之人”“她一無是處,是凌家的廢物”但又有誰知道,一朝穿越,她成了藏得最深的那個!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傾城容顏,絕世武藝,腹黑無恥,我行我素。他是帝國的絕世王爺,姿容無雙,天生異瞳,冷血絕情,翻手雲覆手雨,卻寵她入骨,愛
74.8萬字7.92 52514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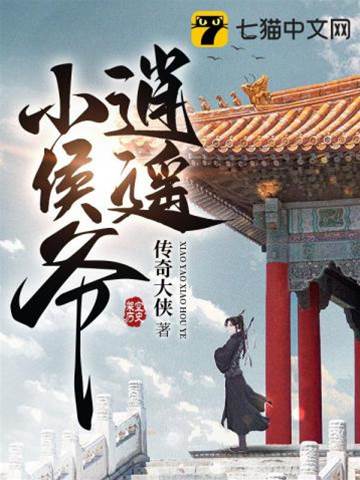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