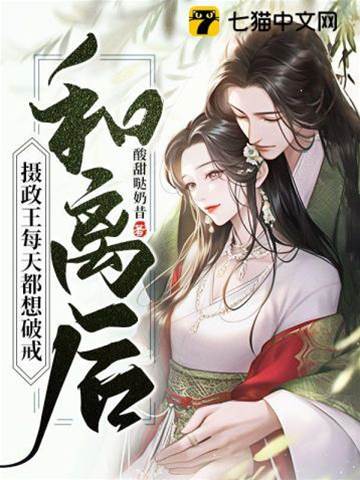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締婚》 第34章 第 34 章
譚廷當晚宿在了外院書房,閉起眼睛,眼簾上便浮現項寓的那行字——
小弟只想八月早早到來,一舉登科,長姐就不必再為小弟學業擔憂,也可自那譚家離開了。
譚家大爺何時睡下的,項宜在院自然不知道。
譚家大爺提起太子邊道人的話之後,就沒了下文。
不過項宜也謹慎地,一時沒有出門的打算。
收到了弟弟妹妹自青舟的來信。
此前,沒有同弟妹提及義兄重傷來此的事,自然弟弟妹妹的這次信里也不會提到。
項宜並未多想,晚間時間,在桌案前,慢慢給他們回了信。
......
翌日,項宜仍舊早早去了花廳理事。
花廳外的小池塘邊,開了一叢白梅,映著水純秀生姿。
譚廷路過的時候,在白梅后定住了腳步。
梅影外的花廳里,他看見一如往日般安然坐在上首,下面魚貫進來人挨個回事,不不慢地挨個點著問了,依次分發對牌。
今日穿了之前的杏長襖並比甲,發間也沒有過多點綴,帶著尋常的銀簪。
就如同這白梅一般清秀。
只是譚廷置辦的那些,今日一件都沒有穿戴在。
譚廷了角,又在梅樹前看了幾息,才回了書房。
蕭觀已將書信擺在了他案頭。
譚廷看著信沉默了許久,才打開了來。
現在信中回復了項寧,亦提了幾件日常事宜,又問及項寧近來的狀況,囑咐若是項寓不在家,莫往人去,今歲奇寒,不知世道會否變,多加小心總沒錯,然後又說了開春換藥的事。
囑咐完妹妹,才回了項寓的那頁紙。
對於自己父親項直淵和知府廖秋的事,並未在信中多言,只提醒項寓,可以通過書院師長,將維平府不安之況,上達天聽。
Advertisement
青舟書院雖然崛起時候不長,但因著是寒門學子讀書的地方,頗得朝中寒門出之員的支持,與這些庶族出的員,亦相甚好。
譚廷看著信中的提議——
對這些事,雖未細論,卻將其中要關係,點得清清楚楚。
維平知府廖秋是庶族平民出的讀書人,但卻是因著投靠世家才出了頭,尋常百姓如何能讓他去治理之下胡作非為的世家,但真正為寒門庶族著想的同樣出的員卻可以。
譚廷不由想到了雲河大堤修繕時,項寓送來的數目記載。
那是項寓想到的,還是......項宜呢?
譚廷腦海中妻子的形象,一時間有些許變幻。
他又繼續向下看去。
繼續回應了項寓讀書的問題,這番只給了他四個字,「戒驕戒躁」。
科舉不是一日之功。要比項寓清醒又明白得多。
只是說完這個,信已經見了底。
譚廷目緩緩移了過去,落在了最後的話語上。
指腹按著佈滿筆跡的信紙,默然。
房中安靜下來,他看到回了項寓那提議。
「至於離開譚家之事,此時言語為時尚早,你安心讀書,此事往後再議。」
沒有細說,可也彷彿說了明白。
庭院裏的零星鳥鳴遠去了,很快與風聲一起消失無影。
會離開,離開譚家也離開他,只是眼下不是時候罷了。
譚廷閉起眼睛,黑暗的視線里,許多緒決堤似地涌了出來,在心頭上不斷泛濫,最後凝了一個巨大而沉重的黑石,在心口之上。
的字跡不似項寓一般凌厲,可一筆一劃,都像是刻在人心頭一樣。
譚廷下意識也想似看項寓的信時那樣,一字一句地再看清楚,可他卻多一個字都看不下去了。
Advertisement
他了蕭觀進來收信,抬腳向外走去。
天上烏雲層層疊疊地著,似是要下雪了,風在原地盤旋著,沒有緩解任何冷凝而沉悶的氣息。
他想尋一個風能吹散沉悶的地方,腳下離開了外院書房,只是不知怎麼,竟回到了來時的白梅樹旁。
從白梅樹影間往不遠的花廳看去,一眼就能看到了花廳上首的那個人。
下面的僕從都已經散了,輕輕點了點剩下的對牌,讓喬荇用匣子仔細裝好,起了。
天要下雪了,今歲的冬日,一場一場的寒冷像沒有盡頭似得,如浪拍來。
站在花廳前仰頭看了看灰濛濛的天。
固執穿在上的舊越發顯得單薄起來。
譚廷不由地想了起來,櫃里的衫滿滿當當的,可不用出門替譚家行事,或者不必去族中照看的時候,多半還是穿著自己平日裏的舊。
首飾也是一樣。
不似妹妹譚蓉,將他從京裏帶回來的頭面拆各種式樣,每日裏換著髮飾戴出來。
可,卻只在某些人多或者要的場合,才正經戴上幾支。
之前還會戴一戴珍珠頭面里的珍珠耳飾,似乎自從楊蓁買了一套珍珠耳飾,送了兩對之後,他送的那套珍珠頭面里的耳飾,就再沒過了。
風吹得人越發冷了。
雜的思緒在腦海中起起伏伏,譚廷不知自己怎麼就隨著的腳步到了正院,站在了正房廊下門前。
他沒有開簾子進去,卻聽見裏面吩咐喬荇的聲音。
的聲音一貫淡淡的沒有什麼緒。
「年前年後我忙了些,只做了一個尋常小印,你同姜掌柜說,待開了春,會再做些能賣上價的來。」
喬荇應了,又忍不住勸,「夫人這些日太辛苦了,連看閑書的工夫都沒有了,二夫人您去打葉子牌,您也都推了,多該歇一歇的。」
Advertisement
天冷,楊蓁在家中閑悶發慌,不是練劍就是打牌。
但笑了笑,回了喬荇,「我又不是能閑下來的子。寧寧約莫病有些反覆,信中不提,字跡卻虛浮,我想等天暖了,再給換一副好些的葯,再者阿寓趕考也是需要有錢傍的......」
譚廷在這些話里,閉起了眼睛。
不管是弟弟科舉趕考,還是妹妹病反覆要換藥,都需要錢。
可不管是之前還是現在,都只是靠著自己,一刀一刀制印賺錢。
沒有跟他要過錢,連借都沒有過。
在信里最後回應項寓的話,此刻就像從口中說出來一樣,那淡然的嗓音,一遍一遍響在他耳邊。
譚廷不由想起自己剛回家時,樁樁件件事引發的查賬。
在查賬之前,就沒想過從他得到什麼,查賬之後,更是一點一滴都沒有了。
譚廷垂了眸,沒再打擾,在那扇門打開之前避開了。
......
哪怕是十五的元宵節,因著今歲嚴冬難過,都蕭索了起來。
楊蓁乘興而去,差點敗興而歸。
不過是個樂善好施的,見縣城街市上實在沒什麼好玩的,便讓人支了個攤子給路人套圈。
把圈弄得極大,幾乎人人都能套到東西拿回去。
這般可把路另一邊的套圈小販急壞了,那麼冷的天,小販急了一的汗。
楊蓁看得哈哈大笑,讓人抓了一把碎銀子給他,直接把他的攤子也盤到了自己這邊來。
小販一看,喜笑開地連聲道謝,還幫著楊蓁做起事來。
譚建在家裏完全坐不住了,簡直用平日裏三五倍的速度寫完了大哥佈置的文章,一時管不上寫這般會被大哥怎樣訓斥,便急著去了街市尋自家娘子。
蕭索的街市到了楊蓁這裏竟堵得水泄不通,譚建一看出門帶著的鼓鼓錢袋,眼下完全癟了下去,驚訝得不行。
Advertisement
倒是笑瞇瞇地看著路人手裏滿滿當當地,行走之間又熱鬧了起來,悠悠嘆了一句。
「這般熱鬧才好啊。」
夜風吹得滿街通亮的燈籠搖搖晃晃,譚建拿了個大紅披風將整個人裹了起來,看著小臉紅彤彤的,了手出來。
譚建驚訝又好笑,「癟了自己的錢袋還不夠,還要花我的繼續做散財子?娘子饒了我罷!」
楊蓁呸了他一聲,「誰要花你的錢做散財子了?我跟大嫂說要買燈給,但好像也被人套了去了,得再給嫂嫂重新買一盞好的。」
譚建一聽是這個原因,就把錢袋子拿了出來。
「娘子隨便買吧,給自己也買一盞!」
「嘖嘖,窮鬼也就有個買燈錢了!」
楊蓁朝他吐舌,揣了他的錢袋子,給大嫂買燈去了。
項宜在家並未閑著,因著每歲燈節,多要出點事,來回吩咐了好幾遍,千萬注意火燭,各留好水,莫要結凍了冰,萬一著了火及時撲滅。
等來回吩咐好了,回到了房中,看到茶幾上悄然放了一盞琉璃燈。
項宜見了那琉璃燈,便笑著問了下面的人,「二夫人這麼快就回來了?」
下面的人卻不甚清楚,道去夏英軒問問。
項宜讓他們去了,順便問問楊蓁他們玩的如何。
上前好生瞧了瞧那燈,燈是梅花樣的,做的緻亮。
難得有興緻挑了那盞梅樣琉璃燈,在院子裏走了幾步。
那燈剔晶瑩,中間點了蠟燭,越發映得挑燈的人,衫都流溢彩起來。
春筍和喬荇都走過來,圍著這燈連道漂亮。
項宜亦點了點頭,彎了眼睛笑起來,。
「弟妹總能尋些讓人喜歡的東西。」
又難得雅興十足地提著燈,在院子旁的小潭下走了幾步。
潭水早就結了冰,但琉璃燈的彩映在剔的冰上,又是別樣的景緻了。
項宜挑了半刻鐘的燈,才回了房,就將那梅樣琉璃燈放在自己制印的書案上。
過了好一陣,去了夏英軒的丫鬟才回來。
只是丫鬟回來時,手中也提了另一盞琉璃燈。
丫鬟道,「回夫人,二夫人和二爺剛回來,這是二夫人專門送給夫人的琉璃燈。」
項宜坐在桌前畫花樣,聞言一頓,訝然看了過去。
丫鬟手裏提著的琉璃燈才是楊蓁給的,那麼眼前這盞梅花琉璃燈又是誰的呢?
項宜晃了一下,才讓丫鬟放下燈,去夏英軒道謝。
看著眼前這盞自己提了好半天的琉璃燈,默了一默,吹熄了燈火。
梅花琉璃燈一下暗了下來,流溢彩消失了,項宜小心提起,原樣放回到了原。
......
今日是十五,還是正月里的十五。
譚廷沒有再宿在外院,在鼓安坊燈火逐漸熄滅時,回了正院。
項宜在暗想他今日到底回不回來時,就見到了他。
時候不早了,他這邊剛一回來,僕從便將燒好的水提了上來,供兩人洗漱。
譚廷看了妻子一眼,只是一轉頭,又看到了茶幾上的梅樣琉璃燈。
目落在燈上,男人眸一暗。
那燈就放在原,既沒有被點亮,也沒有被提起,甚至也許,都沒有被人多打量幾眼。
譚廷悶聲了角,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在信中所寫的話,又浮現在了腦海里。
兩人誰也沒有多言,夜如某個譚廷剛回家時的夜晚一樣,安靜的讓空氣都想要逃離。
直到洗漱完畢,蠟燭熄滅,帷帳將兩人在了狹小的空間里。
今日要做什麼,他們都知道,可一時間誰都沒有。
譚廷餘輕輕看了看枕邊的妻子,同往日的緒沒有任何分別,彷彿是如果他要,就會給。
但是今天,他也還能同往日一樣嗎?
譚廷忽然想要從這張床上離開,可又無法在這樣的日子裏離去。
床榻似覆了寒冰一樣,讓人無法安然躺下,譚廷第一次有這般覺,他不住了。
只是他一,手臂在了枕邊人的手臂上。
手臂一如往日冰涼。
譚廷不由地向看去。
項宜卻在此刻,意識到了什麼,低了低頭,解開了腰間的系帶。
只是下一息,譚廷突然出了聲。
「不必......」
項宜抬頭看了過去。
正房裏的夜晚寂靜異常。
譚廷在困的神里,心中抑制不住地掀起了大浪。
沒有留下的打算,或早或晚會離開,可他如果要,就可以這麼給嗎?
他誤會,不在乎;他查的賬,亦無波瀾;他愧疚想要補償,也無所謂一樣。
除了面對項寧項寓,在譚家甚有什麼緒。
從沒想過從譚家得到什麼,也沒有想過從他這個丈夫這裏,得到任何夫妻本該有的東西吧。
所以,只是想借一借譚家的勢,為此,把自己「抵」給了譚家......
這般念頭一出,譚廷再看到邊安安靜靜的妻子,心間似乎絞了起來。
他分不清這般絞痛的原因。
是他終於知道了,在眼裏,他們的夫妻是怎樣的關係;還是他難以想像,怎麼就捨得這樣對待自己......
他只是忍不住想要問一句,可是話到邊又被他咽了回去。
這是在譚家最後的保留了,他怎麼能將最後的保留,就這麼輕易說破呢?
他已經做了許多錯事了......
帷帳里的黑暗與寂靜,撕扯著人的緒。
譚廷收回了目,深吸一氣,似若無意地起了,嗓音低低地輕聲說了一句。
「我有點事,你先睡吧。」
項宜看著他的背影幾息。
而他在的視線里,果真走去了另一邊,便也沒再多問,睡下了。
*
翌日,楊蓁跑來問項宜花燈喜不喜歡,項宜自然道喜歡,也聽說了在街上做善財子的事。
「弟妹可是要出名了。」
楊蓁嘻嘻笑,「主要還是清崡縣太小,太不熱鬧了,大嫂在京城看過燈會嗎?簡直是這裏燈會的十個八個這麼大!」
項宜本是應該看過的,只是隨父親在京的那年,燈會還沒開始就走了水,宮裏見兆頭這般不好,臨時取消了燈會,項宜也就沒看了。
搖搖頭,楊蓁連道可惜,「等回頭大嫂隨大哥進京,到時候一定要看京城的燈會!」
項宜笑了笑,沒應這話。
譚廷進京,應該並不會帶著同去。
至於他的子嗣,雖然要,可譚廷年歲算不得大,等過幾年他正經想要子嗣的時候,自然是會有的。
只是那時,這譚家宗房又是另外的氣象了......
項宜邀了楊蓁在正院吃些點心,但楊蓁道與譚建約好一道練劍,便風風火火地走了。
項宜趁下晌無事的時候,出府去了一趟顧衍盛暫居的院落。
前腳一走,後腳蕭觀便來稟了譚廷。
......
街道上還有燈會延續下的幾分熱鬧。
項宜甚是謹慎,換了不起眼的裳混在人群里,不時到了偏僻院落。
譚廷從另一邊過來,護衛引他到了那院子甚是近的一顆樹下,恰能聽到幾分院中言語。
當先是見禮的聲音,譚廷聽見禮數周全,又是一陣暗暗鬆氣。
接著,便聽項宜問了一句。
「大哥這幾日好些了嗎?」
譚廷在稱呼里微怔。
大哥?
他暗想了一下,就聽小廝道爺好了許多,然後小廝又去門前通傳,不時開了門,有人走了出來。
此人不知為何,腳步沒走幾步便定了下來。
院院外不尋常地安靜了下來。
譚廷皺了皺眉,眼皮飛快地跳了一下。
院中,項宜沒能察覺什麼,看了一眼剛從房中走出來的大哥,剛要問問他傷,忽然見他笑了一聲。
他看向院外,朗聲說了一句。
「閣下既然追到了此,何不現?」
說完,示意了小廝秋鷹一眼。
「去開門,請客人進來喝杯茶罷。」
形陡轉,項宜見秋鷹當真快步往門前而去,睜大了眼睛,忍不住向門口看了過去。
院外。
譚廷聽見那聲,便曉得這院中人果真不是一般人。
原本今日,他是想等項宜從此離開,再現與明說的。
不過,既然那人如此警覺,他也沒必要再藏了。
他轉走出來,抬腳進了院子。
他走過去,便看到了訝然失的神。
譚廷抿了抿,剛要同說句「莫要害怕,我沒有怪你的意思」,就聽見廊下的男人,在他之前溫聲開了口,了一聲。
那人似乎是了的閨名。
「宜珍別怕,到我邊來。」
猜你喜歡
-
完結986 章

農門有喜無良夫君俏媳婦
東臨九公主天人之姿,才華驚艷,年僅十歲,盛名遠揚,東臨帝後視若珠寶,甚有傳位之意。東臨太子深感危機,趁著其十歲壽辰,逼宮造反弒君奪位。帝女臨危受命,帶先帝遺詔跟玉璽獨身逃亡,不料昏迷後被人販子以二兩價格賣給洛家當童養媳。聽聞她那位不曾謀麵的夫君,長得是兇神惡煞,可止小孩夜啼。本想卷鋪蓋逃路,誰知半路殺出個冷閻王說是她的相公,天天將她困在身旁,美其名曰,培養夫妻感情。很久以後,村中童謠這樣唱月雲兮哭唧唧,洛郎纔是小公舉。小農妻不可欺,夫婦二人永結心。
173.1萬字8.18 37020 -
完結237 章
重生后王妃咸魚了
沈妝兒前世得嫁當朝七皇子朱謙,朱謙英華內斂,氣度威赫,為京城姑娘的夢中郎君,沈妝兒一顆心撲在他身上,整日戰戰兢兢討好,小心翼翼伺候。不成想,朱謙忍辱負重娶出身小門小戶的她,只為避開鋒芒,韜光養晦,待一朝登基,便處心積慮將心愛的青梅竹馬接入皇宮為貴妃。沈妝兒熬得油盡燈枯死去。一朝睜眼,重生回來,她恰恰將朱謙的心尖尖青梅竹馬給“推”下看臺,朱謙一怒之下,禁了她的足。沈妝
37.5萬字8 18649 -
完結239 章
念卿卿(重生)
【男主篇】 梁知舟一生沉浮,越過屍山血海,最後大仇得報成了一手遮天的國公爺。 人人敬着他,人人又畏懼他,搜羅大批美人送入國公府,卻無一人被留下。 都說他冷心冷情不知情愛,卻沒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漫長的夜裏,是如何肖想自己弟弟的夫人,如癡如狂,無法自拔。 他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便是沒能阻止她成親,哪怕拼死將她救出,得到的只是一具屍骨。 所幸他重生了,這次那怕冒着大不韙,他也要將她搶回來。 沒有人比我愛你 在你不知道的歲月裏,我已經愛了你很多年 —— 【女主篇】 虞念清出身樂平候府,生得冰肌玉骨,容貌傾城,不僅家中和順,還有樁令人豔羨的好親事,京中無人不羨之妒之。 可無人知,她夜夜所夢,與現實恰恰相反。夢中,她那才學雙絕的未婚夫勾引她人,而素來對她慈愛有加的祖母卻爲了家族利益強逼她出嫁,再後來,母親兄長接連出事,一夜之間她引以爲傲的一切都成了鏡花水月。 夢醒後,爲了化險爲夷,虞念清將目光對準了前未婚夫的兄長—— 那個善弄權術,性子自私陰鷙的、喜怒不定的天子近臣,梁知舟。 虞念清膽顫心驚走過去,望着面前如鬆如竹的的男人,猶豫很長時間才下定決心問:“你能不能幫我?” 男人俯身捏起她的下頜,俊臉隱匿在陰影裏,看向她目光沉沉,“我從不做虧本的買賣,你可想好?” —— 【小劇場】 虞念清記錄日常的生活的小冊子被發現,上面這樣寫着: “梁知舟很危險,但是他願意幫我” “晚上做夢夢見了一個和梁知舟很像的人,他一直親我” “梁知舟變了樣子,我很怕他” “原來那幾次夢中親我的人都是他” “我想起我們的上輩子了” “他是壞人”(被劃掉) “他很愛我” “我想我也是”
39.5萬字8 2844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80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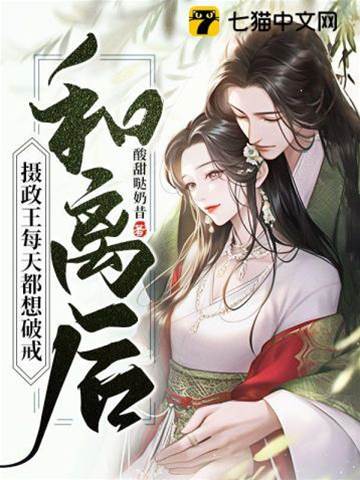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