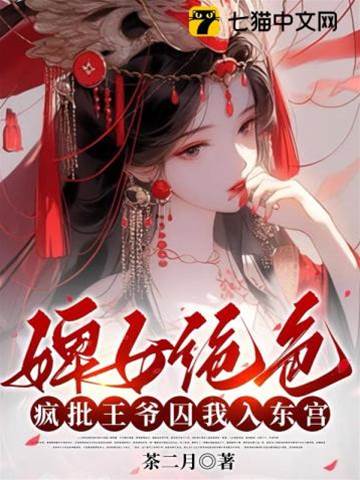《一念桃花》 一百八十九、冬去(一百六十九)
“不是當下,那是何時?”譙國公主奇怪地說,“早納晚納不都一樣?早點還能早生。說不定等你班師回朝,孩兒都落地了,大喜事一樁。”
裴淵有些納悶。
這位姑祖母,傳言行事大膽,無拘無束,如今看來,并無半點虛言。
“姑祖母誤會了。”他直言道,“我從未打算讓晚云做妾。我珍惜,等回去稟了父皇,便娶為妻。”
譙國公主看著裴淵,神吃驚不已。
“你要明正娶?”譙國公主大驚,“出微末,哪里配得上你?退一萬步,你縱是不計較,你父皇可會答應?”
“那是父皇的事。”裴淵冷靜道,“侄孫非不娶。”
“糊涂。”譙國公主沉下臉,“你父皇是何脾,你莫非不知?他若惱怒起來,你和晚云什麼都得不到。你尚且好說,堂堂皇子,自可什麼也不在乎。晚云卻要壞了名聲,日后誰敢娶?此事,你須聽我的,今日便納了。”
姜吾道在門外聽著,心中咯噔一想。
他不知這老婦人究竟是在打的什麼算盤,昨日還云兒長云兒短的,擺出一副樂見其的架勢,還教導他如何應對。不想今日就在裴淵這里宮,竟是非要他將晚云納妾。
裴淵不為所,道:“恕難從命。”
譙國公主冷笑一聲:“那就是不給我面子了?你知道,你父皇也不會忤逆我。”
裴淵跪地拜道:“求姑祖母收回命。”
譙國公主盯著他看了一會,悠悠地倚回榻上,再度冷笑一聲:“你倒是真像岳舒然。”
裴淵聽不明白這是夸他還是罵他,只道:“云兒的事,侄孫自會辦妥。只是剛才姑祖母的提議,侄孫萬萬不能答應。”
Advertisement
“哦?”譙國公主道,“你若日后果真納了呢?”
裴淵冷著臉:“姑祖母放心,侄孫言出必行。”
譙國公主淡淡道:“年輕兒郎,話不可說太滿。若真有了那麼一日,你會后悔不曾聽我告誡。”
裴淵卻從這話語里聽出了些意味,眉頭了。
“姑祖母何意?”他問。
“方才不是說了。”譙國公主道,“你父皇不會同意這樁親事。你既做不到,別耽擱晚云,放去吧。”
“我亦不能應。”裴淵道,“我也說了,此事我自有主張。”
“你有甚主張?”
“我讓亭認當妹妹。”
譙國公主笑了聲。
“你以為,你父皇反對,便是為了這門楣之事?”說。
裴淵出訝:“莫非不是?”
譙國公主搖頭:“其中淵源,比門楣深遠了去了。你自是不知,但你父親知道。”
裴淵不明白,忙拱手道:“請姑祖母賜教。”
“我聽聞,晚云你是小時候在山里揀到的。”譙國公主拿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文謙這樣有名的人,為何要認這個山野丫頭當徒弟,你覺不奇怪?”
是有些奇怪,可裴淵一直以為是巧合。
“云兒曾說,文公與他們家是世。”他說。
譙國公主笑笑:“什麼人能當文謙的世?我為何會在此給晚云做正賓,你不覺奇怪麼?”
此事,裴淵確實不知道。
譙國公主道:“你當真幸運,不小心撿到了寶。晚云可沒有半點配不起你。若父親當年沒有出走,功勛不輸孫放齡。”
裴淵的目定了定:“姑祖母是說,云兒的父親也曾是與父皇有牽連?”
Advertisement
“正是。”譙國公主嘆息一聲,遙遙憶起往事。
畢竟想起了許多回。待那歲月的烙印漸漸清晰,徐徐道:“此事,還須從前朝的吉貞十三年說起。那時,我已經二十七八歲,雖嫁了人,但膝下無子,便隨意在路上收養了兩個小。當初,我只將他們當貓狗作伴,但見這兩個小聰慧,便送他們學讀書。就是在哪里,他們結識了你父親。你父親是鎮南王世子,那兩個小則當了陪讀,長大之后,就了鎮南王府做了謀士。那兩人,一人王庭,一人常仲遠。”
裴淵的目一。
譙國公主似陷思憶,不由得笑了笑:“當年,那三人意氣風發。他們結伴遠游,從江州一路北行,在東都遇見了文謙。四人一拍即合,當下決意訪遍名山大川,游歷神州。彼時陳朝已病沉疴,山河飄零,民不聊生,四人心生。尤其是王庭和仲遠,二人出貧寒,對世間不平甚為憤慨。”
至今仍然記得,阿庭和仲遠游歷結束后曾來拜訪,說起陳朝的苛捐雜稅、朝堂的腐朽破敗,慷慨激昂。畢竟不問政事,便勸他們,國運總有高有低,他們若想做點什麼,何不考功名、仕途?
他們那時對看了一眼,言又止。到了五年后,才知道他們所為。
譙國公主繼續說:“待你父皇接替你祖父,當上鎮南王后,王、常二人終有一日,送上了一份洋洋灑灑的萬字書,痛數陳朝弊病,而后,又寫下《十諫書》,勸你父皇起兵,取薛氏江山而代之。”
裴淵是頭一回聽聞此事,很是詫異。
Advertisement
“姑祖母方才說的王、常仲遠,莫非就是……”
譙國公主頷首:“便是王和常晚云的父親。”
裴淵蹙起眉頭,沉片刻,道:“可云兒從前告訴我,父親只是山村里的教書先生。”
“是麼?”譙國公主出一苦笑,“我那常郎學富五車、足智多謀,原來竟當教書先生去了?還委屈得連家人都要瞞。”
說著,仿佛了往日的心事,出悲愴之。
一旁侍奉的宮人忙將水杯端前,勸喝下。
待稍緩過來,裴淵才問:“后來發生了何事?”
譙國公主想起往事,長嘆一聲。
“你父皇本是懷大志之人,得了勸諫,自是心。于是開始籠絡名士和權貴,準備起事。我不問政事,卻看過那十諫書,寫得確實出,不愧為轟一時的名篇。自此之后,王、常從此被你父皇被奉為座上賓,為起事出謀劃策。”
猜你喜歡
-
連載932 章
重生鳳女追夫忙
她到死才明白,她愛的人傷害她,她信的人算計她,唯獨她恨的人,纔是真的愛她。重生一世,害她的人她要一個個報複回來,而那個她虧欠了太多的人,就由她來保護!重生鳳女追夫忙
134.6萬字8 36294 -
完結581 章

絕色啞妃:王爺,彆來無恙
臨終前還被男友騙光了所有的財產,她含恨而終。再次睜開眼,她竟然穿越到了古代一個啞巴的身上。小啞巴芳齡十八,正是青春好年華,不想有個自稱是她夫君的趙王爺一口一個“賤人”的處處為難。她堂堂21世紀的新新女性怎麼可能被你這封建迷信給打到?虞清絕:趙王爺,你我都是賤人,難道不能一起和平共處嗎?看她一步步破封建思想,平步青雲,殺渣男,捶渣女,絕不手軟!【如果你這輩子,你都不能開口說話,本王便說儘天下情話與你聽。】
115萬字5 46938 -
完結787 章

娘子乖乖:種田種個夫君來
葉清清揣著一包種子去旅游,卻天降火雷,將她劈到了異世的農家院。父親好賭,母親懦弱,哥哥無賴,原生家庭的災難,都落了十二歲的女娃身上腫麼破?惡霸上門,無恥渣爹賣她抵債。幸得娃娃親父子出手相救。救命之恩,無以為報,以身相許,太過淺薄。唯有致富發…
148.3萬字8 103754 -
完結5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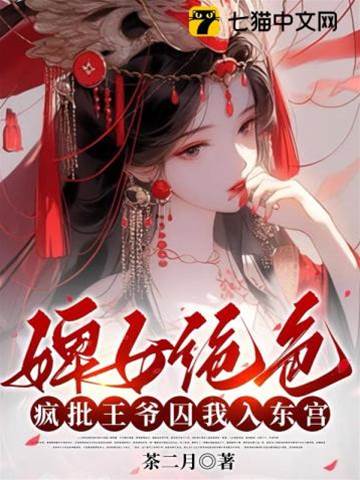
婢女絕色,瘋批王爺囚我入東宮
五年前,洛瓔悔婚另嫁,在夜景湛被誣陷通敵,流放邊城的當天,她風風光光地嫁進了東宮。五年後,夜景湛攜赫赫軍功歸來,洛瓔承受了他如海嘯般的報複。她一夜間從高高在上的太子妃成了過街老鼠,輾落成泥,受盡折辱。再次見麵,她跪在他腳邊,卑微祈求,“求你幫我找到我的孩子。”想起那個孽種,他眼裏似是淬了毒,“好。”從此,她成了他見不得光的暖床丫鬟,被迫親眼看著他與她人柔情蜜意,相知相許。當心徹底冷卻,洛瓔決心離開,可夜景湛卻在得知一切真相後,死死不肯放手……
97.7萬字8 21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