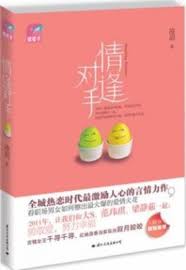《錦繡女嬌醫》 第592章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父親是個招人疼的小老頭,但凡清醒著,總和人科打諢地鬧上幾句。
醫院裏的小護士平時見了老人都躲著走,都不願意伺候,卻總往我父親的病床前跑,說「這帥老頭一看年輕的時候就是個男子」。
我聽后當著父親的面跟母親告狀,「我爸真是風.流了一輩子,都到這時候了,還這麼招小孩喜歡。」
「可不,」母親把橘子皮剝了,又剝了橘瓣外面的那層薄皮,把裏面的籽單獨弄出來給父親吃,別提多細緻,可溫的作還伴著兇的眼神,「我管了一輩子也沒管住,就是這麼個風-流種,有什麼辦法呢?」
父親沒有什麼牙齒的緩慢咀嚼著橘瓣,沒了平日裏那份中氣十足,調子都不如平時高了,哼哼道:「說的跟我犯過什麼事似的。」
母親輕哼一聲,「你沒有嗎?」
「我哪有。」父親一臉委屈,「小姑娘們都喜歡我,可我只喜歡你。」
這麼大年紀的人了還能說出這麼麻的話,我們在病床邊都被麻的了半邊子,母親抿著笑,紅著臉嗔父親,「也不怕孩子跟你學壞了。」
父親吃了半個橘子就累了,躺下睡了好一會兒,呼吸聲原來越緩慢、綿長,院長過來悄悄告訴我們,就是這幾天的事了。
我和母親都是醫生,又怎麼會不知道父親的況呢,只是不願意去想。
剩那麼幾天,父親不願意在醫院裏待,吵吵著回家。
到了家,我們幾個師兄弟,以及孫輩、重孫輩都在家裏候著,守在父親邊照顧著,真真是四世同堂,兒孫滿堂。
小弟和二師哥也趕了過來,跪在父親面前,握著他的手,一個喊「爸爸」,一個喊「義父」。
父親勉強睜開雙目,看看二師哥,再看看小弟,手在小弟臉上一拍,「你小子,也老了啊。」
Advertisement
小弟哽咽地喚出,「爸……」
父親又出大手了二師哥的臉。
二師哥膝行上前,握著他的手,滿眼是淚,「義父,對不起……」
「還義父?」父親嘆口氣,「了一輩子的義父了,改個口,跟著易恩喊我聲『爸』吧。」
小弟泣不聲,二師哥噙著淚,當即叩首改口,「爸!」
父親說想拍個全家福,致敬請了照相館的師傅來家,父親母親坐在正中央,孩子們都蹲在他們跟前,依次依偎在他們邊,滿滿當當一家子。
「都樂一樂啊,孩子們給打個樣,哈哈幾聲讓太爺爺聽聽。」致敬在我後提議。
我那小孫子是個鬼靈,當即「哈哈哈哈哈」笑了起來,如平地一聲雷,讓眾人一驚,跟著笑了起來,照相機「咔嚓」記錄下了我們的樣子。
父親又昏睡過去,我們守在床邊,看著氣若遊的父親,淚水止不住地落下來。
母親卻是說不出的平靜,揮揮手把我們都推了出去,「忙了好些時候,大家都累了,回去歇歇吧,最後這段路,有我陪著就行。」
我不敢走的太遠,就守在門口,觀著裏頭的靜,主要是怕母親熬不住。
母親坐在床邊,拿著小梳子,給父親梳著頭髮,「都快一百歲的人了,頭髮卻茂,我把你梳的帥氣點,等到了那邊你好繼續做你的風-流鬼。」
「那你還是把我梳的丑一些。」父親著些迴返照的力氣,著母親笑,「丑點沒關係,你能認出我來就行,我在那邊,老老實實地等著你。」
母親道:「這輩子還不夠啊,你還想要我的下半輩子?」
「當然要!」父親霸道得很,「別說下輩子,你的下下輩子,我也要,誰也搶不走!」
Advertisement
母親手父親的鼻子,「你這混蛋,霸道了一輩子。當初娶我,也是這個臭德行,還得讓我穿著婚紗大老遠從天津奔過去,壞了!」
父親咯咯笑了笑,「誰讓你不肯嫁我呢,為了娶你,老子兵法都用上了。」
他勉力掀開薄被,拍了拍旁,讓母親躺下去。
母親了鞋子,在他旁躺下,腦袋伏在他的肩膀,聽到父親問,「音音,嫁給我,你后不後悔嫁給我?」
「若要後悔,就不會嫁你兩次了。」母親這樣答他。
父親了的頭,「你啊,倔強了大半輩子,跟著我吃了不苦頭。我真害怕,我走了以後,有人欺負你怎麼辦?孩子們能孝順你嗎?」
母親聲音變得嘶啞,「放心吧,孩子們孝順得很,沒有人會欺負我。這輩子,欺負我欺負得最狠的就是你了。」
「我那是為了讓你記住我。」
父親連笑的力氣都沒有了,只是努力湊過去吻了吻母親的額頭,「音音,再喚我一聲相公可好?」
母親抬起頭來,扯著角笑了,像年輕時候那般,地喚,「相公。」
「哎,真好聽。」
父親笑著,雙目緩緩闔上,竭盡全力輕喚了一聲,「夫人。」
我們失聲痛哭,母親抱著父親,很久都不曾鬆開。
父親的喪禮,我們本想大肆辦一下,母親說不需要,「我們不講究這些,能讓他乾乾淨淨、面面地走就行。」
一樓客廳設了靈堂,說要簡辦也簡不了,前來送輓聯、悼念的人太多了,母親力招架不住,索留在了屋裏,讓我們幾個師兄弟出面應付即可。
父親母親的舊友多,門客、學生、徒弟、徒孫,紛紛趕來悼念,還都要留下來守靈,盡一份孝心,一撥撥迎來送往,足足三天都沒停歇過。
Advertisement
我的子骨也算不上太好,早早被兒子們趕回房歇著,在床上躺了一會兒,實在睡不著,便溜達著又去了母親那。
母親坐在院子裏的藤椅上,桌上泡著一杯茶,收音機里放著《捉放曹》,是冬姨生前特意給錄的,和父親時常拿出來聽,裏也跟著哼唱著。
茶涼了,我重新燒水給母親沏上一壺,一曲戲唱完,母親睜開眼睛,回了回神,我把沏好的茶奉上去。
母親接過茶,抿了一口,問,「賓客都走了?」
「致誠致信他們在前頭招待著,您就不用心了。」我說著,又道:「大家都問您好,要您千萬保重。」
「大家都記掛著我,我當然要好好保重。」
母親神平靜,看不出太多悲傷,但我知道,父親一走,最不住的就是母親。
我伏在母親的膝上,靜默了一會兒,道:「媽,父親剛走,我就開始想他了。但又覺得,他好像並沒有離開我們,還在保護著我們。」
「我也是。想他得很。」
母親了我的頭,目向不遠,彷彿看到父親還蹲在院中種著小柿子,一邊種一邊碎碎念,「不知道為什麼喜歡吃柿子,酸的要命。」
「我說老婆子,我在院子裏給你綁個鞦韆怎麼樣,你還敢坐上去嗎?等我晃一晃你,你可別嚇哭了啊。」
「哎呦,你別扎我,我最怕你手裏的針了,扎人一下疼得跟什麼似的,太狠了吧,輕點輕點,我可是你親老公,我要是死了你就了寡婦了!」
「音音,咱們打個商量唄,我想死在你頭嘍,沒辦法,我你比你我多啊,我要是死了,你一個人還能再多活幾天。你要是前腳先死,那我肯定後腳就蹬,沒有你的日子,我怎麼忍得了呢。咱都這麼大年歲了,你就讓讓我,讓我先走,你過幾年清凈日子,要是想我了,我再來接你,如何?」
相公,我想你了,你來接我吧。
【全文完】新作很快就要跟大家見面了,敬請期待哦~咱們江山不改,綠水長流!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撩人幾許不自知
【霸總忠犬vs清冷醋壇,酥甜撩人,先婚后愛】 商界合伙人夫婦,表面舉案齊眉,背地里各玩各的。 你有你的白月光,我有我的舊情人。 總裁被爆八卦緋聞,夫人熱情提供高清側臉照。 總裁找上門求打架,夫人沉迷事業甩手閉門羹。 雙向暗戀,卻一朝夢碎,兩人在深愛上對方的時候簽下離婚協議。 夫人另嫁他人做新娘,大婚當日,陰謀揭露。 江映月:你是來復仇的嗎? 沈聽瀾:我是來搶親的。 江映月:我們已經離婚了。 沈聽瀾:我把心都給你,只要你繼續愛我。
43.9萬字8 10653 -
完結2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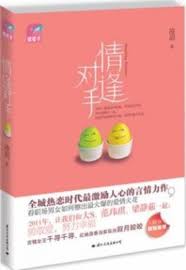
情逢對手
我們兩個,始終沒有愛的一樣深,等等我,讓我努力追上你
55.5萬字8.18 4086 -
完結99 章

天鵝頸
南城歌劇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舞臺上的今兮吸引—— 女生腰肢纖細,身材曲線窈窕,聚光燈照在她的臉上,眼波流轉之間,瀲灩生姿。 她美到連身上穿着的一襲紅裙都黯然失色。 容貌無法複製,但穿着可以,於是有人問今兮,那天的裙子是在哪裏買的。 今兮搖頭:“抱歉,我不知道。” 她轉身離開,到家後,看着垃圾桶裏被撕碎的裙子,以及始作俑者。 今兮:“你賠我裙子。” 話音落下,賀司珩俯身過來,聲線沉沉:“你的裙子不都是我買的?” 她笑:“也都是你撕壞的。” —— 賀司珩清心寡慾,沒什麼想要的,遇到今兮後,他想做兩件事—— 1.看她臉紅。 2.讓她眼紅。 到後來,他抱着她,吻過她雪白的天鵝頸,看她臉紅又眼紅,他終於還是得償所願。
31.2萬字8.18 32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