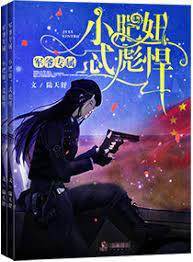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寒門巨子》 第171章 誰之過(中)
「在下蕭元,京城人氏,也是今科會試的舉子。」這名士子落落大方地先報出自家份,這才直奔主題,「在下雖非家學淵源,但也曾在閑暇時讀過幾本兵書,自來也對兵事頗興趣,故而也仔細了解過此番我大越與鬼戎之間的戰事。
「此番北伐之失,堪稱是我大越立國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敗績了,以往縱然也有過損兵折將,但無論損傷還是影響都無法與今次相比,故而我以為朝廷這回定要追責,相關將領員皆都難辭其咎。而要論本次失利最大的元兇,自然非北疆都督沈重山莫屬了!
「戰端一開,他輕敵冒進在前,為主帥不識天候,居然帶了大軍深荒漠而被大雪阻道,致使十多萬大軍困守一隅,被敵軍圍困在後。縱然之後有他臨陣果敢,帶兵死守直到援軍抵達的微末功勞,但與他所犯下的過錯相比,這點功勞就完全不值一提了!」說著,他微一欠,施施然走下臺來。
這第一個上臺一說,果然就把大傢伙的積極全給調了起來,在他下來后,也跟著有人上臺講述自己的看法,不過觀點倒是與蕭元頗為相近,最多就是更著重強調某一方面,其中有個真懂兵事的,居然還指著地圖不斷批駁沈重山的用兵之失,說他若是進軍稍緩,就不會深敵後,導致進退兩難了。
但無論如何細說,他們的觀點依舊逃不過蕭元的見解,直到另一個名楊邗的士子上臺:「諸位適才所言固然有著一些道理,但在我看來,卻還是有失偏頗。各位想必都忘了沈都督出兵卻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朝廷曾下令讓他主出擊,務必要敵於國門之外,若只此看來,沈都督做得已相當到位,並無任何過犯。至於最終的損兵折將,畢竟勝敗乃兵家常事,須怪不得他。
Advertisement
「更何況,在初戰告捷之下,沈都督趁勢向北也不失算,奈何天有不測風雲,這才幫了鬼戎。故而在我看來,沈都督即便有錯,也不是最主要的罪臣,最大的罪過當落在薊幽都督岳霖上!」
「楊兄,你這話我可無法認同了,岳都督可是此番力挽狂瀾的大功臣,怎麼在你口中倒了擔罪之人了?如此顛倒黑白,只為嘩眾取寵可非君子所為啊!」蕭元當即站起來反駁道。
隨即,又有一人起:「蕭兄所言在理,若無岳都督及時趕到,只怕我大越北軍真就要在草原上栽個大跟頭了!更何況,當時的況大家都清楚,他出兵救援雖然拖延了一些時日,可終究也是為了幽州的安危著想。事實也證明他的顧慮是完全正確的,並因此在幽州城下大破鬼戎軍馬,從而得以扭轉戰局……」
「諸位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岳都督固然是最後的大功臣,但在我看來,他也是我北軍在落星海被困近月的罪魁。因為當時沈都督出兵北伐時是和岳都督約定好了,互為犄角之勢,左右進兵。
「諸位,你們想一想,倘若這兩路大軍當真守而進,即便真遇到惡劣天氣,即便鬼戎大軍趁時而,又怎麼可能是我大越邊疆數十萬雄兵的對手呢?到那時,便是泰山頂之勢,足以橫掃草原,將敵軍殺退數百里而無須付出太多代價了。」
他這番話說的倒也在理,使得那些反對他的人一時無言以對,而楊邗的氣勢也越發的盛了:「另外,大家所提到的幽州之危,其實也有個前後之分。若非前線失利,讓鬼戎上下膽氣大壯,則他們是絕不敢冒進殺向幽州的,畢竟百年來,鬼戎最多就是殺到鎮北關附近一帶,還未敢對我幽州重城起過覬覦之心呢。
Advertisement
「所以,即便岳都督確實曾立下功勞,但功是功,過是過,論此番北進失利的最大罪人,我以為還是當數薊幽都督岳霖!」
他這一說,也贏得了不在場之人的認可,在楊邗下臺後,又有幾人上臺,開始列舉岳霖所犯下的過錯,一時間,兩種論調各不相讓,難分高下了。
四樓雅間,皇帝似笑非笑地聽著這些年輕人在那兒激揚文字,眼中芒幾度閃爍:「雖然都是老生常談的說法,但顯然他們也都是家學淵源,平日裏在其長輩的調教下沒有用功啊。」
「皇兄果然慧眼識才,剛剛率先提出這兩個看法的蕭元和楊邗皆是我這兒的常客,平日裏也多發深刻之論,還有不擁躉呢。」
「唔,條理清晰,言辭便給,確實是難得的年輕才俊。只不過……說的這些東西並非他們的真材實料,多半也就是家中聽來的一些陳詞濫調而已。朕在宮中早聽太多人說過相似的話語了,不夠出彩啊。」皇帝笑著喝了口酒道。
懷王無奈苦笑,卻也不好說什麼。這朝中任的,那都是天底下的英才,他們的見識又豈是這些年紀輕輕的士子能比的?所以這酒樓里縱論古今的士子們的一些見解必然不可能別出心裁,超過朝堂諸公的卓見去啊。
話說就他所知,其實現在朝上也就這麼兩種論斷而已,要不就是歸過於沈重山,要不就是說岳霖出兵太遲,導致前軍被圍……當然,這其中又有多是黨爭所致,他一個閑散王爺就不好猜了。
不過他也看出了自己皇兄的失,但這種東西自己都不了解,自然不可能安排人來讓皇帝高興了。
就在這時,下方講臺前又走上一人,卻是個看著二十來歲,極其年輕的書生。只見他也似模似樣地微微欠施禮四周:「在下淮北衡州府江城縣李凌,見過諸位!」
Advertisement
「衡州……李凌……」皇帝一聽到這個名字,略略一怔,「這個人倒是有幾分悉啊……」說著看了眼一直站在自己側的老侍,後者當即會意,笑道:「聖人,您之前確實是讓奴婢查過此人的,就是那個黃麻捐……」
「哦……」這下皇帝立刻就想起來了,饒有興趣地看著下方的年輕人:「想不到這個給朕出了道難題的小縣百姓居然如此年輕,他還今科舉子了?」
「是的,他之前從淮北鄉試中考了出來,據說還頗得張禾的賞識呢。」老侍作為皇帝邊的絕對親信,自然有其過人之。一般時候不怎麼說話,但只要皇帝詢問,他總能給出極其詳盡的答案。
皇帝輕輕頷首:「聽聽他又能說出什麼見解來。」
下邊已經有人打趣說道:「李公子,你若只是拾人牙慧,我勸你還是不要多說了,大家都已經把兩位都督的功過說得很清楚了,無須你再多言。」
李凌笑瞇瞇地沖他們一點頭:「各位說的是,在下既不通軍事,也未打小看什麼兵書,所以這等論點自然是說不好的。」說著一頓,又是一個轉折,「不過在聽了諸位的一番說法后,我卻有一點自己的愚見,此刻卻是不吐不快,若有什麼不對的,還各位多多包涵。
「諸位都只說過錯在沈岳二位都督,卻有沒有想過,其實大家都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人,那才是我邊軍在北方草原陷困境的本所在。」
在眾人略顯疑的目注視下,他肅聲道:「那就是糧草轉運!是因為對前線的糧草輜重的運送不夠及時,大雪所阻礙,方才導致了前軍在落星海被困,甚至於,在我看來,岳都督所以未能及時出兵,也與糧草調撥未能及時跟進有關。只是沈都督子急了些,也認定了糧草調度不是難事,必能跟上,才貿然進兵,岳都督則更為老穩重,便留在了幽州!」
Advertisement
這一番話不但說得眾酒客士子一陣發愣,就是四樓的皇帝,也出了若有所思的神來:「他所言,還真有一定的道理。對了,一開始就把過錯推到沈重山上的,不就是北關轉運使方面的人嗎?」的,居然就讓他抓到了一些之前被忽略掉的細節。
下面眾人這時已經有些反應過來了,頓時有人反駁道:「你說的隨意,這糧草轉運本就不是容易之事,有所耽擱也是經常的,怎能胡把罪名編排到他們頭上呢?」
「就是,你如此嘩眾取寵,可非我輩讀書人該做的事啊。」
面對眾人的詰問,李凌依舊是一副笑的鎮定樣子:「諸位且聽我慢慢道來。其實我一開始也未察覺到這一層,直到這位仁兄剛才在地圖上點了數糧倉,要鎮和堡壘給我看了,我才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況——這些常勝倉、北進鎮,萬勝堡都是在我大越邊境線之的,而在鎮北關之外的大片區域,雖然我們依然有不下數十個堡壘要塞,可我們的糧草卻極在出兵前後送到這兒,這兒,還有這兒……」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在地圖上把幾個重要位置上的堡壘一一點出,面卻已變得極其凝重。
猜你喜歡
-
完結2261 章

影視世界當神探
陸恪重生了,還重生到了美國。但他漸漸發現,這個美國并不是上一世的那個美國。 這里有著影視世界里的超凡能力和人物,他要如何在這個力量體系極其可怕的世界存活下去? 幸好,他還有一個金手指——神探系統。 一切,從當個小警探開始……
416.5萬字8 46115 -
完結358 章

嫡女無雙:惹火棄妃太搶手
手握大權卻被狗男女逼得魚死網破跳了樓。 可這一跳卻沒死,一眨眼,成了草包嫡女。 不僅如此,還被自己的丈夫嫌棄,小妾欺負,白蓮花妹妹算計。 你嫌棄我,我還看不上你;你欺負我,我便十倍還你;白蓮花?演戲我也會。 復雜的男女關系,本小姐實在沒有興趣。 和離書一封,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 原以為脫離了渣男是海闊天空,可怎麼這位皇叔就是不放過她? 說好的棄妃無人要,怎麼她就成了搶手貨了?
81.3萬字8.09 94242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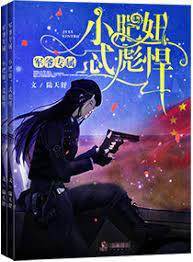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
完結529 章
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一朝穿越,慕容輕舞成了慕容大將軍府不受寵的癡傻丑顏二小姐,更是天子御筆親點的太子妃!略施小計退掉婚約,接著就被冷酷王爺給盯上了,還說什麼要她以身相許來報恩。咱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躲躲藏藏之間,竟將一顆心賠了進去,直到生命消亡之際,方才真切感悟。靈魂不滅,她重回及笄之年,驚艷歸來。陰謀、詭計一樣都不能少,素手芊芊撥亂風云,定要讓那些歹人親嘗惡果!世人說她惡毒,說她妖嬈,說她禍國?既然禍國,那不如禍它個地覆天翻!
89.6萬字8 47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