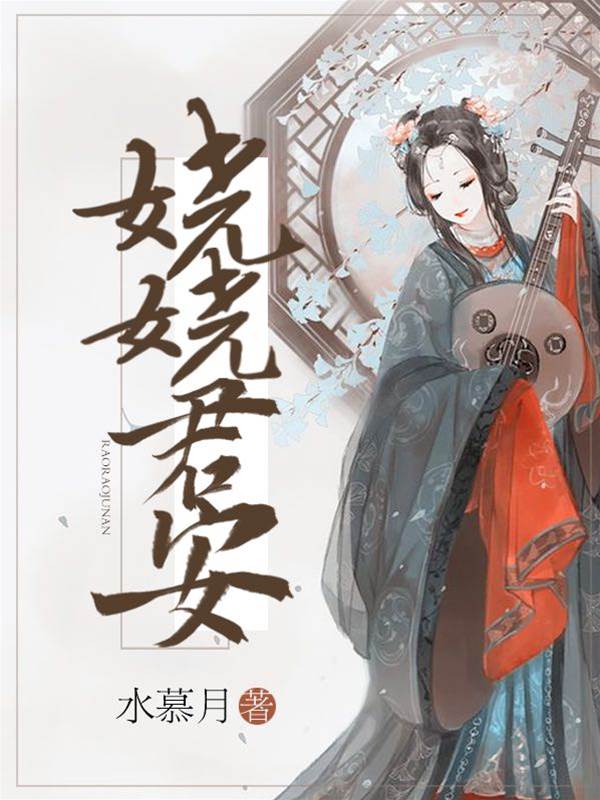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詐尸狂妃要逆天》 第348章 淳于焰去了東堂
第二天的清晨,新婚燕爾,赫連玥是從甜幸福之中醒來的,昨夜被折騰得夠厲害,即便他足夠溫,可到了最后,還是有點招架不住,竟然哭出聲來,渾酸痛得很。
一想到昨晚的種種,臉上止不住浮起一層紅暈,不已。
“大王......”微微翻了個,手抱住邊之人,然而卻撲了個空,被子里蓋著的是枕頭,不是淳于焰!
赫連玥目一凜,立刻將枕頭丟出去,小手在被窩里探了探,才發現被窩是冷的,證明他早就離開了。
昨日大婚,他竟然一早就消失不見!到底是什麼意思!
“淳于焰你個混蛋!”
赫連玥心里的甜瞬間變了憤怒和疑,猛地掀開被子下床,隨意披了件裳就跑了出去,門外侍衛看見穿這樣,頓時紅了臉龐,低下了頭。
“王后......”
赫連玥沒有發現自己穿得多淡薄,直接抓著侍衛就冷聲問,“大王呢!他去了哪里?你昨夜一直在這里,肯定知道他的行蹤!”
侍衛耳子都紅了,睜眼就是襟的位置,他驚得跪下,連忙道:“王后息怒!大王......大王確實天未亮就離開了,他還留了一封信給你。”
說著,這侍衛從懷里取出一封信來,畢恭畢敬地舉到頭頂上。
赫連玥一把奪了過去,當場就想撕開信封看看,但想著還有人在,生生忍住,抿抿轉回了寢宮里。
信封上面寫的“王后親啟”龍飛舞,不算好看,但虬勁有力,豪邁大氣,確確實實是他的字。
赫連玥幾乎可以想象他當時在燈下匆匆寫信的模樣,大概是走得急,所以字跡才如此焦急潦草吧!
Advertisement
到底是什麼事,會讓他連個告別都沒有,在大婚次日就匆忙離開?
想不到任何理由,想到哪個男人會在新婚之夜丟下新婚妻子離開,除非,不在意罷。
不知道是以什麼心打開信封的,已經沒有了憤怒,竟然出奇地習慣他一而再再而三得這樣對待,就像曾經的那些年一樣。
習慣真是可怕的東西,以至于那麼平靜,默默地把信看完了。
他在信里說,他要去攻打東堂,原本不需要那麼著急的,但是他想著東堂肯定會以為他在忙著大婚的事,不會去攻打東堂,于是,他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連夜率兵去突擊東堂!
信里前后都有道歉,說他也不想離開,但是況急,希理解。不辭而別,也是擔心傷,也希原諒。
前前后后,他總有自己的理由和借口,卻從未真正站在的角度考慮,即便道歉,也顯得那麼無力。
在赫連玥眼里,大過天,沒什麼比和心的人在一起更重要了,和江山,必定是選擇江山的。可是他呢?口口聲聲的道歉,卻依舊在新婚之夜離開了。
呵呵。
虧得以為他是真的接納了,虧得昨夜那麼歡喜,抱有期待,卻不曾想,都是空歡喜罷了。
赫連玥不知道衫淡薄地站在原地多久,著腳在地上,腳趾都被凍得通紅了,似乎也不覺得冷,如同寒風中冷卻的雕像,半晌都沒有過。
“王后......”侍得到侍衛的消息,輕手輕腳走了進來,小心翼翼地躬道:“天氣寒冷,奴婢先為您更吧!”
赫連玥聽見有人說話,眼睛才了,侍見沒發怒,自作主張地拿了新的王后服飾過來,“王后,奴婢伺候您更。”
Advertisement
赫連玥麻木地掃了一眼,淡淡嗯了一聲,不聲將那封信塞回信封里,隨即張開手,任由侍伺候換上新。
侍退下上的衫之后,看見上那些痕跡,臉忍不住紅了,作也慢了下來。
雖然不過是慢了一點,赫連玥也察覺到了,看了侍一眼,隨即也發現了自己皮上那些瘋狂的痕跡,心頭微微一熱。
這些都是他昨夜弄的,他那麼瘋狂那麼癡纏......記得他每一個作每一句話,都那樣溫,含脈脈。
心底突然燃起了一希,也許,他真的在乎的,要不然他昨夜怎會如此瘋狂呢?
是的,追他那麼多年了,他的心若是石頭也都焐熱了,如今嫁給了他,他不管不,也是在意的。
所以,他離開的時候,才會和解釋那麼多吧?
且不管那是不是自我安,赫連玥心里好歹舒服了一些,自己接過服遮住,對侍道:“你出去吧!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那奴婢告退,王后有事就奴婢,奴婢在門口守著。”侍恭敬地退了下去。
赫連玥不喜歡這些累贅的服,直接換了自己平時穿的勁裝,扎了個高高的馬尾,然后就出門去了寧珂和楚君越的住。
來到的時候,寧珂正抱著小木木站在廊下,楚君越則在雪地里舞劍,煞是好看,沒一會兒,那些飛揚的雪落在地上,竟然是一副畫,描繪的正是寧珂抱著小木木看雪的場景。
“啪啪啪啪!”
赫連玥率先鼓掌,表示驚嘆與贊許。
寧珂聞聲回頭,看見是赫連玥來了,立刻笑了出來,“玥兒你怎麼那麼早就過來了?新婚燕爾,也不睡個懶覺什麼的?”
Advertisement
“可不是。”楚君越收了劍走過來,難得出了笑容,揶揄道:“當時你珂兒姐姐可是三天都下不來床。”
寧珂瞪了他一眼,腳尖一踢,勾起一塊雪團砸到他上,“沒點正經!”
“哈哈哈哈!你這樣豈不是被我說對了,惱怒!”楚君越不躲不閃,笑得更是開心。
他收到了消息,昨夜淳于焰確實是和赫連玥房了,他多安心一些,不必再那麼擔心淳于焰覬覦小珂兒了。所以,他今日心不錯。
赫連玥看著他們兩人如此恩的樣子,心中又羨慕又酸,苦笑了一聲,低聲道:“我沒有珂兒姐姐這樣的福氣,昨天夜里,大王連夜離開了。”
而,早上才發現。
說出來都可笑!
寧珂一愣,隨即臉上出怒氣,“昨天房花燭,他怎麼可以一走了之!”
楚君越擰著眉,眸沉浮,沒有搭話。
昨夜發生了什麼,他再清楚不過了。
赫連玥見寧珂也不知的樣子,不知道為什麼,心中竟然松了一口氣,臉也沒有那麼郁繃了,坐在了寧珂邊,啞然失笑道:“是啊!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他說要趁著東堂松懈,趁著房花燭夜......去突襲東堂。”
“什麼?”寧珂蹭地一聲站了起來,小木木被嚇了一跳,瞪圓了眼睛瞅著,都合不上。
寧珂憤憤不平地指責,“他怎麼可以那麼魯莽!即便東堂不會料到他在大婚之日發兵,但是路途遙遠,等他過去的時候,那東堂也會察覺!這樣的大事,他怎麼可以不和我們商量就善做主張,太過分了!”
現在總算是明白了,為什麼淳于焰昨天那麼遷就赫連玥,不就是疚麼?
Advertisement
他一早做好了打算,卻誰也不告訴,獨自率兵去攻打東堂!
簡直是任!
“珂兒姐姐......”赫連玥拉著坐下來,反而比寧珂平靜,嘆了一聲,“你別生氣了,他不告訴你,也是不想將你們卷進去,北越的仇,他自然要親自手。”
“你的意思是......”寧珂這才聽出來了什麼,愕然道:“當初北越,和東堂不了干系?后面利用弄走你們的牲畜,也是早有預謀的!”
赫連玥點頭,“對,東堂是個小國,對北越遼闊的地域早就虎視眈眈了。挑起北越,本來就是東堂的一個計謀而已,只是我們及時趕回來才沒讓東堂得逞,后來牛羊馬匹被弄走,也算是東堂賊心不死吧!”
“那他更加不能自己親自去了!他是北越大王,大可以派人出站,何必......”寧珂嘆了一聲,一旦他出了什麼事,北越群龍無首,又該如何?
赫連玥抬眸看住,肅然道:“所以,他把北越給我了,一旦他不測,我就......”
“他不會有事的!”寧珂打斷了,隨即抬頭對楚君越說道:“我們不能讓他一個人去,準備一下,我們也去!”
楚君越一點都不意外這樣決定,豪爽地點頭,“好,只要你想走,現在就可以。”
“珂兒姐姐......”
赫連玥愕然,臉上出了愧的神,剛才還在懷疑......沒想到珂兒姐姐竟然不顧自己安危,也要幫北越。
是想多了。
寧珂素來是個雷厲風行的子,說走必須是要走的,也沒有什麼東西要收拾,親兵那些也有楚君越去安排,不出半個時辰,就啟程離開。
赫連玥親自送到城門口,姐妹兩人不了依依不舍地逗留一會兒,各種叮囑待,仿佛此去就是生離死別似的。
楚君越看不下去了,催促,“時辰不早了,我們該走了。”
“那玥兒,我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寧珂用力地抱了赫連玥一下,赫連玥也抱著,眼睛潤,“珂兒姐姐,你也保重,我等著你們回來。”
“好!”
寧珂拍了拍,隨即頭也不回地轉踏上了青鸞的背上。
然而,就在要起飛的時候,不遠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隊人馬,卷著風雪洶涌而來!
“那是什麼人?!”驚呼!
楚君越一看,也微微變了臉。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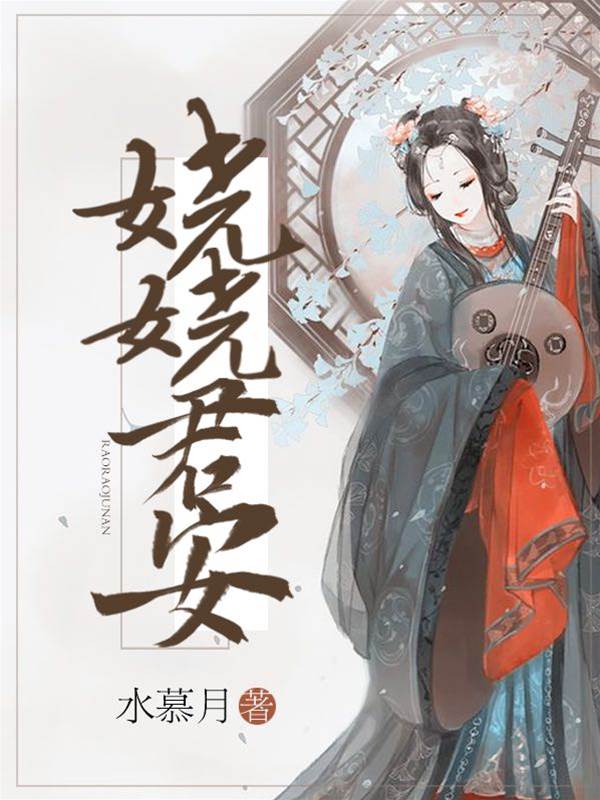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