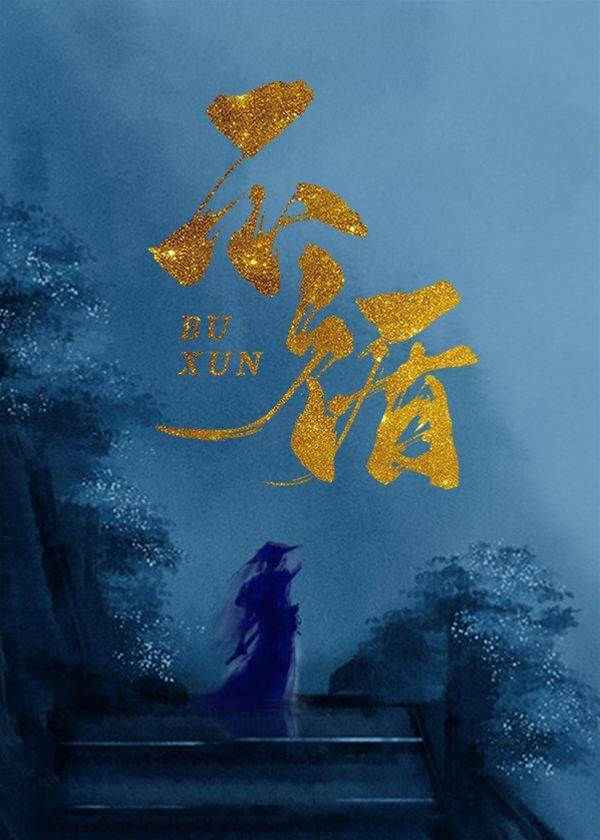《毒妃有喜,我的將軍好殘暴》 第160章 鎮南王妃生前之事
下了一夜的暴雨,“搖搖墜”的河堤況更加急。
曾府尹貪墨歸貪墨,總不希看到河堤真的坍塌,河水淹到城里來。
天剛剛亮,也不管雨大雨小,去看了眼自己的夫人,叮囑丫鬟好生照顧后,便領著幾名屬下,以及工部派來的那幾個人,匆匆忙忙的往淮河上游趕去。
幾乎是他前腳剛離開曾夫人的院子,后腳一抹影就溜了進去。
院子外面守著不士兵,算得上是除了地牢之外守衛第二森嚴的地方。
然進得院子后,里面卻沒什麼守衛,下人籠統不過十個。
蕭璟月好不容易找到書房的位置,正要進去,一名面容祥和的夫人走了過來。
據線報容,曾策雙親已故,岳父岳母在他出任潼淮府府尹后沒幾日清福便相繼去了,三姑六婆之類的親戚多但鮮來往,偌大的府中只有一名弱多病的夫人,和一個十來歲的兒子。
如此看來,眼前這位夫人必定是曾夫人無疑。
不過,傳聞曾夫人弱多病,常年纏綿在榻,并不似面前這位夫人一般面紅潤。
蕭璟月心下生疑,縱躍上屋梁,將形藏起。
“你在這里等著。”曾夫人淡聲吩咐完,獨自推門走了進去。
跟隨前來的兩名婢應聲守在了門口,目不斜視的著正前方。
蕭璟月低頭看了眼纏在手腕上的青蛇,而后指了指站在最右邊的那名婢。
青蛇像是聽懂了他的話,點了點它的蛇頭,吐著蛇信子蹭了他的手背幾下,沿著屋梁爬到那名婢頭頂上。
找好位置頓住后,再次沖蕭璟月吐了吐蛇信子。
蕭璟月點頭。
下一刻,倏地閃至另外一名婢面前。
作快得如殘影般,手起手落,婢來不及發出半個音節,便倒在地。
Advertisement
另一邊,青蛇死死的絞住那名婢的脖子,那婢便是想發聲,嚨也得發不出半個音節。
等想起來去踢門制造靜的時候,蕭璟月已經走到面前,一掌將劈暈。
“誰?!”
屋忽然傳來曾夫人的喝聲。
蕭璟月淡定自若的將青蛇纏回手腕上,推門而。
曾夫人看到他,愣了一愣,有些不確定的問:“蕭將軍?”
自打蕭將軍年中班師回朝后,民間流傳了不關于他的畫像。
輾轉幾月,畫像大肆傳開,就連潼淮府這邊也有人開始賣將軍畫像了。
據民間傳言,說是蕭將軍大殺四方,可鎮妖邪。
曾夫人自然不會買男子的畫像,是自己那個心肝兒子,兒子自打進學起,便仰慕蕭將軍,偶從街上走過,遇到賣畫的,直接就將所有畫像買了回來,掛得滿臥房都是,便是想不看見都難。
蕭璟月輕輕頷首,“曾夫人。”
曾夫人看了蕭璟月一眼,并未大喊大將護衛引來,也未質問他為何出現在此。
走到桌邊坐下,倒了兩杯茶水,將其中一杯推到對面的位置,溫聲道:“將軍請坐。”
蕭璟月開擺坐下,垂眸了眼面前的茶水。
曾夫人道:“想來那兩個丫頭已被將軍擺定,無人奉茶,將軍若不喜喝冷茶便不喝吧。”
蕭璟月沒有作聲,端起面前的冷茶,用力溫熱后,將曾夫人面前那杯冷茶換了過來,淡聲道:“聽聞曾夫人子骨弱,天氣寒冷,忌飲涼水為妙。”
曾夫人低下頭,看著面前冒著裊裊熱煙的茶水,神忽然變得復雜起來,“自打我纏綿病榻起,便是連酷暑之時下人端上來的都是溫水溫藥,已多年未曾嘗試過冰水的覺了,而今……”
Advertisement
說到這里,曾夫人突然嘆了口氣,雙眼微微潤,繼續道:“而今能下榻自由行走,不需他人照料亦能生活無憂,只是,卻已經不曉得冷熱是什麼覺了。”
蕭璟月聞言,倏地抬眸,看向坐在對面的中年婦人。
傳聞曾夫人弱,親七八年才得一子嗣,而后便病魔纏數年。
如今細瞧這比實際年齡大上許多的容貌,想來傳言起碼有七八分是真實的。
蕭璟月沉默片刻,問道:“曾夫人可是有難言之?”
曾夫人搖頭,“事已至此,多說無益。”
頓了頓,目沉沉的著對座的年輕男子,問道:“不知蕭將軍此行,所謂何,所謂何事?”
“說來慚愧,本將軍奉皇上懿旨,前來潼淮府協助調查河堤坍塌一按的八皇子,于日前被曾府尹引淮河中下游的中,九死一生出來,撞見窩藏大量銀的房屋,而后被曾府尹收押牢。”
蕭璟月說罷,著曾夫人的目凌厲了幾分,聲音也冷了下來,“本將軍此番從牢中私逃出來,為的便是查清河堤坍塌一案的,以及那些被私藏在河堤附近的銀。”
因為蕭璟月的話,書房,頃刻間安靜得一針掉落的聲音都清晰可聞。
曾夫人好似早就知道了曾府尹的所作所為一般,并不驚訝。
沉默了許久,輕聲道:“今日,民婦沒有見過蕭將軍,蕭將軍也沒有來過此。”
蕭璟月明白過來。
即便深知對方只是個手無縛之力的婦人,亦沒有輕舉妄。
深深的看了曾夫人一眼,干脆利落的起離開。
將將踏出門檻,又聽婦人的聲音傳來:“昔年于潼淮府中,民婦得鎮南王妃搭手相救,多活了數十年。而今是人為,但恩猶在。不論將軍信也好,不信也罷,民婦在此冒著大不韙之罪提醒將軍一句,將軍天縱之才,只可惜鋒芒太過,雖有鎮南王府為后盾,但若無宏圖壯志,不如遠離朝堂,承接先輩,固守一方安穩。”
Advertisement
蕭璟月聽到“鎮南王妃”四字時,目微微閃爍。
又聽后面的話,轉問道:“依曾夫人所言,若有宏圖壯志,當如何?”
曾夫人并未接他這茬,說那等大逆不道之話,只是道:“鎮南王妃非潼淮府人士,時卻在潼淮府長大,是遠近聞名的大人,將軍自喪母,若對鎮南王妃生前之事有所好奇,可至城東的東南茶肆詢問管事一二。”
靜默片刻,蕭璟月回過,面對著曾夫人,拱手行了一禮。
才消停了小片刻的天空,轉眼又開始下起了綿綿細雨。
蕭璟月輕著青蛇的腦袋,往城東的方向看了眼。
頃,突然轉過,朝相反的方向而去。
蕭璟月離開不久,曾夫人站起,將燭臺上的蠟燭取下。
為固定住蠟燭,一般燭臺放置蠟燭的位置,都會有一半指長的鐵針。
蠟燭取下后,燭臺中央尖銳的鐵針畢現。
兩名丫鬟仍舊倒得不省人事,橫七豎八的躺著。
曾夫人走到們旁,高舉手中的燭臺,猛地將燭臺尖銳的鐵針扎進其中一名丫鬟的太中。
咬著牙關,發了狠似的,在兩名丫鬟的上一連扎了數十次。
確定全都斷氣后,手中的燭臺無力的落。
旋即雙一,坐倒在地。
著滿風雨前來找曾夫人的年見狀,失聲喊道:“娘!”
猜你喜歡
-
完結310 章

重生有喜:皇後孃娘撩又甜
前世,鄰居家竹馬婚前背叛,花萌看著他另娶長公主家的女兒後,選擇穿著繡了兩年的大紅嫁衣自縊結束生命。可死後靈魂漂浮在這世間二十年,她才知道,竹馬悔婚皆因他偶然聽說,聖上無子,欲過繼長公主之子為嗣子。......再次睜眼,花萌回到了被退婚的那一天。自縊?不存在的!聽聞聖上要選秀,而手握可解百毒靈泉,又有祖傳好孕體質的花萌:進宮!必須進宮!生兒子,一定要改變聖上無子命運,敲碎渣男賤女的白日夢!靖安帝:生個兒子,升次位份幾年後......已生四個兒子的花皇後:皇上,臣妾又有喜了覺得臭兒子已經夠多且無位可給皇後升的靖安帝心下一顫,語氣寵溺:朕覺得,皇後該生公主了
69.4萬字8.18 60887 -
完結436 章

秀色可餐:夫君請笑納
一窮二白冇有田,帶著空間好掙錢;膚白貌美,細腰長腿的胡蔓一朝穿越竟然變成醜陋呆傻小農女。替姐嫁給大齡獵戶,缺衣少糧吃不飽,剩下都是病弱老,還好夫君條順顏高體格好,還有空間做法寶。言而總之,這就是一個現代藥理專業大學生,穿越成醜女發家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
98.4萬字8 1680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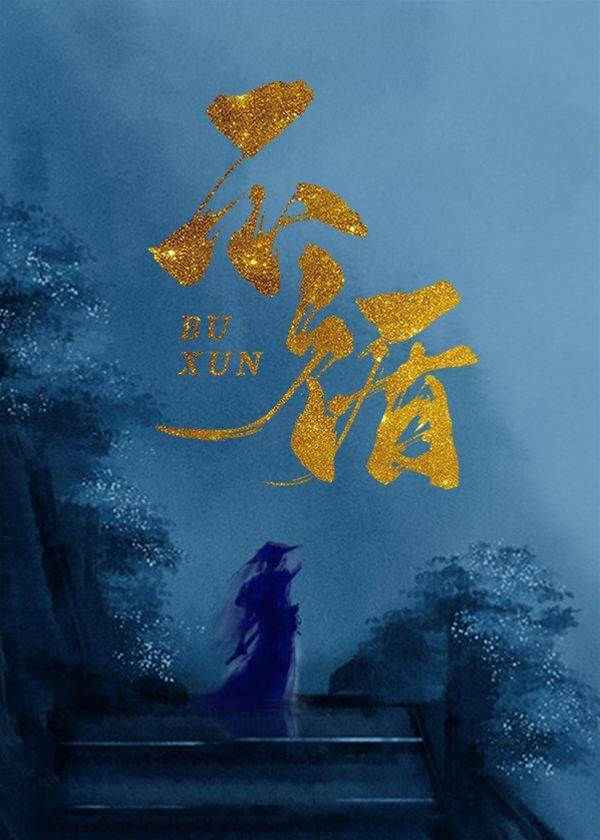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194 章

曾聽舊時雨
鎮北大將軍的幺女岑聽南,是上京城各色花枝中最明豔嬌縱那株。 以至於那位傳聞中冷情冷麪的左相大人求娶上門時,並未有人覺得不妥。 所有人都認定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 可岑聽南聽了卻笑,脆生生道:“世人都道他狠戾冷漠,不敢惹他。我卻只見得到他古板無趣,我纔不嫁。” 誰料後來父兄遭人陷害戰死沙場,她就這樣死在自己十八歲生辰前夕的流放路上。 再睜眼,岑聽南重回十六歲那年。 爲救滿門,她只能重新叩響左相高門。 去賭他真的爲她而來。 可過門後岑聽南才發現,什麼古板無趣,這人裝得這樣好! 她偏要撕下他的外殼,看看裏頭究竟什麼樣。 “我要再用一碗冰酥酪!現在就要!” “不可。”他拉長嗓,視線在戒尺與她身上逡巡,“手心癢了就直說。” “那我可以去外頭玩嗎?” “不可。”他散漫又玩味,“乖乖在府中等我下朝。” - 顧硯時從沒想過,那個嬌縱與豔絕之名同樣響徹上京的將軍幺女,會真的成爲他的妻子。 昔日求娶是爲分化兵權,如今各取所需,更是從未想過假戲真做。 迎娶她之前的顧硯時:平亂、百姓與民生。 迎娶她之後的顧硯時:教她、罰她……獎勵她。 他那明豔的小姑娘,勾着他的脖頸遞上戒尺向他討饒:“左相大人,我錯了,不如——你罰我?” 他握着戒尺嗤笑:“罰你?還是在獎勵你?” #如今父兄平安,天下安定。 她愛的人日日同她江南聽雨,再沒有比這更滿意的一生了。
29.9萬字8 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